《乡村音乐家》
该文是关于乡村音乐方面论文如何写跟乡村音乐家和音乐家相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有风无风的日子,总能听到一曲曲或高亢或低沉,或啼啭或响脆,或愉悦或刺耳的歌声.这些歌声不是风靡一时的流行音乐,且不以农人的喜厌为存在理由,只为乡野大地而律动.虫声唧唧,鸟鸣啁啾,独唱,重唱,对唱,合唱,汇成一条音乐的河流,融入农人的春种秋收耕耪耱耩,融入农人的喜怒哀乐苦辣酸甜,抑扬顿挫,洪钟清音.这天籁,不是点缀,而是共存.于是,冀西北山间盆地的乡村在贫瘠与美丽的交织中成长着,生动,活泛,生机盎然.
青 蛙
青蛙耐得住寂寞,整整一个冬季深藏地下,闭了喉嗓,潜心冬眠.漫长的养精蓄锐,只为等那一声脆响的春雷.大地复苏,青蛙跳出洞穴,置身于白光光的天地,清一清淤积的蒙气,“呱呱”声在北方大地渐次响起,怯怯的,鲜鲜的.蛙声,唱绿河边的柳丝,唱白山脚的杏花,唱红郊野的桃花,乡村立时有了春天的气息.
歌声暴露了行踪,给青蛙招来杀身之祸.民间素有惊蛰日喝煮青蛙水治感冒、哮喘病的说法.一些农人捞来自用,或用水桶运到县城换得几大票票.甚至,有城里人不辞辛劳到乡村亲自捕捞治病.青蛙无力反抗,只将自己的歌声一如既往地唱响.春光明媚,人来人去,青蛙的身影还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溪流、河滩、林地、水田,“呱呱”的歌声并不曾在乡野上空消弭.
那是在发泄对捕捞人的怨怼和不满,还是抒发对生命的坚持、坚守和向往?
冰雪消融,小河水一漾一漾的,闪着炫目的光,在村边的田野上流淌,流过头碾的水车,流过二碾的油坊,流过三碾的村小学,流向附近的大小村庄.河水给了青蛙用武之地,藉着流水,可以让后代把自己的音乐传承下去,广播乡野大地.
半围着泉眼的,是一片水地,平展展,水汪汪.畦子已经变得松软,水中露出一簇簇的稻茬.滑冰的节令已过,孩子们不再来这里嬉戏玩耍,青蛙把安静的稻田当作繁殖的好地方.一片片、一团团粘稠而透明的胞衣漂浮在稻田里,黑色的点状物清晰可辨,一个个天生的歌手在静静地孵化孕育,等待着破衣而出的刹那.
不知,神农氏最初培植水稻,是否也把青蛙邀约到泠泠稻田?
乡语称幼蛙为青季子,个中缘由虽然不懂,但听惯了觉着亲切.从游来游去的蝌蚪到活蹦乱跳的幼蛙,需要一个漫长的嬗变过程,至少在青蛙妈妈的眼里是这样.这个当口,稻田里的成年蛙声寥寥,时显焦急,时显躁动,却无不满含期盼之情.当一只只可爱的青季子开始张口鸣唱,整个稻田便沸腾起来.稚嫩的嗓音、娴熟的歌声交织在一起,是小青蛙找到妈妈后的喜悦,也是青蛙妈妈看到小青蛙成长后的欣慰.
稻田在青蛙的歌声中茂盛.雨后初晴,彩虹高挂在东山之巅.空气清新,到处盈满泥土的腥味.痛痛快快淋了一场甘霖,蛙群立刻兴致高涨,卯足劲高歌起来,生命的在大地上涌动.青蛙俨然成为稻田的主人,“嘎嘎”高鸣着飞来的野鸭,稻叶上“唰唰”作响的稻蝗,以及水黾、瞎虻等的歌声顿时相形见拙,无不闭口失声,噤若寒蝉.
我去泉眼挑水,身边是郁葱的景象,水稻、玉米、葵花,层次错落,浅香徐来.青蛙生活在稻丛里,黄绿色的皮肤辅以黑褐色的斑纹,便于其避开天敌,得以更好地生存.靠近稻畦的脚步声,也或者是嘎吱嘎吱的扁担钩子声,惊扰了一只瞪着圆鼓鼓大眼睛,晾着白肚皮的青蛙,急促的一声“呱”后,“噗咚”一声跳进了田里,没有花里胡哨的动作,简单却实用.这一响不要紧,紧跟着,稻田里“呱呱”声相应和,“噗咚”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如此盛大的场面,更像是青蛙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欢迎熟识的乡人.我索性将两只铁皮水桶摇晃起来,于是,稻田里愈加热闹.盛满清凉泉水的水桶,在肩膀上一颤一颤的,那里面浸润了青蛙的歌声,伴着年少的我行走在乡间土路上.
蛙声是大地丰收的欢歌.“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宋辛弃疾笔下的蛙鸣无疑是一曲愉悦心情,让人心生无限憧憬的乡间音乐.农人在青蛙的歌声中插秧,施肥,拔稗,浇水.水稻听着青蛙的歌声长高,开花,结穗,成熟.晴朗的夜晚,阵阵如潮的蛙声从村边传到农家小院,悠远,绵长,深情,余音袅袅.这样的合唱不需要整齐划一,声调优雅,却收放自然,极具亲和力和穿透力.月色皎皎,下田归来的农人,光了印有阳光肤色的膀子,徐风中就着蛙鸣下酒,犒劳疲惫的身子,听到的是清畅的歌声,闻到的是脉脉稻香.
直到某一天,泉眼生病了,恹恹的,弱弱的,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稻田也随之逐渐消失.好像就在转眼之间,那么多的青蛙不知去了哪儿.一样的月光,一样的乡村乡人,一样的本地老酒,唯独没有了佐酒的蛙声.那是我最想听到的歌声,一曲最简单的原生态歌声,一曲早已溶入农人身体血液的歌声,悠然,恬静,亲切,让人心安,让人心醉.
我知道,这歌声,即便再美,一旦失去,绝难复来.
蚊 子
蚊子的歌声不美,算是另类音乐,轻微,弱小,却令人惊悚.只要蚊子的歌声响起,人们便会如临大敌,循着歌声急急搜寻到访的不速之客.
有水的地方,粪坑,猪圈,水沟,池塘,麻潢,稻田,蚊子皆可繁殖,而且孳生快、数量多.盛夏的乡村,是蚊子的天堂.正值庄稼茂盛,雨水淤积,蚊子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只要农人出现的地方,都可听到蚊子恼人的“嗡嗡”声.
绿头大苍蝇和臭蜜蜂,个头大,奏出的乐声也大,横冲直撞地闯进敞着堂门的农家,“嗡嗡嗡,嗡嗡嗡”,一阵狂轰乱炸.农人迅速挥起蝇拍或随手舞动枕巾、衣服甚至孩子的书本之类的东西,将之驱离或消灭.相反,蚊子个头小,动静也小,行动隐蔽,精于偷袭,往往让农人措手不及.
对付蚊子的另类乐声,白天还好说,虽然各种聒噪的声响给蚊子提供了消声功能,但农人至少能发现蚊子的飞行轨迹.各家各户也会提早从野地拔来白蒿或青蒿,拧成草辫草绳,晒干后用来驱除蚊子.我不知道这种方法是何时何人发明的,但确实管用,不然,不会流传至今.傍晚,屋子里热得慌,农人将小饭桌摆放到院中,盛上饭菜,边乘凉,边吃饭.孩子们早早将蒿子绳燃着,吹灭明火,只让蒿子冒出缕缕青烟.然后,手执蒿绳,你追我赶,绕着院子熏蚊子.蚊子在蒿烟释放的独特香味中销声匿迹,不再强行在农人面前.直到饭菜快凉了,玩得正起劲的我们,才在父母的不停吆喝声中,将冒着袅袅青烟的蒿绳放在一边,悻悻地围坐到红色的小炕桌前,端起饭碗.
“嗡嗡”的音乐声大都在夜晚响亮,尽管听起来微小,却感觉像是一架架轰炸机,盘旋着直冲过来,让人一阵阵心悸.蚊子很聪明,灯光亮着时,静静地藏身在仰层(天花板)、墙角、柜后,伺机而动.灯光一灭,蚊子立即行动.迷迷糊糊中,循着飞来的方向伸手一抓,没逮着,赶紧拉灯四下里找,灯光昏黄,已是不见了踪影.过不了一会儿,耳边再次响起“嗡嗡”声,朝着脑门“啪”地一拍,要么没打中,要么击个正着,手指间的鲜血红红的,惨不忍睹,那可是自己的鲜血啊.蚊子踏着“嗡嗡”歌声一阵阵袭来,搅得人心神不宁,拉灯、躺下,再拉灯、躺下,折腾得一夜睡不好.早晨醒来,伤痕累累,嘴里不停骂着,却对蚊子肆无忌惮的行为毫无办法.涂抹清凉油,用茵陈烟熏,也只能解防一时之痛痒.
玉米地、麻地、麦地等能上水的地都能见到蚊子的身影.家里曾种过二分水浇地.一条小河渠不够大家用,母亲只好等到黑夜去浇水,还得排队,有时一等就是大半夜.夜幕笼罩着田野,手电筒的微弱亮光下,浑浊的河水缓缓流进自家麻地,麻丛深深,清香氤氲.汩汩的流水,掩盖住蚊子的歌声.蚊子的毒针不光能轻松刺破农人裸露的皮肤,还能穿透衣衫伤人于无形.母亲的身上留下蚊子的杰作,脸上,颈上,胳膊上,手上,脚上,到处是红肿的小疙瘩,奇痒难挨.母亲使劲地挠,挠了这儿挠那儿,大扁疙瘩忽忽起得老高,可她必须得坚持着把地浇完,才能回家,才能看到大炕上已经熟睡的孩子们.
农人眼中,蚊子属于名副其实的吸血鬼,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招惹蚊子.有的农人好像对蚊子的“嗡嗡”声一点也不感冒,也不需和蚊子过招拆招,皮肤却毫无损伤.饱受蚊子叮咬的农人很是诧异,田间打诨、巷头闲扯时纷纷请教.说笑之间,对方一句“谁让你的肉嫩来,谁让你的血香呢”,满是调侃、嬉戏的味道.
蚊子是不受待见的歌者,也是农人绕之不去的梦魇.虽然极不情愿听到蚊子的歌声,甚至是排斥、讨厌、反感,深恶痛绝,如同不喜欢绿头大苍蝇、臭蜜蜂和风葫芦(一种蛾子)的另类音乐,也渐渐讲起卫生,但蚊子并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不分昼夜与农人周旋,并适时突袭.
大自然,一个“大”字,包罗万象.看来,蚊子烦人的音乐和农人震天的鼾声,将会一直存在下去,相伴相生,生生不息.
蛐 蛐
秋日的田野,黄黄绿绿.庄稼地,圪塄上,洞穴里,草丛间,到处是昆虫,灰色的、绿色的、黑色的、花色的、褐色的,大小不一,形色各异.事实上,这些昆虫从夏季乃至春天开始,已活跃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伴随着稼穑的枯荣,嘤嘤嘒嘒,为大地增添几许生长和收获的动感.蛐蛐,就委身在田埂的草窠石缝,窸窸窣窣,“吱吱”地鸣唱着秋意正浓.
昆虫们聚会,或者各干各事,都不忘吹弹一曲,吟诵一阕,对歌、赛歌抑或就是自娱自乐.伴随着农人紧锣密鼓的收秋抢秋,别具一格的音乐盛宴正在上演.扇动着红纱翅的蚂蚱不时“嘚嘚”飞起.雄性的中华剑角蝗,乡人称为嘎哒剪,振着的内翅从豆地、谷地、荞麦地上空飞过,“嘎哒,嘎哒”声连绵不绝.草绿色的蝈蝈附着在杂草叶上,摩擦左右两只前翅,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体态娇小,披一身黑衣的蛐蛐,鸣叫声远不如“嗞嗞”的蝉鸣高亢刺耳.不过,蛐蛐日夜都可鸣唱,想啥时唱就啥时唱,高兴了唱,不高兴了也唱,“唧唧吱,唧唧吱”,或悠长,或短促,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尤具韵味.
秋意阑珊,狗尾草在风中摇曳,鹅绒藤绽开朵朵白絮,酸麦麦枝叶绯红.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形,从高空飞过,清越的“嘎,嘎”声拖着长长的尾音,惊动了还未收割的紫花苜蓿地里的蛐蛐.蛐蛐望着南飞的雁群,闭了低得可怜的嗓门,倏地一跃,闪入一片衰败的土,不见了.
月凉如水,浅草长叶上白露欲滴.蛐蛐的歌声再次从巷南堡墙下的草丛传出,又或者就在半坡的榆树棵子、芨芨草中,一声声,一阵阵,混合着滴落的露,凸显了夜的静,平添了秋的伤.天气已经有些凉意.隔着薄薄的窗户纸,蛐蛐的歌声由远而近,街门洞,羊棚,院中盛放着黄灿灿玉米的囤子,仔细聆听,又似乎在窗台根.只是歌声惆怅,清凄,落寞,远不比夏季.
那是在极力挽留稍纵即逝的大好时光吗?还是在叹息自己的体微声弱?
蛐蛐身手敏捷,行动迅速,在母亲行将掩住堂门之际,轻轻一纵蹦到屋内.其时,土坯房内还未生起红红的炉火,却比外面要暖和得多.无怪乎乡人从不称其为蛐蛐,也不唤作蟋蟀,只叫做“秋凉儿”,无形中拉近了人与动物、环境之间的情感距离.如此看来,一些地方方言来得形象,生动,言之有理.待到灯灭后,不需报幕,蛐蛐的独唱音乐会就会拉开帷幕,“吱吱吱,吱吱吱”,长长,短短,缓缓,急急,愈是狭小的空间,愈是显得清晰.那声音一会儿在立柜下面,一会儿在腌菜瓮后面,一会儿又在水泥躺柜下面,听来听去,也不知到底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下得炕来,犄角旮旯瞅瞅,微弱的灯光下,笨拙的家具底下黑咕隆咚一片,终是找它不得,母亲只好作罢.虽然蛐蛐不是什么益虫,歌声不是太优美,但也不是什么难听的噪音,比不得苍蝇、蚊子般讨厌.何况,明早一开堂门,蛐蛐自然会跳出去,也就懒得再找,在蛐蛐的伴奏声中一觉到天明.保不准,这“吱吱”的小夜曲就是一剂催眠、解乏的良药呢.
衣食无忧、闲来无事甚至游手好闲的人,尤喜蛐蛐.他们不辞劳苦,深入穷乡僻壤,将尽可能多的蛐蛐收入囊中带离田野.为了欣赏蛐蛐飙高音、秀歌技吗?当然不是,这些蛐蛐在喂养得身强体壮后,像古罗马的角斗士一样,被关进一个狭小逼仄的罐子或盒子,用来打赌玩乐,俗称斗蛐蛐.两只小小的蛐蛐在小小的竞技场上,拉开阵势,相互厮杀,舒缓的轻音乐变成了尖厉的吼声,细长的触角变成了战斗的旗帜,却是任凭怎么使劲嘶吼,怎么旌旗招摇,都在围观人群极度夸张的喜怒笑骂声中淹没殆尽.
斗蛐蛐在宋代盛极一时,许多部古装电视剧里都有相关情节.更有靠玩蛐蛐、研究蛐蛐而得相位的贾似道,一个贪生怕死、临阵逃脱的主儿,却生来喜欢在围观两强争斗中寻欢取乐.不过,贾似道所著的一部《促织经》,也算开创了天下蛐蛐文化的先河,让蛐蛐这等乡村之寻常野物登上了大雅之堂,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蛐蛐的点点滴滴和前世今生,不仅是其形态、肤色、习性、技巧,也包括其微弱的歌声.
兴许,记住了这微不足道的歌声,也就记住了蛐蛐,记住了田野,记住了乡村.
喜 鹊
家乡土话称喜鹊为歇雀,但喜鹊并不是候鸟,一年四季,农人都能看到喜鹊的身影,听到“喳喳喳”的歌声.这歌声,干脆,利落,短促,一气呵成,绝不拖泥带水,矫揉造作.
喜鹊的羽毛黑白分明.树枝上,屋顶上,地面上,蹦蹦跳跳的,背部黑色的羽毛在阳光下不时闪出蓝莹莹的光泽.冬雪茫茫,田野上高低错落,银装素裹.喜鹊轻轻落在雪地上,尾巴一翘一翘的,低头啄几下,抬头“喳喳”地唱两声,像是在盼望着冰雪消融,春暖花开.
鹊巢建在树上,杨树,柳树,槐树,栎树,凡是可以搭窝筑巢的树木,喜鹊都不会放过.喜鹊不仅是鸟类中的高嗓门,也是出色的建筑能手.根据树桠的粗细、长势,合理确定巢穴的位置和形状,在树桠间一点点垒成或圆或长或扁或宽的窝,如桶,如锥,如盘,如杯,如碗.
春回大地,乍暖还寒.“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天空中传来一阵脆亮的歌声,两只喜鹊一前一后飞过小巷,其中一只嘴里衔着一根短小的黑色枯枝,它们要乘着春光把自己的小窝修葺得坚固而舒适.夏季,鹰鹞在高空展翅滑翔,虎视眈眈地巡视大地,尖厉的唱腔显出王者霸气,撼人心魄.喜鹊窝隐蔽在茂盛的枝叶间,给生存带来较为安全的保障.秋天,树叶变黄,远远望去,金色簇拥的喜鹊窝,给人以沉静、安详之美.进入冬季,树木变得光秃秃,喜鹊窝完全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萧索,冷清,一目了然.一个窝,二个窝,三个窝,有的一棵树上竟达到四五个窝,上下的,左右的,平行的,对称的,相依的,各式各样.蓝天高远,站在树下望去,像天平,像糖葫芦,像三足鼎立.我看见,几只喜鹊站在各自的窝上,“喳喳喳喳”地用歌声交流着.想来,这些或近亲或朋友的喜鹊们,能够栖居在同一棵树上,也是一种难得的机缘.
起初,听到远处山棘林里传来“哇哇”的歌声,我以为是喜鹊,后来才知是通体黑的乌鸦.那些年,田野上的喜鹊和乌鸦一样多,一群群,一,经常从庄稼地飞过,从农林飞过,从农人的房顶飞过,一路上,不忘撒下一串串“喳喳喳喳”的歌声.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喜鹊越来越少,不止我村,连邻近的几个村子里,也鲜见喜鹊的踪影.年少的我曾一度认为,那么多的喜鹊不会平白无故没了踪影,定是飞往银河为牛郎织女搭建鹊桥去了.
少了喜鹊的歌声,农人们听到更多的是家雀“叽叽嘁嘁”的鸣唱.家雀太淘气,经常祸害农人的庄稼,农人对家雀不待见,听到家雀的叫声就很反感.半翅(沙鸡的一种)从庄稼地扑棱棱滑翔式飞过,发出“沙沙”的歌声.石鸡在灌木丛“咯咯咯”地唱歌.布谷鸟“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歌声,听上去像是在唱“布谷布谷,布谷布谷”,意在提醒农人该播种了.啄木鸟“嘣,嘣,嘣”的歌声,是在为树木捉虫.这些音乐家在数量上远逊于家雀和喜鹊,歌唱的季节和时间也远比不上家雀和喜鹊.呱呱油子(猫头鹰的一种)的歌声,听上去则更像是一种“嘿嘿嘿”的奸笑声,在夜深人静时传来,带着恐惧感,极度瘆人,农人越发在已经发凉的被窝里缩得紧.
喜鹊是农人心中永不褪色的美好图腾.那么多的歌者,农人之所以更喜欢喜鹊,当是因为民间流传着“喜鹊喳喳叫,喜事要来到”的谚语.长久以来,喜鹊被农人奉为一种吉祥的鸟,认为喜鹊的歌声会给农人带来喜庆和吉祥如意.当喜鹊落在谁家屋顶或院内的大树上,“喳喳喳”地一个劲鸣唱,主人家就会特别高兴,估摸着一定有远方亲戚要来,或者是出去粜粮能卖上个好价钱,连吃饭都觉着格外香.喜鹊的歌声嘹亮,传出老远,村中的人们无不暗自揣度,这是谁家又有喜事降临呀?啥时也来咱家叫唤叫唤,给咱也带点喜气.听声音,前巷老李家的大儿子不会是要张罗着结婚了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老大不小了,也是该结的时候了!要不,就是老赵家的三来考上中专了,那孩子学习好着呢,走个中专没问题,最赖也能上个柴沟堡师范.
农人把喜鹊的形象刻进窗花,美其名曰“喜鹊登梅”.窗花中的喜鹊不再拘泥于日常生活中的原型,色彩鲜艳,栩栩如生,诗意盎然.大朵大朵的梅花凌寒自开,艳绝清朗,瑞气盈盈.腊月里,前巷,后巷,前堡,后堡,站堡,家家户户都会挑选上一个晴好的日子,把集上买来的抑或自制的喜鹊窗花,用糨糊小心地粘贴在新糊的窗户纸上,新黍穰做的笤帚刷了又刷,抚了又抚,平展展,鲜亮亮,红红火火迎新春,欢欢乐乐过大年,寓意新的一年里幸福吉祥.母亲盘腿坐在大炕上,手里紧握着笤帚把子,越端详越喜庆,越觉得那喜鹊正一顿一顿地摆动头尾,朝着自己“喳喳喳”地叫.
进城潮席卷着乡村汹涌而至,远非村里一条河渠可比,任凭高耸入云的小五台山绵延成黛青色的巨大屏障.好多房屋铁锁看门,锈迹斑斑,院墙残破不堪,甚至只剩断壁残垣,老高老高的荒草,肆无忌惮地占领了院子的各个角落.逃离,也或者是暂别.我从村中穿过,院落和街巷旁的杨柳树上,好多喜鹊窝都空荡荡的,黑黢黢,灰楚楚,一种凄凉感油然而生.
也是,连人都不知去了何方,纵然是最受农人欢迎的歌唱家,喜鹊的歌声又该唱给谁听?
乡村音乐论文参考资料:
总结: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乡村音乐家和音乐家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乡村音乐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乡村音乐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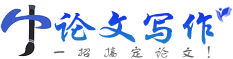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