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女性书写:性别经验和乡村图景的重构以梁鸿、孙惠芬、郑小琼的写作为考察对象》
该文是性别方面学年毕业论文范文跟孙惠芬和郑小琼和梁鸿类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写作栏目迄今已有众多作家参与,其中女性作家有关乡村的书写更是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梁鸿、孙惠芬、郑小琼的写作在其中颇具症候性.女性的“非虚构”乡土书写从细节出发、从个体出发,显示了把“个人言说”有效地镶嵌进“性别/底层/民族国家”话语的努力.她们从“女性叙事”向“社会性别叙事”、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从“个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转换,为女性的写作实践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而复调的、多元的、颇具张力的叙事声音,也在个人与世界、性别与社会、情感与理性、启蒙与民间之间构建了一种可能的对话关系.
【关键词】女性非虚构书写;个人经验;社会性别;复调叙事
【作者简介】吴雪丽,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四川成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8)03- 0112 -06
2010年《人民文学》第2期开始推出“非虚构”文学栏目,尝试开拓另外的写作空间和探寻文学写作的新的可能性,迄今为止,“非虚构”已有许多作家参与其中,而女性作家对乡土的书写和对乡村人的生存境况的关注,使“非虚构”呈现了它重新面对现实、书写大地经验的可能性,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乔叶的《拆楼记》《盖楼记》、郑小琼的《女工记》、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李娟的《羊道春牧场》《羊道夏牧场》等,这些女性书写者不仅关注当下农村的现实境遇,而且开始关注乡村人的精神困境,不仅书写“在地”的依然在土地上的人们,而且书写了那些从乡村到城市的“漂泊者”.因为女性视角的介入,“非虚构”的女性乡土书写和整个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构成了丰富而有意味的对话关系.笔者想探讨的问题是,女性视角为“非虚构”文学提供了怎样独特的性别经验与乡村生存图景?女性的“非虚构”关注的乡土的颓败、乡村人的精神荒芜在乡土文学史与女性文学史上有怎样的意义与价值?性别视野给“非虚构”文学书写提供了怎样的叙事经验、又可能遮蔽怎样的问题?
一、细节、个体与“我”的在场
“非虚构”栏目开设以来,大多数女性书写者选择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作为自己的写作资源或直接的深度调查对象,或者书写乡土的颓败(梁鸿),或者书写乡村的温情(李娟),或者书写乡下人狭隘的精神空间(孙惠芬),或者书写乡下人在都市逼仄的生存空间(梁鸿、郑小琼).而女性的视野,使她们“非虚构”世界的乡土不再只是宏大叙事意义上乡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更重要的是,她们关注更多的是乡土的日常生活,并把整体意义上的乡村生存境况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通过讲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还原一个个丰盈、鲜活或者卑微、凡俗的个体,乡土的生存现实自然呈现.
《人民文学》的“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的宗旨是:“以‘吾土吾民’的情怀,以各种非虚构的题材和方式,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而且“特别注重作者的‘行动’和‘在场’,鼓励对特定现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体验”.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吾土吾民、行动、在场,而践行“非虚构”写作计划的这些女作家们的写作可以说是对这几个关键词的极好注释,她们回到自己成长的村庄,回到和自己一起打工的姐妹们中间,和自己的村民、乡邻、亲人、姐妹们在一起,忠直无欺地记录她们的生活、乡土的过去与现在,并思考、追问、质疑这个时代乡村的种种困境与悖论.
周芬伶在论及张爱玲的小说时曾经说过:“细节描述意象被视为是女性文本的特征,亦是女性文体被排除于主流文学的明显‘缺陷’.”“女性特质与细节描写关系密切,可以说细节描写是对抗整体、宏伟、统一、国家等父权符号的有效策略.”女性书写的一个重要取向是关注细节、关注个人经验.在“非虚构”的女性书写中,“我”就在“他们”中间,而且常常,我就是“他们”,触目所及的是“他们”的生活,也是“我”正在经历的生活.虽然“我”的疼痛不完全等同于“他们”的疼痛,但“我”的疼痛确定无疑是对“他们”的疼痛的见证、记录与体察.在《中国在梁庄》中,“奶奶活成了爹妈、老师和校长”的芝婶,在“我”提到留守儿童的问题时,她一再重复的是“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因为在乡村生活中,她们必须用坚强来对抗软弱.”光河用一双儿女的命换来的钱盖起了新房,被村里人诟病,可是,“我”看到的却是他内心不能言说的伤痛和无奈: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残酷、无儿无女的生活的无望、住在新房里内心的负罪感……
《中国在梁庄》不仅在乡土生活的细部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它最重要的叙事选择也是通过乡土中个体的生存境遇观照乡村的疼痛、迷茫与困惑.五奶奶辛苦带大的孙子被淹死后悲怆地呼喊:“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干啥?”从五奶奶叩问天地不仁中,我们看到的是乡村留守儿童和老人的生存困境.认为“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的菊秀,挣扎、努力、奋斗,却逃不出宿命般的人生,一次又一次梦想的破灭,以至于“现在生活再富足,也不快乐”,折射的是乡村青年生存空间的逼仄.因丈夫出门打工,长久没有消息而思念成疾的春梅,在精神崩溃后自杀,呈现的是在青壮年流失的村庄中的情感危机.父亲梁光正一生的命运沉浮,和古老的乡村政治、家族政治纠缠在一起.“他们”是“我”的乡邻、是“我”的亲人、是“我”曾经的朋友,从对蓬勃的“废墟村庄”的忧患、“救救孩子”的焦虑到对出走的理想青年的梦想破灭的悲悯,对被围困的乡村政治的关注,这一切几乎都是通过一个个“个体”的讲述和“个体”的命运得以呈现.乡村的破败不再是站在高处的理性观察与道德评判,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的真实生存境遇.
诗人郑小琼曾经是打工者中的一员,她痛感于现代化的机械流水线对个体的淹没,在《女工记》中,她试图让那些个体发出声音,“我知道自己需要努力深入到女工中,把这个‘们’换作她,一个有姓名的个体,只有深入到她们中,把这个‘们’换作她,一个有姓名的个体,只有深入到她们中,才会感受到在‘们’背后的个体命运和她们的个人经历”.那些从乡下来到都市的打工者,五年、十年、十五年……最后被都市吞噬或抛弃.17岁的刘美丽,满足于每月150块的零花钱,把剩下的寄往湖南的乡下,她成为乡间外出女子的榜样,可是她无法在城市立足,回家结婚成为她唯一的选择.16岁出来打工的谢庆芳,“纤细的手指慢了半拍/露出乡村的胆怯/眼神里有铁锈样的羞涩/斑驳而灰暗”,而在被机器吃掉三根手指头后,“你的哭泣无法渗透工业的铁器与资本/你无法把握住生活的本相/残断的手指/无法握住农具与未来/同渗透了心灵”.37岁的女工,“像松散的废旧机台/在秋天里沉默,身体里积蓄的劳累与疼痛/化学剂品/有毒的残余物在纠缠肌肉与骨头”,可工厂的招工栏外赫然写着年龄:18-35岁,“37岁的女工/站在厂门外/抬头见树木/秋天正吹落叶”.那么多从别人的都市回到自己的乡村的“旭容”,“饱受疾病的折磨/默默死去/成为无声的部分/工业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呈现虚荣的风景”.无数个“蓉蓉”,希望“用身体打开枯叶”般的命运,可“仍没有遇到收获的秋天”.
作为女工群体中的一个,郑小琼深感这个巨大而沉默的人群正在被变成一个个抽象的影子与数字,正在被公共话语简化与省略,因此“我觉得自己要从人群中把这些女工掏出来,把她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们是一个女儿、母亲、妻子……她们的柴米油盐、喜乐哀伤、悲欢离合……她们是独立的个体,有着一个个具体名字,来自哪里,做过些什么,从人群中找出她们或者自己,让她们返回个体独立的世界中”.在郑小琼那里,“每个人的名字都意味着她的尊严”,她要为那些沉默的自杀者、意外死亡者、不知所终者,那些“被遗忘,最终被时代的胃消化得干干净净”的卑微者立传,把整合进流水线上的“无名者”还原为一个个妻子、母亲、姐妹,把一个个无名的工业生产中的“螺丝钉”还原为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个体,对抗这个“铁”的时代的冷硬与荒寒.
孙惠芬在《生死十日谈》的“开篇“中写道:“小人物、平民的自杀,似乎很少闯入我的视线,即使闯入,也很少了解其具体姓名.他们就像秋天枝头凋零的树叶,飘摇着坠人大地,之后萧萧地归于沉寂……”她尝试探寻活着的痛苦与他们自杀后亲人的伤痛,“一泡屎要了两个人的命”中精明、能干、爱面子的婆婆,向往外边的世界、不愿意干农活、喜欢在网上看书的媳妇,为了孩子拉在炕上的一泡屎双双自杀.赵凤19岁就嫁给乡里人杨柱,可在外边做生意的丈夫发达后却抛弃了她,儿子不学无术,上网成瘾,她得了性病后不敢去医院,最后喝百草枯自杀.张小栓在城里买了房,可没办法接辛苦的父母去住,自杀后三个月父亲也上吊自杀.“回乡A计划”中的耿小云,这个贫苦农家的孩子,多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和家乡的命运,可是却在恋爱失败后自杀.姓万的人家里三个兄弟相继自杀,留下蒙昧的母亲倔强地活着,可她内心的悲苦却无人知道.好强、要面子的周凡荣的老伴出身大户人家,有文化、明事理,年轻时常常替村里人调解是非,可晚年却不堪媳妇的辱骂和儿子的懦弱跳水塘自杀.借助这些曾经鲜活的生命的离去,那些冰冷的死亡统计数字变成了一个个不甘地发出自己声音的魂灵,叩问着天地不仁;借助这一个个死亡事件,那些活着的亲人们的悲痛、承受、忍耐,不屈地言说着生命的悲苦与坚韧.
周蕾在论及女性写作时曾经说过:“细节被用来作为问题切入点,探讨现代中国叙事里‘历史’探究底层矛盾的情感结构.这些探究的出现常常是对于‘自由’以及国族‘整体’既一致但其中又充满矛盾的关注.在此,细节被界定成感官的、琐细的与浮面的文本呈现,与一些改革、革命等等较为宏大的‘眼界’存在着矛盾关系,这些宏大的眼界企图将这些细节纳入其臣属,但却出其不意地为这些细节的反馈所取代.”对日常生活的细节的关注,可以说是女性文学书写最重要的叙事策略.梁鸿、孙惠芬、郑小琼们都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时代转换中,这个时代的主流话语是市场、资本、文明,但她们并没有背对时代而去,而是携带着女性对细节、对日常、对大时代中的个体的关注,深入这个时代的内部,深入被表面的喧嚣和浮华所遮蔽的乡村、工厂,把“个人言说”有效地镶嵌进“性别/底层/民族国家”的话语中,打通了以往的女性书写中两种话语的对峙,在“细节”与“大叙事”之间、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在“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之间搭建了一座浮桥,为女性的写作实践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这种新的叙事策略和性别经验无疑应该被女性文学史所铭记.
一、从“性别”叙事到“中国”经验
在20世纪的女性文学史上,从新文学以来的女性作家庐隐、丁玲、萧红、张爱玲到1990年代的陈染、林白、徐小斌等,女性多从自我的生命经验出发,书写个人悲欢与家国命运,这几乎已经成为女性文学最重要的叙事美学.而女性的“非虚构”书写在这个脉络上可以说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写作空间,她们也是从个人经历、个体体悟出发,但面对的却是自我身在其中的广阔的外部世界,带着自己生命的体温与感悟书写“他们”的故事,并从“他们”的故事中探寻个体与家国伤痛.女性的“非虚构”书写,显示了女性文学从“女性叙事”向“社会性别叙事”、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从“个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转换.换言之,女性写作不再单单是从性别出发的生命经验的表达,而是携带着性别经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中发出声音.
董丽敏在论及中国的女性文学时曾经追问:“置身于后发现代性国家的特定语境中,女性书写到底应该怎样来设计自己的叙事立场:女性叙事主题在面对性别问题的时候,又该如何来放置‘自我’的位置,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浪漫主义意义上的‘个体’,还是更多将其当作某个集体/共同体的代表而在国家、民族和阶级的格局中来加以定位?”“非虚构”的女性书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有效回应,我们姑且搁置关于“虚构”与“非虚构”的理论探讨,单从“非虚构”女性书写目前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的问题出发,即可看到,梁鸿、孙惠芬、郑小琼是“个体”,但她们书写的不再是“我”的经验,更是“我们”的经验,是一个群体与国族在社会转型期的重重裂痕.
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讲述了乡村的破败与凋敝,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可是人却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家族制度的衰落、公共道德监督力的衰退、国家的法律与赡养习俗之间的矛盾,都使得儿子、儿媳不把父母放在眼里.梁庄小学已经关闭近十年了,曾经教书育人的小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也许村庄的真正破败并不在那些内部的废墟,而是这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觉到了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散”.这些叙述可以说彰显了梁鸿关注的不只是“我”的“梁庄”,更是“我们”的农民兄弟们、姐妹们,“我们”的中国.她看到乡土生活细部的裂痕,并以此为“症候”,追问乡土的现状与未来、中国的现状与未来.从梁庄出发,梁鸿试图抵达中国的疼痛,抵达我们这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
如果说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讲述的是“在地”的乡土经验,是农村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日益破败和荒芜,那么,郑小琼的《女工记》记录的则是现代性进程中的另一张面孔,那些从农村出走的、到城市里讨生活的“打工妹”的生命经验.作为曾经的打工妹中的一员,郑小琼一直在艰难地记录、描述、指认被现代工业流水线淹没的那些个体,“她”曾经是“她们”中一员,她要让这些无名者发出声音,让这些卑微的、弱小的但又是朴素的、坚韧的中国经验呈现在“中国”的幕布上.虽然,郑小琼痛感:“文字是软弱无力的,它们不能在现实中改变什么,但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见证,我是这个事情的见证者,应该把见到的想到的记下来.”因此,她要让失语者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她们”中的幸运儿,她有深深的忧虑与不安,她讲述“她们”的故事,也是讲述自己,讲述内心的伤痛、不安、愤怒、悲悯,并承担、抵抗、追问这个世界被光明遮蔽的那个暗角的真实的生存状态,以一块铁的闪亮,坚韧地追问这个“铁”的时代的冷硬、荒寒.换言之,她的《女工记》是及物的写作,这是“我”的生活,也是“我们”的生活,更是“这个时代”的影像,是“这个中国”的疼痛.而这些不为人知的卑微者的痛楚与悲伤,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另一张面孔,正如谢有顺在论及郑小琼的写作时所说的:“她的写作意义也由此而来——她对一种工业制度的反思、对一种匿名生活的见证,带着深切的、活生生的个人感受,同时,她把这种反思、见证放在了一个广阔的现实语境里来辨析;她那些强悍的个人感受,接通的是时代那根粗大的神经.她的写作不再是表达一己之私,而是成了了解这个时代无名者生活状况的重要证据:她所要抗辩的,也不是自己的个人生活,而是一种更隐蔽的生活强权.”
孙惠芬关注的是农村的自杀事件,但对她来说另外的一重意义却是:“自杀在我的笔下不过是一个篮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对生死终极问题的追问和思考……”在对死亡遗族的寻访中,也始终贯穿了以“我”、朋友“贾树华”等对乡村、旷野的赞美与迷恋.乡下人想进城,“一泡屎要了两个人的命”中的婆婆因为未能在城里为媳妇买楼而深感愧疚,所以一直纵容着媳妇最终却忍无可忍.张小栓的梦想是在城里买楼接含辛茹苦的父母进城,却被媳妇的父母占了先,压抑、苦闷最终自杀.乡村与都市这个古老的话题在《生死十日谈》中再次被激活.从对乡村自杀事件的关注、对乡村精神困境的探寻出发,孙惠芬尝试抵达这个时代的普遍症候:关于乡村与都市、生与死、卑贱与尊严,而女性的敏感与细腻,使这种追问接地、及物、触动人心.
从梁鸿、郑小琼、孙惠芬的女性“非虚构”书写可以看到,她们与其说是对乡村、对那些从乡村到都市的漂泊者的生存境遇、精神状况的记录与展示,不如说是想借这种“展示”和“记录”对普遍的中国“现代性”进程发出抗辩之声,这是在一个崛起的中国背后被淹没的、被遮蔽的、抑或是被刻意遗忘的声音.当主流的国家叙述以一个崛起的、富足的“大国”形象呈现时,梁鸿们的写作以一种尖锐的方式,呈现了在“现代性”进程中乡土的现实焦虑与震惊体验.同时,她们也试图为个人的震惊体验寻找到一种可以潜合进大历史叙述的路径,这在梁鸿那里是现代性进程中日益破败的乡村,在孙惠芬那里是乡村的精神荒芜和自救,在郑小琼那里是繁荣、浮华的大工业生产背后被淹没的个体的疼痛.显然,她们都无法超越关于历史进程的话语,但是她们记录的创伤性经验显示了试图去触摸历史本体的努力与尝试,并通过自己的创伤性“震惊”体验,为乡土立传、为乡土步履蹒跚的背影画像.
三、复调:民间、启蒙及对话的可能
如果把新世纪“非虚构”的女性乡土书写放置在整个现代以来的乡土文学脉络中,则会发现她们之于“传统”的复杂性,她们不仅接续了某种文学传统,如梁鸿、孙惠芬等之于鲁迅式的启蒙乡土书写、李娟之于沈从文式的审美乡土书写、乔叶之于赵树理式的乡村政治的书写,都有着或隐或显的承续,或者说,她们的乡土书写是向传统的致敬,而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她们的书写抑或成为乡土文学的一个新的起点,那就是文学试图再次最贴近地、最有效地与现实的对话,或者说,为“现实中国”画像、留下记忆并从“病症”中得以反省自身.这些女性乡土书写者本身就是乡村的女儿,都有着漫长的乡村生活经验,所以,当她们重新面对乡土时,那种或温润或疼痛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体恤、理解等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但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梁鸿、郑小琼、孙惠芬们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她们在对谁说话?她们的立足点在何处?她们认同自己是什么人?她们如何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群体中间,并试图按照她们的方式看待这个变化的世界?
梁鸿在谈到写作《中国在梁庄》的缘起时说:“即使在我离开故乡的这十几年中,我也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我”是“村庄的女儿”,我要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传,“我”所做的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可同时,故乡的痛苦也是“中国的病症”“中国的悲伤”,在此出发,我追问的是乡村何以成了“民族的累赘”“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在这里,内、外两个视角产生了巨大的叙事张力.内视角和外视角的交替使用,使叙事者既在村庄之中、又在村庄之外.当她以内视角观看梁庄时,她是梁庄的女儿,常常深陷于自己的情感记忆中;而当她以外视角、从现实亲历者的角色中抽离出来以旁观者的姿态观看时,她试图探寻的是“乡村”“中国”的病症.王家少年并杀害了82岁的老太,原始古朴的乡村道德认同王家少年那么残忍的行为只有判死刑才能达到惩罚的目的,而“我”关注的是,那么年轻的少年怎样做出了如此残忍的事情?“我”是乡村的女儿,“我”深切地体恤建昆婶在老母亲被害后的愤怒与悲伤,但“我”也是一个归来的“知识者”,从少年杀人事件看到的是中国乡村的“病症”,是“救救孩子”的焦虑.
在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对死亡遗族的调查过程中,叙事者的“乡村的女儿”视角使她部分地认同乡土生存的逻辑,赵凤自杀后,她的父亲一直陷于深深的自责中,他唯一安慰的是女儿托梦给妈要衣服,使父亲认为女儿在那边病好了,叙事者感慨:“狐仙豹真好!狐仙真好!离开徐家,我心里一直响着这样的声音.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不知道死者父亲的心灵如何获得安宁.”但是,“乡村的女儿”视角和“知识者”“启蒙者”的视角也常常发生背离.姜立修的自杀案例就明显地体现了这种认同链条的断裂.在民间伦理和民间道德的视野下,姜立生和小环的爱情为人所不齿,尤其是小环的丈夫姜立修因此而自杀.但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我”更认同的是他们之间的爱情,是自杀也不能摧毁和漠视的当代农民追求爱情自由的权利.可是,在知识分子进入乡村公共空间后引发的道德认同危机、知识分子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对此事件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知识分子的一元化叙事再次显示了它的霸权.在这一关于爱情自由的启蒙霸权下,“二嫂们”再次成为了鲁迅笔下那些“庸众”“无名杀人团“的代表.她们把小环视为迷惑男人的天生尤物,用乡村道德把她定在了耻辱的十字架上.在此,民间伦理与启蒙视野构成了巨大的张力空间,显示了在告别单一的道德判断后,叙事可能到达的多重走向.
郑小琼曾经是打工妹中的一员,“我”曾经和“她们”一样,因此,在《女工记》中,在看到“我”和“我的姐妹们”的梦想、苦恼外,我们还看到了压抑的悲怆与愤怒.但作为诗人的郑小琼,或者说作为知识分子的郑小琼和作为打工者的郑小琼已拥有了不同的视野,在记录下许许多多女工们的挣扎和哭泣时,她也看到了其中可能隐含的爆发和抵抗:那个常常在梦魇中醒来的“周阳春”,“梦里的尖叫成为工业时代的身体里/缓慢的痛楚/正在积聚/迸发”.在《女工:忍耐的中国乡村心》中,郑小琼写道:“身体里的虚弱/跟废旧的机台/加班/欠薪/它们黑色的阴影带给你的伤害/这一切/都让你用一颗中国乡村心忍耐……”而她同时忧虑的是这一颗忍耐的中国乡村心也许有一天不再忍耐:“我不希望这些女工沦为麻木的器具者,也不愿意她们成为的暴力者,但是现实却不能找到和解这些的方式,我只能深深担忧着在底层积聚的暴力,或者被压抑的暴力会成为一股怎么样的力量,它会将我们这个国家如何扭曲.”于是,在郑小琼那里,对女工的生存境遇的记录,不再仅仅是记录这个时代的悲伤、眼泪和感动,还有这个时代的愤怒和对历史的代偿可能付出的代价的忧患.
但在“非虚构”的女性书写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时时提醒着我们——“她们”已经不再是乡村的女儿,她们是外来者,是已经离开乡村的“知识者”“作家”“成功者”.虽然菊秀反复告诉“我”,帮砖厂拉人那段生活是不能说出的秘密,但“我”不仅讲述了她的故事,甚至“我知道菊秀还隐瞒了她的其他更为复杂、黑暗的经历”.在对春梅之死的追问中,堂嫂一再说,“我只给你说这些,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这几天,我心里不美得很,可难受,说起来,春梅的死也怨我,与我有关”.但作为“非虚构”,希望对“真实”再进一步的靠近,“我”依然做了“忠直无欺”的“记录”.还有在《生死十日谈》中,滨城电视台国际部记者张申的摄像机,也让人常常感到强烈的不适,虽然在摄像机的注视下,那个失去了妻子和儿媳、给人逆来顺受的无奈感的老人于吉良,拉开铁门来到摄像机前,“却顿时有了精神,仿佛早就知道在某个时候,他就该是一场戏的主角”,但是,“摄像机”下的讲述,更像是用探照灯重新撕裂并展示那些自杀者已钝痛的伤口,多少让人觉得残忍、冰冷.
但不管怎样,梁鸿、孙惠芬、郑小琼等的“非虚构”写作,在对乡土、民间、城市里的漂泊者等的书写中,已告别了女性书写中那种深具“女性特质”的具有标签意义的私人经验、身体叙事,也告别了乡土书写中那种较为一元的或启蒙、或民间的叙事视野,以女性经验为起点,以社会性别视野去省察“中国的病症”去倾听那些被淹没的、被遮蔽的声音,在一种复调的、多元的叙事声音构成的张力空间中展开,在启蒙与民间、情感与理性、性别与社会、个人与世界之间构建了一种可能的对话关系.
谢有顺曾经指出,“生活的贫乏、想象的苍白、精神的”,是当代文学普遍存在的三大病症,“而核心困境就在于许多人的写作已经无法向我们敞开新的生活可能性”.如果说对底层的、被损害者的漠视是一种写作暴力,是“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殖民,那么,“非虚构”的女性写作可以说是对“生活的贫乏、想象的苍白、精神的”的一种反抗,也是对漠视底层、被损害者的“写作暴力”的一种反抗.现实永远比文学想象更丰富、震撼,“非虚构”的女性书写,正是在直面现实、记录现实并发出自己声音的意义上,重建了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和“文学性”“现实主义”“女性特质”“社会性别”等诸多文学理念、文学传统等构成了并不遥远的回应.这些“乡村的女儿”们带给新世纪乡土书写与女性书写的是一种开阔、丰厚、清明且深具现实意义的乡土经验和性别经验,在日常生活与宏大叙事之间,在个体命运与群体经验之间,在现实讲述与文学镜像之间,“非虚构”的性别叙事落回大地、落回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并在性别、政治、国家的多重视域下展示了一种新的文学可能.
性别论文参考资料:
简而言之:上述文章是关于孙惠芬和郑小琼和梁鸿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性别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性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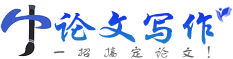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