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里的夏特》
本文是天山里的夏特论文范文数据库和夏特和天山方面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唐荣尧
天山,亚洲之脊,莽莽苍苍的数千公里躯干中,不仅有森林、矿藏、草场,更是容纳了不同族群的人生活于其间.他们在各自生活区域,点燃起一盏盏信仰之灯,构成了一片辉煌.夏特,西天山深处的一条古道,也是天山北麓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的一个柯尔克孜族自治乡的名称,一处中国多元文明的样本.2007年和2014年,我先后两次抵达这里.
古道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古时修就的道路,至今仍被人们所用;二是作古了的道路,亦即被人遗弃,死于人们记忆的路.
古道扮演着两个角色:文明未碰撞之前,古道是一种阻断,是隔开两种文明的栅栏;文明交融的愿望出现后,古道就成了无水之河流上的摆渡,成就着其两端的人们在来往中交流、贸易、结亲或生息.
千百年来,这条以丝绸之名铺呈在大地上的夏特古道,一直闪动着神性的光芒.成就这些光芒的,不仅仅是在来去之间带给沿途城乡的物产,不仅仅是那些身负信仰之薪的传教、求教者,还有不同的文明在来往中扎根于沿途民众的心里,点燃起天堂和大地间的一缕温热.
夏特是一条隐居在西天山中的古道,是连接着北疆伊犁州的昭苏县和南疆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之间的一条旱河,没有河床与码头,但又不乏这样的一些人——领受军命的将士、为了生计奔波于江湖的生意人、传播一捆信仰之火者、肩负一个族落或王朝重大责命的使者——穿梭于其间.
时光的淘洗前,人类的任何一个选项都可能改变古道的命运.
现达的交通工具终结了这条旱河的使命,使之落入被旁落的冷寂境域里.至目下,它或许仅仅是史学家考证某段它发挥过作用的一段证据,或许是探险者挑战自我的一次远行之途.剩下的,就是日益死亡的记忆.我试图通过文字对它给予一场唤醒,这源自于一场新的人文之旅.
从天山南端的温宿县起步,沿着这样一个被遗弃的古老山谷横越天山,意味着我要沿这条被遗弃之道,完成从炎热、干旱的农耕区到凉爽、草盛的北疆游牧区的穿越,完成对两种地理单元下的,一种来自异域的文明如何挤占于古道两侧的辨析与书写.
夏特,因古道角色而成为一条各种游牧部族汇集、混居的文明之河.往者的背影被一场大雪掩埋,来者的脚步往往会驻足于险峻之前.这历史的空档处,就如雪季退去、雨季未至前的季节节点处,徒留下一段尴尬,让夏特的角色,显示在时下中国行政版图上,便被定格为天山北麓一个高原草地乡镇的名字.
对于游牧地区的地名,我天然地有着一种探究心理.诸如塔里木河渗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多浪、蒙古草原腹地的多伦、青藏高原西部边缘的聂拉木,等等.遇上夏特,自然也会产生这样的兴趣.生活在这条古道深处的维吾尔人和蒙古人,对夏特的语指,各有说法.前者的语境中指的是“梯子”或“台阶”;后者的语境中是“草场”的意思,两个语义的背后,是倚重农耕与游牧两个部族的心理所指.前者是指从古道的北端南而行,就是沿着北疆草原和天山之间的大地台阶而上,逐步接近一个个冰川;后者更多是指这里相对于那些高耸云端、常年身披冰雪之衣的冰川而言的碧绿草原.
当地人的口传历史中,唐代著名高僧玄奘西去取经时,曾穿越过这条古道,他在沿天山之北向西而行的足迹至此产生了转向——沿着夏特古道向南穿越天山进入南疆,继续他的求佛之旅.那时,伊斯兰教还没传至这里,他的行旅是孤寂而安宁的.
公元1820年8月,张格尔率数百人,通过夏特古道潜入南疆,煽动当地民众叛乱.清军领队大臣色普徵额率兵进击,将其大部歼灭.张格尔仅率残部二三十人逃往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费尔干纳盆地西部的浩罕地区.在浩罕,殖民者和流窜者达成一项合谋:英国殖民者给张格尔提供装备,组织训练军队;张格尔则想借英国的支持返回新疆,建立他的王国.所以,突围后的张格尔恐驻守北疆的清军通过夏特古道来援助驻守喀什一带的清军,以出卖祖国权益为条件向浩罕求兵,答应如果浩罕地区的军队能帮助他攻破今新疆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田四座城市的话,就将这里的财富、美貌的女子与其共享,并且将喀什割给英国人以作回报.
有了张格尔这样的求助,浩罕的穆罕默德·阿里汗便亲率万人入侵南疆,攻打喀什,驻守在这里的清军开始近两个多月的艰难守城.那本是喀什瓜果飘香的季节,本是当地人民在秋日的收获中享受劳作果实的季节.然而,那时的喀什天空被血抹红.最终,喀什失守,指挥那场保卫战的参赞大臣庆祥,始终在前线和将士一道血战,喀什失守的时刻,他选择了自杀殉国.夏特古道上,造成南北疆混乱的张格尔及跟随他的叛军,给中国历史留下了如此一笔.
这条古道,在清代有了一个蒙语称呼——沙图阿满台.“沙图阿满”蒙语意为“台阶”,“台”意为“有”,合在一起则为“有台阶的山谷”.逐渐,人们将其简化音译夏台、夏特、夏塔等.
我无意像个旅游者去叙说从南至北的穿越夏特古道的艰难,因为那些艰辛和我探访夏特古道里的穆斯林生活无关.站在整个夏特古道的最高处——西天山的哈达木孜达坂和木扎特冰川下时,我看到了南北疆的一个高界点,从这里继续北行,就进入伊犁州的地界了.劈开达坂的窄路上,千百年来,穿越于这条古道上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回族等穆斯林,就是一股连接西部新疆南北的生息之力;他们的背影给孤寂的古道添加了一丝生机,他们的生活习俗构成了古道上神秘而艰险的风情,他们的来往穿梭构成了这条古道在伊斯兰文明传播于南北疆之间的地位.一次次灾年后的流民、一个个身负传播信仰之命的阿訇、一次次引起战乱或平定战乱的兵士、一个个带着养家糊口之责的商旅、一个个跟随着牛羊或马匹牧食足迹后穿越古道的牧民,等等.来与往之间,往往是生与死之间、贫与富之间、贱与贵之间,从容也好、匆促也好,就这么写就一部低调的、没有几个读者的历史书卷.
就此而言,我对夏特的亲近与穿越,是为了探究生活在这里的穆斯林积淀的民族风情.我眼中的夏特就没了旅游景点的角色,而是一幅流动的人文画卷,一卷被不停翻阅、修缮的精神大书.
虽然是夏天,但山顶上的积雪依然是一片巨大的纯净之白,远远地就能感受到那股高傲的冷来,没有充足的长旅,是无法走近这股冰冷中的尊贵的.冰川和积雪是夏特河之源,翻越达坂后,沿着夏特河而行,目睹一条河流由小溪变成汤汤之水,见证了从三千七百八十米的木扎尔特达坂到二千多米山谷的地理变化.然而,那暗潜在这山和水之间的历史,需要慢慢走近.
夏特乡因夏特古道而得名,真正使它具备一定内涵的是它的民族特色.从南疆穿越夏特古道,一过分水岭,迎接古道穿越者的便是夏特乡的辖区,乡政府位于昭苏县城西南七十余公里处,柯尔克孜人占全乡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夏特却是一个柯尔克孜民族乡.
进入二十一世纪,政府实施牧民定居工程,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等高山游牧部族陆续告别天山深处的游牧生活.乡政府所在地的人气就越来越旺,定居者越来越多.不由让我想起“小镇如巢,众鸟来栖”——著名作家张承志用八个字给夏特如此定义.巢不大,但众鸟纷飞,甚至鸿鹄来兮.有张承志这样的作家,更有不同民族的行旅、游客、探险者,将各自匆促的背影和容色留在这里.
镇子里的那两条街道划隔出的一个个家庭,集中修建的乡一级政府的构成单位,商人们率先建起来的店铺,等等,无言地收留这里的居民或过客.张承志在《夏台之恋》中这样描写:“从正东和正西方面溪水一样汇来的东干人(回族)、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塔尔人,骑着毛驴从南疆翻山而来的、后来名称为维吾尔的耕种人(张承志先生说他们被游牧民族的牧人们称为塔兰其,即农民.其实,在晚清时期,塔兰其也是高山游牧部族或东干人对伊犁绿洲一带耕种的维吾尔人的称呼).”
来与去之间,不是一个背影的轻轻转动,而是生计变化引领出的幸福抑或悲楚.定居下来者,自然带着一份对这里的欢喜甚至感恩,慢慢地呼朋唤友,让夏特的巢内充满更多的内容,而离开者自然带着些许无法适应这里的无奈,将当初来这里的所有美好愿望及在这里的生活回忆,沉沉地叠进简单的行囊里,自然也就叠进了后来忆起、聊起夏特时的一份苦涩里.留下者也好,离开者也好,他们的语言、笑声、哀愁,被夏特的风吹走了多少?收容了多少?两下相抵后的结果,就如这里的穆斯林女性的面纱朦胧而含蓄,背后便是汇集在这里的不同穆斯林民族之间,穆斯林的各族和汉族、俄罗斯族之间交往的风情.最能体现这种风情的,应该算是这里的学校了.这儿的小学同时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以及汉语四种语言,每个小孩子随便能用这四种语言交流,汉族的学生能用哈萨克语和蒙古族学生交流,维吾尔族的家长能用哈萨克语和教师交流,甚至还有上年纪的牧民能用俄罗斯语唱歌.因此,那两条横贯小镇的街道上,当地人相遇了,这个用维吾尔语向对方打招呼,没准对方会用哈萨克语回复;两个当地人在街角交谈时,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维吾尔语,一会儿可能就变成了蒙古语或俄语.
晚清时期避乱的陕甘回民、盛世才时期为了击退马仲英部队邀请进疆的哥萨克骑兵与白俄战士、从放弃伊犁绿洲上的农业来这里贸易的维吾尔族人、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远征时来到天山下的蒙古族将士后裔、以原居民脸孔亮相的哈萨克和柯尔克孜人、镇政府机关汉族干部、边防派出所工作的汉族,等等.面容、语言、风俗、信仰不同者,就像一艘艘形制、大小不一的舰船,或早或晚,或东或西,或张扬或低调地汇集在了夏特的港湾.那西天山的一抹绿色海洋里,游弋的船只,文明各异.
天山脚下,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夏凉冬冷,当地的牧民在这冷凉之间便完成着千年来沿袭的转场生活——夏天去山上的牧场放牧,冬天到低海拔处过冬.在他们的概念中,一年似乎没有春天和秋天.
在昭苏这样的边境地区,设置的边防派出所常常被民众称为“二政府”,既有维护边地安宁的角色,也扮演着内地常见的派出所角色.来这里工作的,时间长了,自然就成了当地的百科全书.我走进派出所,是为了特意拜见夏特柯尔克孜民族乡边防派出所副所长李建民,他曾经获得“全国优秀人民”称号,和他交谈中,发现他简直就是一部夏特词典.得知我想了解夏特乡的穆斯林,他给我介绍道,夏特的柯尔克孜人主要生活在牧区的达尔吉村和农区的喀塔尔托别村,这两个村里有柯尔克孜人建的两座规模很小的清真寺.全乡境内,哈萨克穆斯林有一个小的清真寺,维吾尔族人有五个清真寺.
逆着夏特河,沿废弃了的夏特古道,往天山深处去,我的目的是找故事,关于生活在这里的穆斯林的故事.
一片平缓的高山草甸上,零星地散落着几个小木屋,在皑皑白雪中显得很醒目.这个叫温泉的地方,当地政府和投资者虽然按照景点的角色定义,但毕竟因为太偏远而没什么游客.
远处的山坡上,一座敖包无言地告诉我,这里有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族.在边防派出所时,李建民就告诉我,整个夏特乡有一千多名蒙古族人,他们散落在全乡境内.生活在这里的巴特尔一家,是夏特古道内唯一的一户蒙古族人家,他的使命仿佛是守护那座敖包.他还有两个不同民族的邻居:哈萨克人热孜宛一家和柯尔克孜人热西普一家.三户人家的孩子在夏天已经见惯了来这里的内地游人.因此,对我的到来并没表示出太多惊讶.
三户当地“土著“的房子都是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松木搭建的,结构基本相似,但巴特尔家中的墙壁上挂着成吉思汗画像,另外两户人家因为信仰伊斯兰教而没挂任何图画.巴特尔的女儿图雅尔丽曾因为在夏特乡汉语学校读过书,而成为这里的“女秀才”,一般在假期从外面来的采风者、摄影师等都喜欢找她交谈.随着旅游开发,巴特尔和热孜宛将各自的牧场划出来一点,用于旅游开发.夏天,从山下雇来服务员帮着打理这个小小的旅游景点,深秋,整个景区就进入了“冬眠期”.大雪封山后,几乎就没有人来这里.即便是李建民这样的边防,也是10月份时骑马才来过一趟.
虽然信仰不同,三户人家一直都和睦相处,从没有发生过宗教或生活上的冲突.热孜宛和热西普这两家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图景是这样的:夏天,他们进山放牧,随时带着一个小的拜毯,上面织着清真寺的图案,到礼拜时间,他们就拿出拜毯,面向西进行礼拜.冬天,他们多在房子里,枯死的松木枝被他们点燃后用来取暖,房子里的温暖和外面的酷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礼拜就在房子里进行!开斋节或古尔邦节时,如果能放得下手头的事情,他们会下山,到镇上的清真寺去做礼拜,那是他们一年中最隆重的时分.
三十七岁时的热西普承包了半面山坡的夏特乡牧场,进行围栏养鹿,这种养鹿生活持续了十多年.养鹿让他家生活越来越富足,我去时,他家正在盖一幢二层楼.望着郁郁葱葱的天山,我想象着林木深处的鹿是怎样生活的?便联系给热西普家养鹿的雇工祖努素,这个柯尔克孜男人友好地骑上他的摩托车,答应带我去看.开始,还有点羊肠小道,摩托车沿着模糊的路迹时快时慢地行驶,后来就根本看不见路了,他却骑速越来越快地向上骑行,从二档调成一档.山坡的陡度越来越大,让我感觉到摩托车随时都能仰翻,自然间便更紧地搂着他的腰.这似乎更加刺激了这位游牧血统的柯尔克孜族男人,不停地轰着摩托车的油门.到了一个山顶,接着便是坡度更大的下山路途,按照我在内地骑摩托车的经历,这样的坡度不能骑行的,便提出不再前往.
还没等我说完,只见他狡黠地冲我一笑后,猛地一踩油门,车便像离弦之箭向山底冲去,转眼间到了半山腰.他依然没减速地行驶,我的感觉是摩托车的刹车失灵了,在一种深深的恐惧中,我一声尖叫,向旁边的坡地上飞身而去,跌倒在山坡上.而这一动作无疑会加剧车速,只见他的车在一种貌似失控的状态中,向山谷冲去.到谷地,他调转车头,调好档位,加大油门,车在没路的状态下,在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的“S”形路迹中,向上爬行而来.
这时,我清楚,山上没路,但在他的心里是有路的.到我身边时,他开玩笑地说:“你的嘛,这个!”与之相伴的是他伸出右手的小拇指.我这才明白,他是完全能控制车辆的,我眼中的危险,对他来说就不是什么问题.于是,重新坐上他的摩托车,往天山深处而去.
沿着西天山脚下的夏特河道边的山间小道继续而行,坑坑洼洼的山路,有的地方几乎就没有路,车速连一辆自行车的速度都达不到.随着夏特古道上的海拔升高,也逐渐体会到维吾尔语中称夏特为“梯子”的含义.
当年,张承志先生来到这里采风,离开时却模糊了那家柯尔克孜族人的姓名,他以此抱憾.这次我替他找到了,其实,姓名不重要,在夏特,我遇见的柯尔克孜人似乎都是那个人的化身——热情、淳朴;热西普和其他地区的柯尔克孜人一样,喜欢穿红色的衣服,戴红色的帽子,即便是他家人的服饰、家中的民族手工艺品等,也多用红色装饰.这和他的邻居哈萨克人热孜宛家有很大区别.
几十年前,张承志来到这里时的身份是一名考古者,考古队员和兵团的战士前去哈萨克人家做客时,“会在毡房门口先把特意准备好的水果糖和饼干分给小孩们,然后才弯腰进门.他们全懂得用水壶洗手三遍,而绝对不会洗后甩手上的水滴”.几十年后,在一个伪旅行的年代,那些前来的旅行者、探险者失去了对牧民们的尊敬心,失去了该有的礼貌,而牧民们则在享受这些人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着那些人的傲慢和无礼.更为遗憾的是,张承志在这里当年听到的哈萨克民歌《Akbulak》(白泉),会唱的人几乎没了,牧民尤其是年轻人更多喜欢在MP3带来的流行音乐中,远离着民族古老的心声.如我一样外来的、对游牧文化心怀敬重的人,还能体会到身心被从民族精神内核处走来的音乐所征服的感觉吗?哪里能聆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而不是为了应付游客所弹奏的冬不拉的真谛呢?哪里能喝到带着民族本色和精神内质的奶茶呢?
虽然伊斯兰教不允许偶像崇拜,但在伊斯兰教进入中国之前,生活在新疆的民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图腾,比如:维吾尔族人尊崇狼,塔吉克族人推崇鹰.这种图腾崇拜就慢慢地延续了下来,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别的地区的标志.用金鹰捕猎是哈萨克族的古老传统,当这种传统上升到图腾的席位时,金雕崇拜就成了哈萨克人的一个民族标识.像鄂温克族的驯鹿、蒙古族的驯马一样,哈萨克人是将驯鹰视为传统的.今天,在哈萨克斯坦的国旗上还高挂有一只金雕.而在整个天山北麓的哈萨克人的集市上,木刻的鹰、树脂做的鹰甚至真的鹰的标本,无声地传续着这个民族的心理.
“一匹好马难换一只好雕”,“一只金雕的价值比一个姑娘的嫁妆还要高”.从这些哈萨克族民谚中,不难看出这个民族对金雕的尊崇程度.
鹰猎是这个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它流淌在每个哈萨克族男人的血液里.张承志当年在夏特所见到的那个“身躯雄大、肩上架着鹰,跨着一匹枣红大马的哈萨克老人”根本见不到了.猎鹰这一传统项目正在逐渐远离着这里的哈萨克族人,枣红大马也被摩托车、小汽车替代了,悠长的牧歌被随身带的MP3取代,浓香的奶茶被速溶咖啡取代.只有在传统的节日里,在山里的牧区,才能看见那些秉承远古哈萨克人马背传统的骑马牧民.
放下茶杯,在热孜宛的家里,我随意地走动着,打量着,他的妻子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依然用缝纫机缝补衣服,依然保持着挤牛奶、做奶酪的哈萨克族人生活习俗.
三户人家虽然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但饮食基本相同,一日三餐,除早餐为馕和茶或奶茶外,中餐和晚餐多以面食、马、牛、羊肉为主;遇上重要的节日了,大家互相送去祝福.虽然和热孜宛同样信奉伊斯兰教,但在热西普的心里,最隆重的节日还有柯尔克孜族的诺若孜节.按柯尔克孜族的历法,新月每出现一次为一个月,十二个月为一年.每年第一个月出现时即过诺若孜节,这个节日和巴特尔心中的春节、热孜宛心中的古尔邦节一样隆重.那天,他的妻子会拿出用小麦、青稞等七种以上的粮食做成的一种名为“克缺”的食品,预祝在新的一年里饭食丰盛.
灰白的炊烟带着这里穆斯林的生活气息袅袅升起,里面混杂着隐约的奶茶香.在夏特的日子里,我虽然饱尝了这种用极浓的茶、盐、鲜奶和奶皮子兑好的,带有浓郁的游牧穆斯林风情的饮品,但放下茶碗的刹那,禁不住胃里抽搐了一下,喉结忍不住动了一下,心里为再也喝不到这片草场上的奶茶而惋惜了一下,仿佛听见自己的内心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叹息!
海拔越来越高,夏特河越来越细瘦,连合适摩托车骑行的路也没了.就在这样的地方,一个我见过的最奇特的建筑出现了.从外表看,那是一座很普通的黄泥小屋,想必是穿越夏特古道的人,为第二天穿越冰达坂时留宿这里时抵御风寒,随意搭建了这么一座普通的房子;为了第二天能够顺利穿越达坂,他们便拿出小拜毯,面向西方,在地面上跪了下来,祈祷一份平安能够降临.时间久了,往返夏特古道的穆斯林将这种习俗逐渐演变为一种常态的功课,这座小屋逐渐就扮演起了一座清真寺的功能.如今,随着旅游开发的力度加大,小屋周围建起了不少房子.这座小屋也被当地的穆斯林自发保护起来,成了一处仅供参观的场所.
有了这样功能的小屋,有了这些信仰的人群,古道内唯一的阿訇自然就出现了.他和其他牧民一样,是以放牧、打草为生.他是开着破旧的二手车来的,他也是为了信仰而来的!阿訇微笑着在那一炉火旁,勾勒出了一幅这里的穆斯林的宗教生活画面:平时,他们分散放牧、养蜂,在景点内打工,只有到主麻聚礼日时相聚在一起.先是到后面的河水中洗小净,然后神情肃穆地在阿訇的带领下礼拜,听阿訇用哈萨克语解读《古兰经》.在黄泥小屋里,阿訇是传教者、领礼者,是神圣且肃穆的.走出清真寺,阿訇也和普通哈萨克牧民一样,会用长镰刀割草、会骑着马去放牧,看起来和其他牧民没什么区别.
再往前走,摩托车也无法发挥功效了,得靠骑马而行.在这样的古道高地,马群出现了!是横越于西天山古道间的伊犁马.牧马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穆斯林,年年在卖马季节里会享受到伊犁马带给他们的快乐和痛苦.前者是买卖后的金钱进入腰包,后者则是他们对曾经陪伴自己的这些马的情感.他们赶着马行进在古道上或山里的牧场上时,高声唱歌、豪情万丈.一旦马的买卖完成,他们的眼圈红了,嗓子沙哑了,抚摸马鬃的动作越来越慢了,看着这些伴随着自己或长或短的马被运往陌生的远方,他们的心情沉重了起来.
夏特古道是神秘的,也是深邃的.这不仅表现其辽阔的身躯中存纳了诸多的动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也包容了一个个从不同渠道、不同方向进入这里的族群.他们途经夏特古道,穿梭于南北疆的路途远近不同,来这里的心理和所领受的风霜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天山以它的冷峻面孔和恶劣的气候会让这些人到这里时,抖落一路疲惫,他们毕竟是以陌生的闯入者的身份来到,还得面对土著居民的态度.张承志在他的《夏台之恋》中如此写道:“回民进入这里的路是最秘密和最艰难的.谁也不知道那些粗悍的甘肃、宁夏、青海的农民是怎样来到这里的.他们不向外人随便讲自己的事,当然,除了别有用心的人和他们内部的人以外,也没有人关心过他们.我遵守这种人心的禁忌,从不多问,直到很久之后.”
那些悄然而至的回民,显然是一群陌生的闯入者.最初的一支是清代同治年间,内地回民起义失败后来到这里的.有的是流放者,有的是盲流者,有的是为躲避追杀而隐姓埋名至此的.他们完全凭着内心坚定的信仰——相信离开故土也是命运的安排,前往的陌生领域一定会有真主安排好的命运,而翻越冰山时遭遇到生命之危时,他们同样会依靠内心里一次次升涌起的信仰之火来温暖自己.没有一张可靠实用的地图,没有沿途可靠的信息安慰,有的只是对未知的前方甚或明天的憧憬.
我只能想象百年前的那些场景:那些回民在离开农耕经济区后,来到这片陌生的生活氛围里,在一片毡房中搭建起了自己的黄泥小屋.他们没有马和牛羊可牧,或许在内心深处也不愿意去放牧,但他们走进逐步升高的西天山古道中,发现了一项令当地牧民吃惊的维持生计的活儿——挖贝母.在天山的草药香味中,一顶顶白色的回民小帽闪现在草场或林地中,开始是靠挖贝母赚取一点生计费用,后来成了富足生活的保障.贝母,在他们的手中演绎了从救命草到致富宝的转变.
有了贝母,有了精准地来往于夏特古道间进行这里南北疆间的生意,他们就有了在夏特古道乃至天山的生存之本.他们互相帮衬着,一间土房子一旦建成,就会有两座、三座,乃至更多的泥屋,出现在这片千百年来滋养毡房的土地上.生存一旦解决,他们内心的信仰升腾而起,回民的清真寺和他们的礼拜生活逐渐在这里生根,在天山的视野里立下了脚.他们的黄泥小屋和清真寺开始遍布在这条古道的视线中,完成了在两百年的光阴里建成了另一个“故乡”的功课.
海拔三千米的卡拉房子是古道中的一处地名,是清代遗留下来的一个军营.住着的唯一一户居民是柯尔克孜族的达尔其拜,他在秋末时就将过冬需要的粮食、清油、蔬菜等必需品拉到山上了,他就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及妻子开始“窝冬”.这个时候,他也才能在一年中难得的清闲里,去不远处的蒙古族、哈萨克族的邻居家里,转门、聊天,最重要的是,马上要过春节了,他要给蒙古族的邻居送一只羊过去表示节日祝贺,而他也在春节那天去邻居家做客,共同感受春节带来的喜庆.
离开卡拉房子再要往南而行,就进入西天山的腹地了,这也标志着再往前走就进入无人区了.李建民他们负责的边防巡逻范围也到这里就画上句号了,也就是说,这里是北疆穆斯林在西天山地区最南端的居民了.
天山里的夏特论文参考资料:
此文汇总:此文是关于对写作夏特和天山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天山里的夏特本科毕业论文天山里的夏特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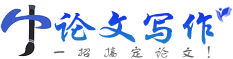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