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地图上画出我》
本文是关于地图类论文范本和地图类论文范文。
停电时,有街上的光出现在眼前,晃着房子里简陋的家具,这样,电线是否断掉就不是问题,至少,在那光里,我听到呼吸声像蠕虫一般伸缩,蜷在床上,我的呼吸声与那光差不多的若隐若现.房子,低矮,临时搭建的棚屋,在运河的浅岸上,一边是干涸的河床,另一边是喧嚣的公路.电线吊在半空中,风稍微大一点,把它荡起又折断.这种情况,多半在晚上发生.白天,大家都到工地上去干活,晚上休息时,有人真的钻到梦里,有人走上公路,走上一大截路去小饭铺喝上几瓶,也有人立在寒风里等着那些专门等他们的女人们走上前来.
在这个城市,父亲和我已经辗转了几个工地,从市中心到郊县,有多少房子竖立起来后,我们就转移驻地,我已经记不清了.这个城市特别大,需要建造的房子特别多,男人、也特别多.刚到这个城市时,父亲并不需要我去工地跟他一样做活.当初,他还隐约记得我的年龄,他说,再去读书吧.我点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我也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借读费很多,这个城市的借读费更多,父亲拍拍我肩膀,犹豫地说,不读了怎么样,你的个子快跟我一样高了.我的喉结没你大,我的胡须没你硬,我的力气也没你大,我心想着这些话,并没有说出口.我推开他的手说,不读书我做什么呢.父亲说,跟我一起上工地.我想了想,没有拒绝.工头不同意,他对父亲说,这个岁数还属于童工呢,被发现了优质工地的称号就保不住了……工头向父亲推荐了一家专门为打工者子女开办的学校,不需要任何学费.第二天,我就去那里上学了.
在那儿,我的个头是最高的,比我稍微小一点的学生都是女的,她们经常主动来找我借东西,有没有黑色的笔?有没有能折成纸鹤的纸?我摇头.她们磕瓜子,她们说看他,很挺的鼻子,很清的眼神,很高的个子,但他好像不喜欢我们,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还没有开窍么.她们发出类似擤鼻子的声音.学校的授课并不正规,不同年龄的学生们坐在一个大教室里,老师的讲课不能引起我的任何兴趣,有很多课的内容我早已在别的学校学过,似乎没有继续呆下去的必要,但不呆在学校里,我又能去哪儿做些什么呢?我在课堂上打盹.学校的房子很不结实,起沙尘暴时,沙子从窗户进到房子里,在课桌上铺开,进入我的鼻子与眼睛里,用手指揉眼睛,有泪水流出来,我像是在哭.抬头看窗外,风把树枝折拧,把几块木板吹向半空,不时又摁下地,又掀起来.天空土,大地灰黑色,没人在风里走,汽车停在公路边,像一座座窑洞.
老师走过来敲我的桌子说,你在开小差吗?校长为了让你们有个地方不受歧视地读书有多难你知道吗?为什么不珍惜呢!我木然地看着他,一句话都不说.老师走回讲堂,激动地在黑板上写下“珍惜”二字,然后走进沙尘暴,瞬间,黄沙淹没了他.我确信他只是走入隔壁的教室去上另外一堂课了,但是,他的身体消失在门缝里的瞬间,我看见他一只脚跨入风的旋涡内便一步跨到了天上.第二天上午,他还是继续来上课,但什么都没有讲出来,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很多人都茫然无措,年龄小的孩子哭了起来.我大概是发出了一种笑声,很轻,却还是被周围的人注意到了.他们看着我,目光里有菜刀上的凶气.我站起来,离开了教室.那个坏消息是校长在昨天的沙尘暴里被一截树枝砸成重伤,她的妹妹,校长的助理,一直以来反对她办学校的妹妹,宣布学校关闭.她要带她回老家养病,等她病好了她要与她一同做茶叶生意挣钱.
教室的门在我身后合上,我把里面人们的唏嘘抛下了.学校在城市的五环边,在我和父亲的住处与城市之间,但我在风里弄错了方向,从五环走向四环、三环、二环,一直走到了城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走到时,天已经黑了.偌大的广场上除了跟石碑一样坚硬的哨兵外没有任何人,路灯雪亮,风小了,我的肚子咕咕叫,泪水不停地流下来.我从来没有流过那么多眼泪,我几乎担心眼睛会瞎掉.为了镇定自己,我开始回忆这个城市的样子.刚来这个城市时,父亲和我,还有工友们在地铁里买了一张地图,我记得它的形状,像一张嵌了几个圆圈的大面饼,那圆圈是什么做的?是麻油,是芝麻酱,还是红糖?现在,我就在最里面的一个圆圈里,像在一波涟漪的中心,当四周的水波散开我便会在这儿沉溺下去.我找到两堵墙的一个夹角,靠着坐下,累得挪不动腿,不知不觉地,我歪在地上睡着了.再睁开眼时,周围是一些早起的游客与几个穿得很体面的乞丐,广场上的旗已经升起来了,风完全停止了,几朵云挂在建筑物的屋顶上.真是清晰的早上,我伸了个懒腰,猛吞了几口空气后,决定走回父亲和我的住处.
路线在地图上是清晰的,在我的脚下却那么逶迤,像蛇扭着腰围拢它的食物,而它的食物庞大笨拙又看不清危险在对方脸上制造的惊吓.走着走着,我突然想到我可以描绘一张地图,地理课上我学过那种画线的方法与制图的比例尺,也学过画出高气压与低气压的图像.画一张高气压下的沙尘暴天气的城市地图,除了高耸的房屋、错综复杂的马路与悬梯般的天桥外,还要有一条从五环外直接抵达城市中心的路径.那道路必然笔直、粗野又凶悍,又隐含着温柔、羞怯与生涩.
一边走,一边琢磨着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绘制这张地图,我的脚下像装了轮子,不由自主地转着.用精密的方法去绘制,可以让人看到城市的全貌,却无法展现我所希望的那条路径所包含的气质.而用蜡笔、水粉等美术的手法,或许可以达到我所需要的效果,却违背了科学制图的原则,这样画好的地图,如果是份作业,更该交付美术课堂.有没有第三种方式呢,既精密地符合地理,又能表现那条路径向城市中心插入时的凶蛮、强横以及其中令人难以看到的含蓄呢?思前想后,不得要领.
靠着对一张有可能被描绘出来的地图的向往,我终于走到了父亲和我的住处.
父亲正在煮面.
没有去工地?我问.
关了.父亲说.
烂尾楼了?我问.
父亲呼哧呼哧地吸面条,没有回答我.
我去取碗.
只是一个人的面.你再煮吧.父亲说.
不了.我想睡觉.我一赌气,放下碗,爬上高低铺的上铺.
脑袋一碰到枕头,我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迷迷糊糊地,我被下铺父亲床上一阵女人的粗重喘气声吵醒了.我用力晃了一下床栏.
醒了?父亲问.
嗯.我继续晃铁床.
饿了就煮面条吃.父亲说.他床上有一个人走了出来,走向门,一声不吭地开门出去.
我下床煮面,面条从水中浮起时,父亲发出了响亮的鼾声.
我知道刚敢于出去的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不用付钱的相好.如果需要付钱,父亲就不会呆在家里了,他会去火车站或窄小的胡同里踅摸.在每个城市他都是这样.
父亲白天上工,和水泥、砌砖头、贴瓷砖,后来因为事故腿瘸了,做过一阵子厨子,做厨子后身体胖了,有了赘肉,他开始乱花钱了:抽烟、买衣服与喝酒.施工队里的老乡们开始来找他借钱,他有求必应,他说反正我老婆也死了,父母也死了,就养活大家的父母老婆吧.他的大方招人喜欢,大家真的喜欢上他了一样,仿佛离不开他了一样.他越来越空闲,总是有人替他干活,工头发现了这一点,就调他到办公室算账.他对那些数字一头雾水,拿回家给我,说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让我替他算那些数字.
有我帮他算账后,他有了更多的空闲,在家里闲不住,就到工地上干老本行,帮这个做点事,帮那个做点事,吹吹牛,“以前,我砌出来的墙那是真的直线”“以前,我跳远可以从这棵树跳到另一棵树”.这样,他还是有很多空闲,他空闲时总不呆在房子里.有一天,我跟着他出了门.我跟着他走到一个有很多女人的地方就回来了.有时,他也把女人带回来,有时避着我,有时也不回避,他说,你也是个男人.但他又怀疑我究竟是不是个男人.你的喉结怎么不像我那么显呢?喝醉时,他说,你不是我儿子,你是你妈跟野男人生的吧?我一年四季在外做活,怎么知道她肚子的种是我播的呢.我说,奶奶说我妈生我死掉那会儿,你一滴眼泪也没有.你为什么不哭?你是不是我爹?他说,老子不喜欢哭.我说,那你死掉时我也不哭.他大笑说,好,这点才像老子.死就死,哭个啥.
男人和女人都喜欢父亲.想到这个我总是忍不住笑起来.女人来到低矮的房子见父亲,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我在上铺脑子里一片空白,身体好像不在床上.女人走后,父亲睡觉.有时,女人来时我会出门去溜达.有时,在空旷的野地里走着走着,我的小蛇会探出来,越来越坚硬,我呆呆地看着它自己在那里探头;有时,我站着一动不动,稍稍收紧小腹肌肉,看它一点点地左右晃动.这时,我并不是一个男性或者少年,我是一架机器,小蛇的摆动纯属活塞运动的前奏,而我并不需要前奏之后的开始.父亲说,只有那样了,才有方向,才有一个新天地.我不以为然.我的小蛇,它的主人不急于寻找出口,他似乎总不迷路,即使到了再陌生的地方,走着走着,都会走到一个新的地方,也能从不同的道路回到老地方.
也有例外.睡梦里,我会失去白日的平静,小蛇会变成大蟒,搅出汹涌的海浪,我总是蓬勃而出,在被子床单上留下身体的分泌物.我知道这只是一种普通的生理现象,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喜欢上了什么人,或者我应该去喜欢什么人.至多,它的出现说明,我跟别的男性与少年没什么不一样.这种现象第一次出现时,我一点儿也不慌张,很平静地接受了汹涌后的那种黏稠度,它像糨糊一般,将一个醒着的我和另一个睡着的我粘在一起.那种释放会伴随着一丝稍纵即逝的轻松,我似乎从不记得它曾经存在过.父亲问我,你是不是一个男人?我说,无所谓,是不是都行.父亲轻蔑地哼了一声,不再理我.过了很久,父亲还是会开口跟我说话,因为我是不会主动对他说点什么的.我可以长久地一个人呆着不说话,这一点,他做不到,他需要房子里有一个人,不是我就是女人,或者,他可以去工地上和工友们呆着.有时,我厌恶他身上用不完的力气,用来发问、大笑、与吃喝.当他发力时,我有点儿厌恶他,仿佛他的力气破坏了我的平静,而我独自沉默时,总是很舒服,脑子里什么念头也没有,身体轻飘飘的,仿佛在云层里,又仿佛并不在那儿,甚至不在任何一个地方.这是因为我长期睡在上铺的缘故吗?还是什么呢?偶尔,我散步时会琢磨一下.
一天晚上,毫无征兆,父亲宣布自己终有一天会快活地死掉,并且什么钱也不会留给我.他说,死就死了,非常简单的一件事.“你不需要给我送葬,我也不会再管你了.”他的话似乎是要把我赶出家——如果那房子是家的话.事实上,他没有赶的动作,却气焰高涨,他说他终于想通了,人是没有什么出路的,除非能比死神更嚣张地去面对死亡这件事.他喋喋不休,简直让我没有办法再在那个房子里安静地呆下去.房子只有几个平米大,除了一张高低铺,一张折叠的饭桌、两张椅子、一个塑料的简易衣柜外别无他物.
我实在呆不住了.我离开房子,从工地所在的郊区往城里走.工地上的楼已经没人干活了,工友们都回了老家,马上就要过年了,他们得吃过年夜饭后再回城市里来.建了一半的楼空空荡荡的,像站在旷野里的一个瞎眼巨人,因为他眼里无光,人们也看不到他.运河在楼的一侧,楼的另一侧是公路,公路边上是建筑工人住的低矮工棚.只有一间房子亮着灯,那是父亲和我的住处.我远远地看了看那灯光,继续赶路.
黑夜,修路工人在公路上围起一截截路障,柏油正重新填平破损坑洼的路面.他们的表情很模糊,低垂的帽檐遮盖了半截面孔.有警车与救护车呼啸而过,那迅速的声音闪过耳边时,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是一种缓慢的爬行动物,速度慢得几乎是静止的,但与一种快速运转的机械擦肩而过时,我分明是在以接近光的速度前进,像一粒灰尘被裹在光里,快得看上去一动不动.似乎一动不动的,我又来到城里.早上的城市特别忙碌拥挤.我跟着一个乞丐到了地铁,他存钱的罐子里伸出一张皱巴巴的钱,我轻轻一拉,它便到了我手里,乞丐没有发觉.用这钱买了张地铁票,过了几站后,我跟着一个头发染成的中年男人下了车.他在读一本书,关于时间的书,作者是爱因斯坦,书页上有关于虫洞的图,我盯着他的书看,一直看,直到他的脚跨出车门,把书合上.我跟在他后面,跟得快了点,他猛地回头,我差点撞上他的脸.你要做什么?他问.我迟疑地伸出手去,他从裤兜里拿出一张钱递给我,我摇摇头,手指着他夹在腋下的书.你要这个?他问.我点头.他把书递给我.我接住,他又抽了回去.哦,刚买的,还没有读完,读完再给你.他说着,转身走了.我跟着他.
出了地铁口,他走入一栋高楼,进了电梯,我也进了电梯.电梯升到十三层,他打开一个房间进去,我跟着他进去.房间里有两张面对面的办公桌,他在一边坐下.我在另一边坐下.他把书放到我面前,自己开始打电话.我读书,翻了几页,晦涩的文字让我很难顺利读下去,碰到问题时,我问他,他有时轻快地回答我,有时有点儿犹豫;犹豫时他对我说,“你再往下看看”或“我也不太清楚”,另一些时候,他非常严肃地说,“理论物理挺难的,不是那么容易学”.不论他说什么,我对这本书的确着了迷,一个劲儿地往下读.他打电话的间隙,整理文件,写下几页东西.我一直读书,吃了他递给我的一只面包,一块黑色的巧克力,还抽了一根他递过来的,我并不会抽烟,咳嗽了,出于尊重,我把烟抽完了,有了一个感受:巧克力与都特别容易让脑子更清醒,读书更快.
不过,因为昨晚几乎没睡觉,后来我还是趴在桌子上打起了盹.某个瞬间,他叫醒了我.他说,下班了,你回家吧.我说,没有家.他问,有住的地方吗?我说,那里爹要用.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一个问号正穿过我与他相隔的短短距离,飘到我的脑袋后面去,而他并不需要这个问号的确切答案.他打开门,把那本书放进他的皮包,做了一个请的动作,我在他的目光中走出办公室的门.在楼下,我抬起头,才看到大门口悬挂着的门匾上写着的字“地图出版社”,脚底仿佛生出了植物的根茎,与地面粘合动不了了,直到他出现在大门口.
我要画张地图.我对他说.
什么地图?他问,城市地图、概念地图,还是游戏地图?
不知道,都可以……我也不太清楚.我说.
他捂着肚子,做了一个大笑的动作,那身体弯曲了一半又返回了原来的姿势,他脸上还是温和的表情.
画好了再来找我.他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画好.我说.
他扭头走向地铁站.我跟上.我抓住他的皮包,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子劲,一口气冲他说了我自己的一些事,母亲生我时难产死了,而父亲是那个样子,学校停办了……我说,我没事做时,就经常走路.我觉得我从不迷路,从郊区走着走着经常走到城市中心,很漫长的路.我想有没有那样一条路,从五环直达城市中心呢.我想画一张地图,图上有这样一条路,很迅速的路.以前,我想,这条路是与大地平行地穿过去,现在,我读了你的书,我有了新的主意,我想或许这条路可以是从空中落下来的,是弧线,但我的确不清楚该怎么画,我自己又该在地图的哪个位置上呢?人需要出现在地图上吗?——好像是需要的,的的确确需要的,而我又实在不清楚怎么在地图上画出我,是画一个正在走路的我呢,还是画一个正在画地图的我?
他惊讶地看着我,这次,他的目光里有小草从冬天的雪里抬头的脆声.
这个地图很难画,出版了也没什么人需要.人们会问,这张地图有什么实际效用呢?我回答不出来.你能回答吗?
他的鞋踢着地上的一颗小石子.
我没想过出版的事.你能教我画吗?我盯着从他脚下溜出来的石子.
我也不知道.他迟疑了片刻,从皮包里取出书,递给我.送给你了,今天我有事,必须得走了.或许你过几天再来找我,你记得住地方吗?
我点点头.他拍了拍我肩膀,快步消失在人群里.
我一只手提起书,让它高于我的头部,好使我抬起头以一个仰角望着它,光线从书的背后包围、扑射开来,使书页的质地具有了一层并非纸质的透明感,像是刚从另一个世界运来的,偶然在这个世界遇到了我,稍作停留,与它对视的一个我似乎变得比较重要起来.书打开的一页,恰好是我在地铁里第一次看到的那一页,页面上有一个虫洞的图.我长时间地盯着它看,看着看着眼珠里浮上细细的盐粒,我的身体似乎正被一股超自然的力量拧成麻花旋转了进去,又不是完全被吸入,因为到了一定程度,我的视线受到了阻碍,图上的洞内似乎有一把黑色的锁,禁止我进入洞的那一头,而我非得有现实中的钥匙才能打开黑色的锁——不是想象中的钥匙,我的直觉告诉我,那没用——我无力地低头,我的脚边是一粒普通的看上去一点儿特殊形状也没有的小石子.叹了口气,我把书卷成筒状,塞到我的裤兜里.
还是往郊区走.天渐渐黑了,我到达工地时,只有闪烁的路灯照出我破了洞的球鞋.远远地往熟悉的房子看了一会儿,那里的灯光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父亲应该在那里,我却不能说服自己回那个房子里去.走近些,门就在眼前,伸手可触,我耳边没有一丝来自房子里的声响,或许,房子里空无一人,父亲并不在那里.可我还是在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后,决定不进去.
我向工地上的大楼走去.大楼二十四层高,十七层以下砌好了墙,十七层以上的部分只是钢筋混凝土的框架,我沿着楼梯往上走.还没有挪走的吊车上的灯将一些微弱的光落在楼梯上,使我不至于每走一步便用脚去探台阶.每走一步,细沙与小石子在鞋下发出碾转声.这样走,走到十七层上,风明显大起来.我停下,坐到地上,我的小腿伸在空中,稍微一个不注意,我的身体便会因失重而栽下去,便会像台机器一样支离破碎,像一只狗般血肉模糊.我往后坐了坐,臀部肌肉不由自主僵硬起来.我想起我小时候在村子里看过的演出,一个演员独自站在草草搭建的舞台上,行头简陋,妆画得粗糙,他应该唱出来,一大段歌词或台词应该从他放松的嘴里吐出来,成为夜空里的彩色肥皂泡,漂浮着涌向观众席,使观众们忘乎所以,兴高采烈,或者,使观众们悲恸哭泣,万分绝望,于是,在那一小段时间里,他与观众们一块儿获得了某种解脱.一个射灯盯着那个演员,像一个圆柱形的笼子套住了他,因为忘词了,因为身体不舒服,因为心不在焉,因为其他人不明了的原因,因为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某种障碍……不管原因究竟是什么,当时,那个演员伫立在舞台上,没有唱出一个字,也没有说出一句话,一会儿后,一阵嘘声把他轰下了台.
风,从身后像一只巨大的手掌般推着我,我不得不屏住呼吸,使自己像一只人形秤砣,原地保持镇定.这时,我对平静的看法有了一点变化.平静,或许没有那么重要,激烈一点,像父亲那种疯劲,或许没有那么糟糕.以前,不论在哪个学校上学,每当老师布置写作文、写周记、写日记时,我总是很抵触,潦草对付,不好好写,有和蔼的老师问我,你为什么不多写一点呢,你写出来的文字很有感觉,可以再写长一点.我回答说,我没有那么多话要说.和蔼的老师劝导说,你要试着表达,多练笔.以后,如果还有机会遇到那么耐心的老师,我可能会非常乐意去写一篇长一点的文章,把怎么想画一张地图,怎么在地铁里遇到送我书的叔叔,这些事情都细细写一下.
好的,好的.我说出声来,就像眼前坐着另一个自己.
楼层里响起“好的,好的”的回声,我以为那是我的回音.但不是,那分明是另一种性别的嗓音.
一个女孩悄无声息地坐到我的身边.
嚼着红薯干,她的目光在我垂下的头上发热.好的什么?她问.
没什么.我说.
递给我一根红薯干,她若无其事地晃荡着空中的两条小腿,风将她宽宽的裤管吹鼓,她像在摇晃两根充气大棒槌.她一点儿也不担心掉下去.
还要吗?她发现了我的紧张,打开背包,倒出许多零食来,饼干、牛肉干、鱿鱼卷、花生……我取了一包已经拆开的饼干吞咽起来.
好的什么?她用我讨厌的方式追问.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反问.
休息啊.你呢?
不知道做什么.坐一下吧.
哈哈,你也离家出走了吗?我离家出走了,一直在走.她浑不吝地说着,躺了下来,头发散在水泥地上,看不清有多长.在她额前,几绺卷发松散地盖住她的眉毛,而眼睛露出来,眼眶上抹了极深的眼线,使眼珠黯淡地沉下去,像两条小船在水中淹没只浮着四条弯曲的船缘.
我的臀部又收紧了,双手撑在大腿的两侧.
我闷闷地嚼着饼干,她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楚.
你不喜欢说话吗?真闷,闷坏了.她嘟囔着,手指扒拉着就近能握到的小石子抛起来,扔到空中.
我可以听你说.我想她可能需要一个听众.
好吧,但你想听什么?总得有个方向吧?
随便.
不行,你必须要确定一个方向.她的声音坚决而快乐.
我喉咙里打了个空嗝,类似哨音的末尾部分.我说,真没什么挑的,随便你说.
一定得你先挑个方向.比如说,小朋友晚上睡觉前会说,妈妈你讲故事给我听好吗?妈妈问,讲什么故事啊.小朋友说,童话.或者,那小朋友会说,恐怖故事.
妈妈一般只讲童话给孩子听,不会讲恐怖故事.我纠正她.
那又比如,你去一家饮料店买喝的,营业员问你,喝什么?这时你必须说出你要喝的饮料的名字,可乐七喜咖啡什么的.现在,我问你想听什么,你也该说个什么大概内容,比如你从哪儿来的,比如你叫什么名字,等等.明白了吗?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看上去,她似乎有些愤怒了.
对峙着沉默了片刻.我把手头的零食推向她,一件件放回她的背包,把背包的拉链拉好.
你喜欢吃什么?她又问.
都还行.我说,其实,这些东西我以前很少吃.
你真……她笑了起来,上身仰起一个弧度,将腿也抬起来,双臂去碰双脚,整个身体悬空,只有腰与臀交接的部位着地.这样持续了两分种,她的呼吸似乎也停止了.两分种后,她又以松弛的姿势躺到地上.
你真太搞笑了.她说.
为什么?我问.
如果你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外星人就好了,我就会教你一些地球上的生活常识,带你四处走走,出各种乌龙事件,你很窘迫,我很逗乐,然后时间过得非常快,终于有一天,你要回你自己的星球去了,你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问句,你问我:你跟我一起吗?可惜你不是,你也没办法说那句话.
我知道,我点头说,我的意思是,我的确不会说那句话.
我会说,再见了,外星人.我补充说.我感到我脸上正显露一种以前少有的安恬微笑.
她哈哈哈大笑,随后翻身,俯卧,双肘支地,从背包里取出一个本子、一支笔与一个小塑料手电筒.
我得记一下,在一栋没有修好的大楼里遇到一个看似傻瓜又看似聪明的小男人.你多大?她问.
不确切知道,17或者19.我说.
她不再追问,似乎已经习惯了我的回答方式.
一个不知是17岁还是19岁的看似傻瓜又看似聪明的男人.她在本子上写下这句话.
你想听听我的日记吗?她扭头问我.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她很兴奋,双腿盘坐,开始念——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每过一阵子,我就会想一想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答案.与其说,非得向自己描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不如向自己展现自己的行动,就是喜欢做什么,做了什么,以后还要做什么.显然,我不喜欢刻板的生活,我喜欢到处走走,喜欢去那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如果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我会莫名其妙地焦虑、烦躁与紧张,晚上会做噩梦,梦到自己被一个可怕的怪物抓走了,自己就要想各种办法从怪物那里逃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所以,我一次次地走啊走啊,就想着可能会遇到跟我差不多的人,然后从怪物那里逃跑起来就比较容易,因为有人会一起逃,就仿佛两个各自逃跑的人是在相互帮着对方一起逃似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谁也没有帮谁,只是从怪物那里各逃各的.
上周,在一家酒吧一个看上去还凑合的男生跟我搭讪,我问他要不要一起逃,他摇头说不要,他说他虽然喜欢我却没有跟我一样会做怪物的梦,所以也没有办法一起逃,不过他强调他非常喜欢做这种梦的女孩——就是我——我很失望,不想再见他了,他却为我的离开哭泣,让我的鼻子也酸酸的.真窝囊.喜欢人很好,不过,喜欢人也真是很麻烦的事情,尤其那个人他还不能跟你呆在同一个梦里.很多时候我只是喜欢跟人呆在一起,至于是否是真的喜欢或者说是他妈的“爱”,都不是那么确定.呆在一起,或者不做,都很好.毕竟,路上,我一个人,而且不得不一个人上路,不然,我的身体里就有一个怪物冲出来让我浑身都难受.那个怪物跟梦里的怪物很像,又不一样.这是病吗?我问流眼泪的他.男孩子流泪,叫人心疼.但他的回答却叫我绝望,他说,你可能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心理障碍.啊!我多么希望,他能告诉我:如果这个世界上这么真实的女孩子都有心理障碍了,那肯定是这个地球病了,因为地球一直好好的,一直跟大自然呆在一起新陈代谢,光合作用,地球什么毛病都没有,所以,你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心理障碍.显然,他不是能说出这种话的人.
她停了,抬头看我.
你自己觉得呢?我问.
不是,肯定不是.我感到很自由,很舒服,明天的事情必须让它成为我所不知道的事情,那样才有意思.而他,只不过是出于软弱,出于想把我留下来的目的才说我有病.那样,他就可以陪我去医院看心理科,用一种怜悯的目光打量我,显示他的心理优越感.你说呢?
我没什么意见.
我使劲想了半天,实在找不到可以像她那样顺溜说出来的东西,但一种怪异的慈祥像一条热毛巾捂在心上.
你的日记写得很好.我说.
对!她合上本子,请我讲讲自己的故事.
生平第一次,我希望自己要在这个城市里住下来,有些变化,未来能拥有更多的故事.
唉,你真不是一个好的聊天伙伴.我来看看.她将脸贴近我,呼出的热气下我的睫毛不由自主地抖动.她将嘴巴努起来,而我低下脑袋,下巴抵到了胸前.
可能,真是一个傻瓜.她站起来.
不说话的话,走走吧.你陪我走一段.不喜欢说话的人往往动起来比较容易.她握住我的手,将我拉了起来.
我们走下大楼,走向公路.她一直握着我的手.有时,她把一个由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的拳头扔向空中,有时把它伸进她的大衣口袋里,有时,她将我的手展开紧紧包裹住她的手.有时,她自言自语,有时,她唱歌.她不再特别要求我说话.公路似乎总是笔直向前,而我觉得它总是在拐弯,我们是在走一条又一条弧线.天空露出一片淡淡的红色时,她拉着我跨出公路,走向一片蒿草地.她松开我的手,躺了下来.我坐了一会儿,看着她的脸,想了一会儿画地图的事情.腰那儿有样东西硌着我,是那本书,我把它从裤袋里取出来,放到脑袋下当枕头,闭上眼睛,我睡着了.一只虫子咬我的眼皮,我伸手赶走了它,却看到我独自一人躺在地上,天光大亮,她不见了,我脑袋下面的书也没有了.
我站了起来……
很多年以前,我在一个清晨的自然光下,瘦得像一根竹子,却站得像一座灯塔,从我鼻子里呼出的气息充满了青草上的潮湿,我的眼神里荡起了露珠向上滚动的节奏,我的脚下似乎踩着可以飞起来的白云——那会儿我有了一个想法:很多年以后,当我经历过更多的生活,我会回忆起一些人在一张地图上的位置变化,怎么在地图上标出我的位置,将不会是一个难题.
在散步、跑步与跳绳中,你更喜欢哪个?
更喜欢不带特别目的、走马观花、随便走走,甚至说不上是一种运动的项目.就是很放松,让人的肢体自然动起来,甚至谈不到一个“动”字,只是随着心脏赋予血液的能量通出去,随性碰上什么就是什么,比如空气、树木、建筑、车辆、行人与每一天偶然发生的天气,那种状态.跑步也很好,但我不是一个勤奋的人,很遗憾.跳绳有点儿叫我忧虑,好像我必须得去着急完成什么事,很抱歉,慵懒有余的我,还没有那个习惯.
为什么会让一个人的故事在地图上展开呢?
标量,小时候很不熟悉也没有概念的词.有了数字概念以后,也不会时时去注意量化的细节,一口气走了多少步路,一个念头花了多短或多长时间……慢慢地,才会注意一些细微之处,比如从躺下到睡着之间是3 分钟或10 分钟,比如一口气可以憋上1 分多钟至2 分钟,比如迟到的平均频率是多少,比如别的.我是指,混沌之轻易,亦如风之自然,却不使人对清醒有庆幸之感,而清醒的觉知会使人对生命的宽厚胖瘦与内在质地,产生一种仿佛可以了解的幻觉,在樱花树下看透明瓣片纷落的轻盈感,在银杏叶铺满的地上以为生命可以很长久的幸福感,诸如此类.地图,不止有被量化的尺度,还有以不同维度去建构时空的便宜,也是一个人以为自己可以掌握的美好幻觉,我能接受这个.
如果给你一种光,你会怎么跟它相处?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渠道上来说,光无处不在,光的明暗度跟PH 试纸上酸碱度似的,层次上的细分,敏感如肤毛孔对温度的反应.而如果给我一种光,我会尝试把自己放掉,光会涌过来,弹过来,塑造我后来具有的身心,它在我里面,也在我外面.会有一个不确定多久的过程,我与它看不见对方,因为究竟彼此的没有分别.
地图论文参考资料:
括而言之,上述文章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地图方面的地图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地图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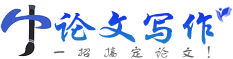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