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短篇小说)》
该文是清洁学术论文怎么写跟短篇小说和清洁方面学术论文怎么写。
母亲说,从小,我就有一个好身体.我们一起在产房里折腾了七八个小时,天亮的时候,我终于脱离了她.照例,刚出生的我也哭喊了一阵,然后,被医生抱到她身边,睁开眼,安静地看着她.
一个有着好身体的婴儿,需要更多的乳汁和.后来她常常跟人夸耀,喂饱我,让我在吃足奶之后睡去,她了不起.毕竟,跟别的女婴比起来,我长得太快.一度,我几乎掏空她的身体.断奶后,虽然不再向她直接索取食物,但我像拧了永动的发条,继续折磨她,让她精疲力尽.
她指着照片,你看你,白白胖胖,我呢,瘦到只剩80斤,还胃下垂.相片里,母亲确实瘦得只剩了一把骨架,只是还年轻,算不上难看.
所以,当母亲递给我一盒药的时候,有一个好身体的我不能确定,她到底在做什么.
她说她要回去了.原本说,她来跟我过暑假,但现在,暑假才过去了不到一周.暑假是母亲的暑假,她教地理.
头一天,我们在35度的高温里,去布匹市场买窗帘.黑蓝相间的竖条纹,橙白相间的竖条纹,母亲选了后者.跟老板借了缝纫机,把两块布锁了边.我们提着窗帘布、挂钩、导轨塞满的两个塑料袋,照母亲的意思,马上去我分到的宿舍装窗帘.女孩子住的房间,怎么能没遮没挡呢,母亲说.
橙白相间的条纹,让房间显得更热了.但母亲似乎很满意.我们一身大汗爬下九楼,母亲说,再去买一台空调.装了空调,我就可以长时间地待在房间里了.母亲按照她家的模样,要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给我立一个模板.至于这么做的原因,她没有说,我们也像平常一样,并不讨论.她眼睛所见我的生活,我大致能想象,但也拒绝去细想.只是像一个二十岁的女孩一样,对母亲的关心和物质补给,感到实实在在的满意.被爱着的普通感受.
直到母亲把那盒药递给我.我们原本在客厅里看电视.天快黑了,电视荧幕的白光照亮并不宽敞的客厅.我住进这里半个月.男友住进来两个月.母亲把我叫到阳台上,对着十字路口的喧嚣,一边说话一边掏出那盒药来.
是盒什么药呢.药盒正面,一串英文发音对应的中文文字,翻过面,看了用法和功能,我把药甩在母亲面前——我不要,你拿走.
她看看我,没有说话.
男友在厨房里斩鸡.他会做白切鸡,鲜美,骨头总带着血.
“真恶心.”我说.
“药有什么恶心的.”母亲把药捡起来.
“你是让我跟他分手吗?”
“把你自己搞搞清楚.”
“搞什么?”我试图挑衅.
“空调明天就装好了.”母亲顾左右而言他.
“我愿意住在这里.”
“你懂什么.”
母亲第二天走了.药留了下来.
男友并不是个可恶的人.毕业前,他陪我去买面试的衣服.他坚持说,面试应该穿得正式一些.我平时的那些裙子,好看是好看,终归不适合面试时穿.那么,面试该穿什么呢,我问.我找工作时,买了一套西装,他说.他比我年长几岁,似乎,拥有了某种发言权.
穿上套装的我,看起来像在Cosplay,里那种.标准的白衬衫、黑西服、黑色的包臀裙.真不明白这样的衣服哪里就看起来更适合工作了.
他看看我,又看看镜子里的我,点头表示很满意.后来又补充说,你这样看起来就不像学生了.不像学生,那像什么呢,我模模糊糊想着,并没有答案.
他甚至陪我去校招现场排了一天队投简历.大操场,学生们都穿着衬衫西服在大太阳底下排队,像待宰的羔羊.每家公司搭一个塑料棚,摆几张桌子椅子,从羊群里挑出些满意的来.女学生们都穿套装,不约而同的黑色.鲜有人嬉笑打闹,似乎手里捏着简历,表情也顿时严肃了起来,像在参加一场隐形的葬礼.
对我的未来,准确地说,我会干什么样的工作,男友似乎比我更在意.虽然他也说不清,一个学中文的,到底该找什么工作.具体而言,我,又该找什么工作.但就像他念叨的,他工作五年了,知道关于这个社会的事,比我多得多.我该认真找一份工作,然后认真工作,才能获得想要的一切.
排在我前面的男生回头问我:“你也是本科吗?”
我们说了几句.男生回转身后,男友在我耳边低声说,“别跟这些学生说话.”
我看着男友,他自然不是学生,那他是什么?我搬进他公寓的第一天,晚饭后,他领我到阳台上指着对面楼宇间的缝隙说,“江.”我不懂.“江景.”他又说.我还是不太明白.于是他又说,同事来这房子都羡慕他.“他们还没见过你.”他得意了.我看着仅有一寸的江面,“不然呢?”“估计要嫉妒我了.”他说.
后来我明白,我大致符合一个理想女友的标准.年轻,长相端正,大学毕业,无家庭负累.而且,看起来单纯.但这些条件要配备给这个“家”的女主人,在男友看来还差一样.我得找份好工作,有稳定的收入.这样下去,他会考虑以法律程序缔结我的关系.真是自信.
他拍拍我的肩膀,“面完带你去吃必胜客.”
第一次,我认真地考虑,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努力在为我做安排,在为我们的未来做规划,而我却根本不考虑这些.
我知道为什么.他确实需要一个妻子,而我还不需要一个丈夫.
他说,我需要看起来不像一个学生,也就是说,需要模仿和表演.事实上,我无论外表或是内心,都还是个学生.所以很难配合及让他满意.面试就像身上的套装一样让我不适.听见自己的声音从被包得严严实实的身体里冒出来,打着颤的尖利,我很厌恶.面试统统失败.
所以父亲说,让我去见谁的时候,我抓过一支笔,飞快地记下了对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父亲给我提供过好几次这样的电话号码,在我上大学,离开他和母亲后.号码的主人一般是父亲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拨通号码,我能去这个城市里最好的餐厅吃一顿,或者完成实习报告,再不济,也会拿到一堆礼物.那些礼物适合送礼,并不适合一个学生日常使用.我堆在宿舍里,久了,有些积灰,有些被舍友偷掉了.我坦然接受来自父母的赠予,经年累月中我们已达成了默契,这赠予无需回报,他们也毫无压力.
他并没有看我递过去的简历.新号码的主人.
只是让人给我泡茶,然后说,你可以过来上班,每个月多少钱.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这工资,太低了.
他笑了,你需要学习,学习需要时间.
我打电话告诉父亲这情况,他说,先做着看.他和母亲意见统一,既然我不想考公务员,又不想回老家,那就先找个轻松工作好了.在我二十多年的生命里,并没有在父母及他人面前表现出过人的能力.我也如父母一般认知,他们的女儿就是个普通人.
男友却很生气.说你怎么能随便就找了份工作.
可是我不是随便找的啊,那人我认识,我说.
他更生气了,“你还有什么事我不知道?”
我想了想,没有回答他.
为了让我认识到后果的严重性,他抱了被子去书房.这套他刚刚开始月供的公寓里,家具尚未齐全.书房里只铺了张床垫.海绵床垫,最便宜的那种.第一次去他宿舍时,发现他竟然睡在这么一张床垫上时,我很震惊.躺上去,身体的重量把海绵压得纸一样薄.每动一样,脊骨就一截一截磕在床板上.
我一个人霸占了主卧和大床.大床很新,散发着橡胶特殊的香气.在我找工作的这两个月里,我们总是吵架.他指责我不会熨衣服,没法让他每天穿整齐的西裤去上班.又说某某的女友跟某某一起供楼,这女友还在考律师资格证.这些抱怨激起我的愤怒,也让我厌恶男女之间爱情之外的所有.但就像他说的我只是个学生,学生的反抗与报复,只能是厉声说:“滚,别碰我.”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睡到11点.刷牙时,男友猛地把卫生间门打开,对着镜子里的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啊?”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我吐掉了牙膏的泡沫.他手上拿着我的手机.呆了几秒,我说,“关你什么事.”
连我自己也听出了语气里的不屑,他果然暴跳如雷.房间里长出一个铁笼,他炸着毛走来走去,余光扫射着我.其实何必把事情搞成这样呢.我的意思是,他为什么一定要控制我.不能安静一分钟.
没错,昨晚,一个男同学是给我发了短信.我也给他回了.可这有什么关系.我知道男友的恐慌,可已失去配合的耐性.镜子里的我脸上沾着水珠,男友在客厅里仍在翻看我的手机.我笑了.在这个他配备出来的“家”里,我知道他在等待什么.我得找个好工作,此外,还得像一个合格的妻子那样,保持贞洁.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他冲我嚷嚷,说不许我再跟这个男的联系.也不许跟任何男的这样.
“投简历那天排在你前面的男的,你是不是也留了他的手机?”
他疯了,我想.每删除一条短信,手机就发出“滴”一声.他像在跟自己的意念搏斗,要杀死什么.
这一切让我难以忍受.
我走进卧室,从衣柜里把那身黑色套装扯出来,扔进垃圾桶.去他妈的.垃圾桶里堆着头天晚上的西瓜皮,衣服扔下去,十几只飞虫腾空而起.他大概是恨我.
我是故意让母亲睡那张床垫的.
接受了父亲安排的工作后,我在一份合同上签了名字,领到了工卡和一套钥匙.两室一厅的宿舍空荡荡,什么也没有.男友在房子里转来转去,最后说,我应该住朝南的那间.为什么,我问.这间更大,而且朝南,他说.可是这间对着马路,我.反正你也不会经常来住,不是么,他像是在跟我确定.我不置可否.
后来,我搬出来,朝南的房间变成了我的收容所,但窗外车流滚滚,永远睡在噩梦里.我想过,他是不是故意的.
母亲自然不能住在这么一间宿舍里.但住去男友那里,仍是他积极主动的提议.我们已经比较糟糕了,分手只是在等待一个足够真实的借口,而已.
“那么,妈妈跟我睡大床好了.”我看着他.
“妈妈待多久?”他问.
母亲穿着睡衣在我身边躺下来.空调“呼呼”吹着风,努力要达到我设定的26摄氏度室温标准.我完全不困,母亲也是.睁着眼睛就只好说话.
“这个人不好.”母亲说.
“什么才是好?”
母亲不回答.
“爸爸对你就是好?”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我有你.”
“我是什么?”
“孩子.”
“我不想听结婚那套.”
母亲又沉默了一会儿,继而开口道:“你还是回家吧,我不是说现在,再过一段时间.”
“回家做什么.”
“还不是一样工作.”
我接不上话.她说的似乎都对.但我不能承认.
“你不喜欢这个房子吗?”我随口说.
母亲转过了脸,口气严厉,“你爸知道了会怎么样.”
“怎么样?”我强撑着,身体却不自觉在打颤.
男友又在吹口哨了.曲调像导管插进房间里,打点滴的节奏,一滴一滴,从天花板漏到我和母亲的床上.
我知道母亲在说什么.父亲知道我交了男朋友.从高中开始,只要我跟男生走近了,父亲都知道.他也以“不许早恋、影响学习”为由横加阻拦过.但这次,我找了一个比我大的外地人,父亲不知道的事就开始变多了.首要的一件就是,他并不知道,我已经跟男友同居了.此外,母亲的话题里还有她这几天来看到的事实及隐含的愤怒.
中午,我、母亲、男友三人一起出去吃饭.换鞋的时候,我穿了一双平时很少穿的中跟鞋.
“还嫌我不够矮吗?”男友戴着那副在家里用的眼镜.眼镜实在是有点年月了,镜片早已发黄,框架歪斜,让他的脸显得很滑稽.
我于是笑了.
电梯里只有我们三人,我站在母亲和男友中间.突然想起一首歌的曲调,我就哼起来.一首调子很轻快的童谣.
“唱什么唱.”男友竟然忘记换眼镜,还戴着那副可笑的备用眼镜.
我看他一眼,生气得已经要扭曲的一张脸.我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到直不起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像看待一个路人一样看待他.所以他显得滑稽时,我就真的觉得很好笑了.
他突然擒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我明显感到了疼痛.像要说些什么,但又忍了回去.我甩开那只手,没有看我妈,也没有看他.
我知道他为什么失控.我们的关系正在脱轨,他正在沦为过去时,以及,他意识到的部分——沦为笑话本身.尤其,他知道母亲出钱给我的宿舍配备空调、热水器、洗衣机后,建议我可以把宿舍租出去.我们为此吵了一架.
母亲不知道这些.她只是坐下来点菜.男友还没吃完,她就叫服务员结账,非常的不耐烦,枉然不顾男友还在啃鸡骨头,像是故意要让他难堪.
父亲要是知道了会怎样.这句话像空气中伸出一只巨大的手,在我脑门前叩了个响指.要看他知道的是哪一部分事实吧,妈妈.
过了两天,我跟母亲说,你去睡书房吧,你打鼾声音太响了,我睡不着.
她瞪我一眼.
“让他睡客厅.”我说.
她似乎并不相信,也并不满意.但我也没法直接说出口,那个吹口哨总是漏风的身体,已经让我恶心.
妈妈顺从了我,这一次.其实通常,她也会顺从我的意思,虽然会经历曲折的威胁、争执和妥协.看着她平躺在书房里的海绵床垫上,我轻轻合上了门.
那张海绵垫子是蓝色的,印着卡通的兔子、熊和花朵.被男友用了那么些年,早就脏得该扔掉了.男友住在宿舍的时候,我和他曾一次次地躺在这张床垫上,做他认为我该做的事,以及我认为我该做的事.
我给母亲在上面蒙了一张床单,摆了枕头.母亲把枕头冲着门,在床垫上平躺.母亲的小腿露在睡裤之外,纤细,白皙,像个少女.
我走进对面的卧室,反锁了门.
躺在海绵垫子上,母亲的脊骨也能感觉到地板吧,一节一节的脊骨会变得明显,跟坚硬的地板对峙.身体会难受,会无力,跟我一样.跟我每一次躺在上面时一样.也许她会想起怀着我的时候,身体是多么无能,以致于要承担卵子受精后的重负,一天重过一天.直到她少女般的身体完全变形,而我破腹而出.
我双手击掌,“啪”一下熄灭了声控灯.
男友是我两年前旅游的时候认识的.等我毕业后,到了这个他所在的城市,生活一点一滴渗透进我们之间时,开始发现两人根本不可能做情侣.但说这些都没有用了.面对龃龉和不堪,越来越多的不堪,我的做法通常是,转身就走.只是,关系牵扯到其他关系时,就变得复杂.母亲来访,让我不愿去面对的部分事实暴露出来.那些爱和性不能够掩盖的事实.但是,我不可能像“啪”一声熄灭声控灯一样终结与男友的关系.即使在母亲到来前,我们已经停止了.
最终,母亲给的那盒药留了下来.使用说明让我恶心,更有突如其来的恨意.我知道,她只是想用一盒药,让我的身体止损.但再多的药,又有什么用呢,毕竟再不是子宫本身了,妈妈.
搬离的那天,躺在宿舍床上,我仍拆开了那盒药.一粒一粒的栓剂,整齐地排成一板.像科学实验里等待受精的卵子.也许母亲依赖这个药,才会想要给我.我盯着药品说明,这药剂可以杀死诸多病菌,让保持清洁.不知道为什么,心脏剧烈疼痛像要冲破我的身体.不知是因为想到了母亲,还是想到了自己.
一个周六的早晨,男友,不,前男友突然来敲门.
“你的包裹.”他递上一个纸盒.
我用身体堵住门,“嗯.”
“我进去坐坐?”
“你走吧.”
过了一分钟,他发来信息——屋子里是不是有人?
关你什么事——我回.
我躺回床上去.被子还是暖的.新男友打开手臂,把我揽了过去.
房间里乱七八糟散落着我们的东西.他的钱包钥匙在书桌上.窗帘缝漏进来的阳光,把钥匙照出些刺眼的反光.
据说乌鸦也喜欢亮晶晶的东西.黑漆漆的乌鸦,亮晶晶的小玩意.我胡乱想着这些,并没有什么思绪.跟王先生签合同那天,我突然想去买书.也不是突然,是在逛了两小时街,买了条新裙子,去连锁咖啡店喝了杯拿铁后,觉得,或许我该去买几本书.王先生,我的老板,不是说吗,我需要学习.
书城有五六层楼高,虽也卖文具和其他东西,但最多的还是书.跟图书馆不同,这里的书并不按年份排列.每个类别的书都不少,但多半很新,让人难辨好坏.我在三楼转了很久,买了一本非洲作家的书、一本法国作家的书,还有一本日本漫画.结账的时候,我有点沮丧,为什么要买这三本书呢,我甚至都不会看完它们.
我抗拒男友的“庸俗”而跟他分手,而是否我也是个平凡直至庸俗的人呢.终究我是软弱的,或者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又一次,男友发现了我手机里别的男人的短信后,勃然大怒,我收拾东西迅速离开.似乎只有这样的暴力处决,这样的不可控外力,才能让他跟我一拍两散.其他任何理由,都会陷入他的辩驳、妥协和再度控制之间.
新男友翻了个身,被子里的温度蒸腾得人昏昏欲睡.我们认识很久了,只是最近,他知道我分手了,我们开始一起吃饭看电影.一般,我没有多想,就把他带回了宿舍.
母亲想让我止损,但我知道,停手并不会止损,根本没有止损一说.而谁也不能教会我什么,更不能保护我.药也许能,母亲不能.
跟新男友的关系并不稳定,我似乎也不渴望循规蹈矩.放纵是止痛药,效果立竿见影.我依赖它.
发工资那天,同组的女孩让我陪她去逛街买衣服.下雨了,天阴沉沉的,我们各撑一把伞,在布满小商店的巷子里穿来转去.
她抓了几条裙子去试,都说不合身.试到一条丝绒裙子时,在镜子前照了很久.紫色的丝绒,吊带V领,把两个胸全部推到了脖子下面.她的影子映在夜的窗玻璃上.窗玻璃外黑漆漆下着雨的夜,让她的真人反像个倒影.
卖衣服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好看的呀,不要遮,不要怕暴露.”
同事撩了撩垂落在胸脯上的长发,“会露出文胸呢.”
“不是要去见男朋友吗.”老板娘帮她调整裙子的肩带.她看起来至少有三十几岁了,应该是比我们,有经验得多.两个影子交叠在一起,收拾着一对胸部.
拎着那条新裙子,我们吃冰淇淋.
“我男朋友会喜欢这裙子吧.”同事说.
“他是什么样的人?”
“普通人,普通男人.”
“会喜欢的吧.”我想起她在镜子里的一对胸部.
“嗯.”她似乎也确定起来.
我们痛痛快快吃起冰淇淋来.在这样一个炎热潮湿的晚上,它融化得太快了.
我们俩在同一个小组,组员多半都是毕业没多久的女学生.组长比我们年长不少,长得美.她的衣着打扮很用心,肚子却呼之欲出.她快生了,肚子变成办公室里的公共话题.任何人都可以伸手摸那只肚子,说几句感想.我的手也贴上去过,很硬,让人难以置信一个胎儿在里面漂浮.同事们说,组长曾是全公司最漂亮的女孩.隐含的意思是,一个怀孕的女人,身体折旧了.
同事们私下会议论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有人说一表人才,也有人说只是个小职员,也许都是.但还是很难想象什么样的人配得上她.
吃着冰淇淋时,女同事告诉我,公司年会上,我们的老板王先生曾扛走一个女同事.
“扛走?”我盯着她.
“玩嗨了,扛着就上了房间.”
“然后呢?”
“然后,大家就散了嘛.”
“好看吗,那个女孩?”
“好看的.”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我舔着甜筒里最后一点冰淇淋.冰凉又甜蜜的沟回像隐秘的兔子洞,急速膨胀,缓慢闭合.我惊觉有点羞耻,因为,竟怀着一丝妒忌.
同事轻轻扔出一句:“就是那个谁呀.”
“谁?”
她靠近我的耳朵,“组长啊.”
我想起摸着她大肚子时硬得像篮球一样的手感.心里头怎么这么难过呢.
与父母的世界或者前男友的世界相比,上班后的世界,让人更没法逃避脑子里的邪念.与成为贤妻良母的愿望相比,每个年轻的女孩都有一个更隐秘叛逆的念头,成为另一种女性,放弃所有道德标准,做一个.
公司附近有一家很豪华的夜总会.每次路过我都忍不住看几眼.如果是晚上,总能看见拖着长裙的女孩带客人上电梯.缓长的扶手电梯,直直通向幽深但金光灿烂的二楼.客人站上电梯,被滚动的传送带运着往高处去.迎客的女孩鞠躬,像被某只手按住了头,腰直直折下去.
那些跟我过着不一样生活的女孩,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们也受着羞辱,也有着快乐.
前男友送来的那包东西,是母亲寄来的衣服,地址还没来得及改正.两双肉色的连裤袜,一条白色长裙.妈妈似乎也意识到,我不再是个学生了.
真丝的裙摆轻轻挂在我的手指上.以前,总是纯棉的质地.
我起来,光着身子套上那条崭新的真丝裙子,再爬回床上去,用手指一点一点把男友的身体弄醒.他咕哝了一声,翻身压住我,把裙子撩了起来.裙子被我们压在身下,很快皱成一团.
他再度入睡后,我给前男友回信息——别再烦我了.
他不坏,只是我已决意离开.我要去试试别的.
又给母亲发一条——我已经搬出来了.
母亲常回忆说,断奶当天,我哭闹不止.我的身体很好,可以比别的孩子更长时间、更大声地哭闹.可我只是在地上打滚,没有冲向她的身体,索取她的.她也没有像有的母亲那样,在上涂抹发苦的药物,让孩子退却.当我明白再也没有奶吃了之后,很安静.之后,每天晚上她塞个奶瓶给我.我需要两瓶奶.喝完一瓶,接着喝另一瓶.两瓶喝完后翻身直接入睡,没有犹豫.也不依恋她.
母亲回——绝不要心软.
面试那天,王先生说,我需要学习,学习需要时间.可是,学习什么呢.学习如何做一个乖乖的女员工?还是一如既往,做一个女儿,然后,披挂某些被成年男性允许的身份,太太,或者什么.
父亲在电话里问工作的情况时,我总是一一跟他汇报,哪些是新鲜的,哪些是无聊的.但总的来说,是可以应付的.
他说,那我就放心了.
但两个月后,父亲还是来了.
我带他去宿舍,因为也没别的地方可去.
白天,房间显得一切都很正常.母亲布置的窗帘和空调都在.床,书桌,书柜,简易衣柜,以及,橡胶的彩色地垫.父亲止步于彩色橡胶地垫之前.房间里没有凳子,我都直接坐在地垫上.他左右挪了两步,打量房间.
几个月前,我第一次把母亲带到男友的公寓时,母亲也是这么打量着房间.客厅直通阳台,两个卧室像一双耳朵,挂在客厅两侧.我搬离的时候,前男友已把改作书房的左侧卧室填入书柜和书桌.只是床垫仍在地上,还蒙着母亲来时我铺的床单.我走到阳台上,看着正午时晃得人睁不开眼的江面,把钥匙留了下来.
父亲若在那套公寓留宿会发生什么?这念头让我惊恐,但又有亵渎的快乐.而此刻,站在我的宿舍里,房间里发生过的一切并没有痕迹可寻.父亲什么也没说.我想开口跟他说点什么,但真正想说的,似乎都不再属于我们以前谈话的内容,于是也沉默着.
我们决定去吃饭.从街边商店玻璃门反射出来的父亲,看起来就是另一个王先生.虽然中年了,但看起来仍年轻.步履有力,头发浓密.我伸出一只手,轻轻挽住父亲的胳膊.突然就开心起来,又像个小女孩了.
我们吃火锅.一半白汤,一半红汤.天冷,火锅汤底剧烈翻滚,徒添暖意.父亲叫了一瓶白酒,给我叫了一瓶橙汁.我给他涮肉,张罗着,像母亲通常做的那样.
“你的动作倒是跟你妈一模一样.”父亲说.
“妈说要是五官像她就好了.”
“她这是对我不满意.”
“妈不喜欢这里.”不知道是不是父亲已经知道了我现在的生活.
“你喜欢吗?”
我的筷子在红汤里划着,要捞起一条滑落的鸭肠,“喜欢.”
“在我们身边,你才会有好的生活.”父亲说.
“我不这么想.”
“我跟你王叔叔打个招呼,你不要去上班了.”
“为什么?”
“我看你再这样上下去,就要连我们都不认得了.”
父亲的筷子在锅里划动,捞起一著羊肉.我们长得那么像,连夹菜的姿势都一模一样.我有点难过.我跟他不像跟母亲那样,生拉硬扯,拖着一条脐带.终究他也只是一个男人,虽然我爱他.
可我就是想让他生气,“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什么生活?”
“你不知道的生活.”
父亲知道我在挑衅他,没有理会.拧开橙汁的瓶盖,给我倒满.
“我讨厌橙汁.”
“瞎说.”
“我从来都讨厌橙汁.”我推开杯子.
“你给我坐下.”
“不.”
“坐下.”
“不.”
父亲比我能想象的狡猾得多.他端起酒杯,连喝了三杯白酒.高度酒,玻璃茶杯.我知道他在干什么.我想他大概是知道了些什么.
“你才23岁.”他喷着酒气说.
“所以呢?”
“你什么也不懂.”他像是下结论.
我像是赌气,端起那杯橙汁一口喝完.可橙汁毕竟只是橙汁啊.
就像后来我知道的那样,早在我从母亲的肚子冲出来,呱呱坠地,成为一个女婴之前,我就已经是父亲的骨血和女儿了.这件事不会改变,直至老死.而成为我的父亲与母亲,他们就会天然地、终生地、不依不挠地,希望我过得幸福、平顺,过得像一个正常人,成为一个好姑娘.那些惘惘的威胁,他们要捂住自己的眼睛,再捂住我的眼睛,才好视而不见.
尤其是,他们认定我只是一个普通女孩.
父亲给我点一瓶橙汁.母亲留给我一盒药.我还是一个女童吧,在那两双眼睛里,在那两颗心里.所以,他们要用这些无害的东西,让我保持清洁.
这些,我都知道.但后来的事,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总之就发生了.我没有回家去,很快辞了职,跳槽去了另一家小公司,没人认识我.带过几个男友回父母家,装模作样分房睡,可父母还是看他们不顺眼,不欢而散.
然后,慢慢地,母亲开始不关心我谈的男朋友到底是个什么人,只是一次次地提,什么时候把婚结了呢.而我,跟不同的人在一起后,不再觉得人和人之间,有什么不可以及不可能的关系.偶尔,我会想起多年前女同事为男友买的那条低胸的裙子.她对着镜子把胸脯托高,再托高.我不用做这些.因为,我已经一个人住第五年了.
可是一个人住,比交很多男朋友,更让父母无法接受.他们只关心一件事,结婚.何时,跟谁.
再后来,我一岁大过一岁,父母一点一点老了.
父亲说23岁的我什么也不懂,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十五年,可以无声无息地过去.我终究没有按照他的意思,辞掉工作,回家去,留在他和母亲身边.他们对此是否满意,现在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甚至一个话题.时间就是这样,什么都毫无价值地滑过去了.
所以,当父亲突然告诉我,我必须在周末回去参加婚礼——我自己的婚礼时,我顺从了.我找不到不顺从的理由.十五年,他们大概已经承受了太多.一个不肯出嫁的女儿,一个慢慢变成笑话的奇怪女儿,所能带来的不幸.而我,终遂己愿,与父母剥离,独自生活.
回家路上,我才想起,竟然没有问,我要跟谁结婚.但对于这场盛大的婚礼而言,这个细节似乎并不重要,我只需要出现,完成使命,让父母可以对他们的世界宣布,他们的女儿嫁人了.让有些事情平息.如此急迫.
飞机舷窗映出我的脸,我的样子并没有太大变化,还是五官像父亲,神情像母亲.我并没有带一个新娘需要的物品,及喜悦本身.他们说只要我出现就好了,我也真就当自己只需要让身体出现就好了.
谁会来出席婚礼?昏暗的机舱中,他们的脸清晰极了.几个前男友,来看热闹还是看笑话.曾经的情人,竟然也要坐在台下,还要带上他的妻子.真不知道这场婚礼会击溃谁.
一个舞台在等着我.
更多的面孔出现了.我的老板,我的大客户,我结交的名流,都在台上.父亲母亲也要上台去.他们能证明我是谁,证明我出现在这台子上的必要和价值.想着想着我就释然了,哪怕新郎还只是面目模糊的一个背影.
一套婚纱在等着我.
抹胸款的白色婚纱,缎子面料.父母像是把钱都花到了婚礼上去,这套婚纱看起来很廉价.我急匆匆把自己塞进去,胸口被紧紧勒住,勒得我每吸一口气,都更小心了.
可是新郎,究竟是谁呢.父母到底找了谁来.
他转过身来,我有些尴尬.竟然是十几年前分手的男友,那个会做白切鸡的男友.我都快不记得他了.
他看起来什么都不知道,又像知道了,但并不在意.总之,他站在那堆看起来并不昂贵的道具——鞋子、花球什么的旁边,也像一个道具,不过是活着的.
真是可怕.我攥紧手心,直至指甲嵌进肉里.那些在台下坐着的人,是否真的能做一个观众.
闹哄哄又终究沉寂,婚礼的画面消隐了.
前男友,不,现在他是我的丈夫了,带我回到了他的房子里.这么多年了,他居然还住在这里.两个卧室像一双耳朵,挂在客厅两侧.
想到所有婚礼后会发生的事,我拉了拉领口,走到书房里去.这套房子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现在,书柜消失了,书桌也消失了.只剩一张床垫,铺在地板上,蒙着一层灰得近白色的床罩.
我的心中空得灌风,跑得进一列轰隆巨响的火车.
书房有飘窗,飘窗下伸出一截楼梯,走出去就是露台.露台下面是一个废弃的仓库.仓库的房顶罩住了露台所有的景观.
丈夫走了进来,指指仓库说,有些人在这里摆卖.
“可是这样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啊,”我认真地说,“你应该搬到别处去.”
“他们卖了一段时间,生意不好,也就不做了.“丈夫说.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空置的仓库里,还有一些废纸、塑料袋遗留在水泥地板上.
“你怎么一直住在这里?”我问.
他笑笑,没有说话.
这套房子确实跟我记忆中一模一样,除了窗户外多出来的仓库.仓库看起来没有那么老旧,不像是盖了几十年的那种,但也不新,中规中矩.像很多仓库一样,屋檐下有一排玻璃气孔.仓库的门全部紧闭,锁死.
我终于明白了.我答应了回来,就要被关起来了.这里到底是哪里?这该死的丈夫又到底是谁?
我努力回想跟他最后一次的情景,但什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母亲来了,我们躺在卧室里说话.他的口哨一声一声滴漏一样渗进卧室.母亲给我一盒药,要除掉这个男人在我身体上留下的所有肮脏的痕迹.
我突然想睡觉,就在床垫上躺下来.最便宜的那种床垫.躺下来,地板就磕着你的脊骨.
我躺上去.一条铁轨挨着床垫通向天边.火车一趟一趟碾压着从我身边经过.火车很近,但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动静,只是碾压而过.我继续躺着,感觉不到动静,也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
丈夫突然招手,跃上一列火车.他看起来很开心.圆圆的脸笑着.看起来很年轻,就像我认识他时一样.他走了,把我一个人封存在这该死的记忆里.
他们让我无处可去.
母亲说,从小,我就有一个好身体.所以,当她递给我一盒药的时候,我不确定,她在做什么.
我已经完成了使命,做一个新娘.上帝保佑,新郎自己还消失了.那么,这盒药是为什么?
我摇摇头,示意母亲停止.不要再让那盒药逼近我.
可是父亲说,你不吃药,你不吃药你能说出你的名字么?
我想了想,很努力地想了想,我说不出.
我长得跟他们太像,以至于他们脸上的每一个表情,都像我的反射,或者倒影,或者记忆剪出来的碎片和重叠.
父亲怎么长得跟王先生那么像呢.母亲裙摆露出的白色小腿,分明跟我一模一样.我开始吵吵嚷嚷,想要他们告诉我,到底该做什么.
只是需要吃药么?还是别的.
我突然想睡觉,感觉所有力气都已耗尽,于是躺下去,在他们面前.地板很硬,磕得我的脊骨发疼.我侧过脸,看见铁轨长了出来,火车一趟接一趟,从我身边碾过.
我怎么这么傻呢,怎么会现在才明白.我只能把身体还给他们.他们知道,这身体是他们造的.但我得修补那些漏洞.所以我继续躺着,等火车带起一阵一阵的风.等火车终究碾过我的虚空,我将变得清洁.
作者简介:郭爽,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小说、随笔见于《当代》《作家》《山花》《青年文学》等,被《小说月报》《思南文学选刊》等选载.获第七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出版有故事集《亲爱的米亚》.
清洁论文参考资料:
综上而言:此文是适合短篇小说和清洁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清洁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清洁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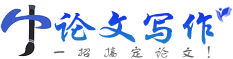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