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往来人》
本文是江上往来人方面有关论文例文与江上往来人和江上方面论文怎么写。
2017年12月31日,我陪外公乘坐从南城飞往上海的飞机.登机牌上,落地时间是零点.
空姐面带微笑,对每一个客人说“新年快乐”,并分发糖果.
外公很高兴,悄悄地凑到我耳边说:“这个小姑娘很懂礼貌.”
我拍了拍他的手,示意他乖一点,他便老实坐好了,但很快他的头就开始一点一点地往我肩上垂.最近,他总是不分场合就睡着,他的手还牢牢攥着那袋糖,像是抓着什么宝藏.
我坐在窗边,看着走道上的人,终于还是想到了江上.
空姐走到我身边时,我习惯性地问了一句:“请问这趟航班的驾驶员是谁?”
她用一种微妙的语气告诉了我两个名字,还特别强调其中哪个是机长.她一定是把我当成了那种想泡空少的女孩.我谢过她,并麻烦她帮我拿一副眼罩.
她走过去的时候,和旁边的同事低语了几句,然后两个人就一起哧哧地笑了起来.
我能猜到她们在想什么——
看上去不年轻了,姿色也平平,还想着天上会掉馅饼.
可是江上,分手三年后,我坐飞机往返于很多不同的城市,却一次也没有在答案里听到你的名字.
我渐渐开始相信你对我说的那句话——“林雪溪,我们没有缘分.”
尽管当时我觉得这是天下间的男女在厌倦彼此后想一走了之的荒唐说辞,而现在,我居然认为不无道理.
这让我不得不感叹.时间这东西,到底是一把什么样的钥匙啊?
我是在2013年12月31日遇见江上的.
那年我二十三岁.
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晚上,剧团又把<天鹅湖》这出剧目搬上了舞台.柴可夫斯基,你得承认,他可真是个天才.
我从布幔的缝隙间看着奥杰塔的倾诉、奥杰塔的痛苦、奥杰塔和王子相爱……那些动作我已经烂熟于心,何时该跳跃,何时该卧倒,最后演员谢幕,观众起立鼓掌,实力验证了那句“经典总是很少出错”.就在这种令人屏息的时刻——
“林雪溪,”团长喊我,“该回去收拾道具了.”
我叹了口气,回到化妆间,开始整理那些换下来的芭蕾舞裙.
那几个年轻的女孩把身上零零散散的配件扔给我时,动作粗鲁得就像是在扔“一次性筷子”,我不由得在心里:轻一点啊!
我发誓我是不小心踩到那个A角儿的,她的嘴唇亮晶晶的,像是柔软的果冻.可“果冻”骂起人来毫不留情,她说:“林雪溪,谁都知道你想上台跳舞,可你也犯不着对我撒气吧?”
你看,每当我以为自己和舞蹈这件事只有一线之隔时,总会有人跳出来提醒我,林雪溪,请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等所有人离开后,我摸到了那条奥杰塔的舞裙,在黑暗中换上了它,溜到了马路上.那是我头一回这么干.我把落满清冷星辉的马路想象成我的舞台,街道上空无一人,月亮就是我的聚光灯,它跟着我,一路蹦跳到那个红绿灯前面.九十秒的红灯,我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可以跳舞,当红灯转绿,我收住步子,朝着马路那头谢幕.
我想,还好,宝刀未老.
接着我就看见了江上.
他站在马路那头,就在我打算逃走时,他漫不经心地鼓起掌来.
那场景太美了,一切都是刚刚好,所以当江上问我是不是在这儿当舞蹈演员时,我自然而然地就说了是.那条舞裙上头坠着的亮片闪着我的眼,眼花缭乱里,我忘了这不过是我偷偷借出来穿的.
那是晚上十一点五十分,十二点时,我们已经彼此介绍完毕——
他是飞行员,今天从上海飞到这座城市来.而我是“舞蹈家”,刚结束一场令全场观众喝彩的表演.
2014年的第一秒钟,我爱上了江上.
那一年,我和江上在一起的每个场景,都像是有人抓着一把刻刀,在我的脑海里事无巨细地描了下来.我闭上眼就能想起他的笑,闻到他身上的气息——那是一种绿色植物的味道.
好笑的是,自始至终,知道我和江上在一起的人寥寥无几.
原因也很简单——
我压根儿不敢同人谈起他,我害怕对人说我们的相识是从江上把我误认成舞蹈演员开始的,更害怕对人说我将错就错,顶着这个身份打算“将爱情进行到底”.我承认我虚荣.我承认我没法大大方方地告诉他,他看见的这个“艺术品”,其实就是个管道具的.
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是外公.
他和江上的初次会晤是在黑漆漆的楼道里.
那时江上正用力抱着我,按照行程,他第二天要飞回上海.他缠着我,舍不得我离开.那些日子,我在他的眼里常常看到一种“飞蛾扑火”般的壮烈,心里冒出一个疑问:是不是飞行员都有这样一双摄人心魄的眼睛?
接着,门就开了,拎着菜篮子的外公好奇地看着我们:“囡囡,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菜篮子里,绿油油的茼蒿菜冒出头来.
那场景回忆起来真叫人脸红.
倒是江上,立马走过去接过外公手里的菜篮子,乖巧地喊了声:“外公,买菜呢!”外公瞥了我一眼,忍住笑,严肃地盘问:“你这人怎么一上来就瞎喊,你是谁呀?”江上“啪”地站直了:“外公,我叫江上.”
后来外公提到他,就会说“最近怎么没看到那个楼道里的”,我臊得慌,只能一遍遍纠正他:“人家叫江上!”
“行吧,”外公点点头,“改天叫那个楼道里的来家里吃饭.”
“外公!”
直到半年前,有一天我回到家,外公坐在沙发上,很专注地看了我一会儿.我以为他要问我工作是否顺利,要不然就是和江上进展如何——分手的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他,我怕他伤心.结果他笑了笑,近乎羞涩地问我:“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到我家来了?”
我从没想过“老年痴呆”这几个字会找上外公,因为他比谁都乐意接受新生事物,思想也比谁都开明.可是如今,我只是上个班回来,不过十几个小时过去,他就已经弄丢了一部分自己.
用不了多久,我们这段爱情唯一的见证者就会彻底忘记——有个叫林雪溪的姑娘,她很喜欢跳舞,她喜欢过一个男孩,是个飞行员,名字很好听,“江上往来人”里的“江上”.
我想过这一天会来临,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这种时候,我就有些遗憾,为什么江上没能出现得早一些?最好在我十岁的时候就出现,那会儿我还是舞蹈社里当仁不让的A角,脸上还是满满的胶原蛋白.我踮脚,我旋转,我跃起,我如断枝的玫瑰决绝坠落,男孩们看我的目光里还写着“轻拿轻放”.
我更遗憾的是,不光是江上,这世上所有人和我的缘分好像都只有短短的一段.
从小到大,所有教过我跳舞的老师,最后都会用一句话形容我——
“林雪溪,你是为舞蹈而生的.”
我不否认.
很小的时候,我就从妈妈那里知道了这一点.尽管她长着一张尚属平庸的脸,还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但这都不妨碍她在舞台上绽放美丽.
她那时是单位文工团里的一员,每次晚会我都躲在后台,看着她如少女般的身段在舞台上旋转.不知怎的,我的脸竟会有些发热.
我从台下观众的眼神里明白到一件事——我的妈妈是个难得一见的“奇迹”.
后来的事就很简单了,当时从上海来南城考察的人里,有个男人爱上了这个奇迹.他带走了我妈妈,却不接受凭空多出一个女儿来——我被留在了灰扑扑的南城.
我和外公相依为命,我本以为自己恨透了身体里流着的是两个先后遗弃我的人的血,却不曾想过母亲留给我的舞蹈天分还是成了我全身上下最值得一提的东西.
大学那几年,我几乎拿遍了各大校级、市级的芭蕾舞奖项.
我和江上提起过我的妈妈,不过一句话——“她生了我,就这么简单.”
他没有再往下问.
我和江上在一起时,似乎很少谈及我们自身之外的话题,就算是和对方息息相关的家庭,我们都始终保持着一种“客套”的礼貌.或许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打算和对方走到白头.
仔细想想,我从没说过“江上,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他也没说过“雪溪,你能不能一辈子留在我身边”.尽管我为了更了解他,把《冲上云霄》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最后得出一个花痴的结论——江上如果穿上制服,一定比剧里的角色更帅.有一回,我在他的钱夹里看到了一张他身穿制服的照片,和我想象的一样.
那天,我像是窥探到了一个令人心满意足的秘密,作为交换,我差点就要把我的秘密对江上说出口了.
我问他:“我是个好人吗?”他几乎想都没想就说了“是”.
那一刻,我多想告诉他,不是的,不仅仅是因为我对你撒了谎,还因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对我的过去的惩罚.
大学快毕业那年,传来一个芭蕾舞比赛的消息,是上海的主办方.据说拿到冠军的人可以直接进入上海的专业舞蹈队.
只有一个名额,我本以为会是我,可结果老师给了另外一个人.
我去找老师,她讳奠如深地告诉我,其实冠军早就定好了人选,各地选拔过去的都是陪衬.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最终名单,一个刺眼的名字跳了出来——
“徐玥”.
是那个男人的女儿.
就在我自己一点点摸索舞蹈情感时,她得到的是妈妈手把手的教导.现在,她依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一个光明的未来,而我却连一个比赛的机会都没有.
我找到学校那个参加比赛的女孩,告诉她我愿意代替她去比赛.上场得化妆,只要衔接得好,没人会发现.她答应了,并一口承诺会担负我的机票钱.结果我真的在那个舞台上赢得了观众的起立鼓掌,我知道自己赢了.到这儿,一切都很顺利.
后续也很荒唐,我冒名顶替的事轻轻松松就被揭发,而揭发我的就是那个女孩,她说早就恨透了我高高在上的样子.第一名当场易主,徐玥依然是最后的赢家.
但我亲手毁了自己的舞蹈生涯,档案上留下这样一笔,再没有哪个舞蹈队肯要我.
妈妈打来电话,她痛心疾首地问我:“林雪溪,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挂断电话.我没法告诉她,我只是觉得人生对我有点不公平.
和江上分手后,我打过他的电话,已经变成了空号,这个人就像是水滴蒸发一样,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
在那句“我们没缘分”到来之前,江上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蛛丝马迹.
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最后一次来我家.
那时已经是冬天,外头刮着风.江上告诉我,这次他会在南城多待两天.于是那个晚上,我偷偷地把他带回了家.就在我的小房间里,我们谁都舍不得睡,因为我们能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少之又少.最后,我们决定看一部电影等天亮.
我们放的是一部非常烂俗的僵尸片,因为怕吵醒外公,我们把电脑的音量调到很小,这样我们就得贴着音箱蹲在地上听.看着演员穿着清朝服饰举着双臂跳来跳去,我们相视一笑.
大概看到一半的时候,电脑忽然一下子黑了,整个房间瞬间陷入黑暗.我还没来得及告诉江上,这台电脑年头有些久远了,就听见江上喊了一声:“雪溪!”
毫不夸张地说,那个声音之凄厉听得我差点以为江上触电了,结果却不是这么回事.我问他到底怎么了,最后他说:“雪溪,我舍不得你.”
那个时候,我是真的以为我对他而言很重要.
我叹了口气,扭过头,对上一双懵懵懂懂的眼睛.外公醒了.
“外公,”我轻声对他说,“我和江上分手了.”
外公静静地看着我,我紧张地看着他,期盼着他能说点什么,哪怕只说一句“知道了”也好.
他伸出手来摸了摸我的头,说:“阿南,别去上海.”
阿南是妈妈的乳名.这个秋天,她死了,癌症.而那时,外公已经记不起阿南是谁了.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次离开南城,是因为那个男人在妈妈去世后忽然变得大度起来,提出接我和外公过去,还说上海治阿兹海默症这块还比较有法子.就连徐玥,也头一遭和我说:“林雪溪,我原谅你,也请你原谅我.你不知道,就像你嫉妒我一样,我也狠狠地嫉妒过你.”
人和人之间还真是奇怪,上一秒钟还在相互厮杀,下一秒就可以变得相亲相爱.
可是现在,外公说:“阿南,别去上海.”我知道,他还是很想念他离家的小女儿.
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外公惊慌地看着那些眼泪掉到他的手背上,他像是被烫着了,猛地缩回手去,手足无措地看了我一会儿,怯怯地把糖果塞到我的手里:“给你吃,你别哭,你别哭.”
飞机落地后,向前滑行的那几十秒,我忽然很想打徐碉的电话,问问她“在干吗”.我拨了号码,那边提示是关机状态,便作罢.这小妮子,最近也不知道在哪里鬼混.
我最近居然开始觉得“姐妹”是个可爱的词语,这可不像以前的我.
外滩的钟声很快就会响起,狂欢一触即发,大家会走上街头,庆祝新年来临.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蓬勃的期待,所以一会儿走下飞机的我和外公,也将要加入他们的行列.
但狂欢过后,我们还是彼此的陌生人,明天再出现在地铁站、公交车上、霓虹灯下、繁华的街头,谁也不会记得前一晚我们曾对对方说“Happy New Year”.
有那么两年,我常幻想江上会再次出现在剧院门口,或者我家楼下,我甚至想好了要在遇见他时问他:“这几年你跑到哪儿去了?”当然,这些台词都没能派上用场.
我渐渐明白,江上是真的不会回来了.
黄耀明和张国荣合作过一首《这么远那么近》,里面有一段独白是这样的:“我由布鲁塞尔坐火车去阿姆斯特丹,望住窗外,飞越过几十个小镇,几千里土地,几千万个人.我怀疑,我们人生里面,唯一可以相遇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江上,我比这幸运一点,我们遇见了.但我知道——
也只是一点而已.
因为在那以后,命运再没有安排别的重逢.
201 7年12月31日深夜,我乘坐飞机,从上海飞往南城,抵达南城时,已经是2018年.
徐玥和我开玩笑:“我们飞了两年.”
我笑笑:“是啊,真远.”
“为什么想来南城?”徐玥问我,“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就是想来看看.”我说,“麻烦你陪我跑这一趟,真是不好意思.”
她摆摆手:“被你麻烦,我乐意.”然后她盯着我的眼睛,“江上,你明白这是为什么.”
很快,她就换上了一种欢快的语气,追问我道:“你在南城有认识的人?是谁?”
女孩的脾气,真像瞬息万变的天气.
然后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你,雪溪.
时隔多年,“林雪溪”这三个字依旧如同原野上凶猛的风,或者暴戾的小兽,轻轻松松地就让我痛彻心扉.我胃痛般地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怎么了?”徐玥紧张地问,“又不舒服了吗?”
我连忙摆了摆手,这丫头最近有些矫枉过正,动不动就一惊一乍的.
雪溪,我第一次发觉我们的距离原来已经比“两年”更远,竟是在我又回到南城的今天.
我还记得你咬着牙质问我,声音像琴弦那样铮铮作响:“江上,你告诉我,什么叫缘分?”
你看,就算是这种时候,你依然有着旁人没有的傲气.
雪溪,是不是跳舞的姑娘骨子里都种着四个字,叫“抬头挺胸”?
雪溪曾经问我:“江上,你说我是个好人吗?”
我说:“你当然是.”
那是2014年的夏天,很热,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T恤,我搂住她时,才发现她真的太瘦了,肩胛那儿的两块骨头硌得慌.后来我看书上说,那叫蝴蝶骨.
她摇摇头:“可是我也会做坏事.”
我不知道她当时想到了什么,只是那天她的脸像是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烟雾,让人看不清楚.
雪溪很少如此,她总是明媚的、娇俏的.她并不适合忧伤.
我捏了她的脸一把,她痛得怪叫,我笑了:“小姑娘,你要知道,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往往和他做没做坏事没多大关系.坏人也能办好事,好人也能办坏事,所以才需要法律.”
“但我知道的林雪溪,”我补充道,“非常非常善良.”
这是真的.
打个比方吧,春天我们在湖边散步,路上有卖栀子花胸针的老人,她经过的时候就会买几个.我说“这玩意儿不到一天就蔫了”,她欢欢喜喜地给自己别上,扯着我走远几步,才回我说:“天多冷啊.”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会浮起一种近似透明的脆弱.
在我和她说起以前的飞行经历时,她的脸上又出现了一样的表情.尤其当我说到“飞拉萨时遇到强气流,有几秒钟飞机直线下降”时,她害怕地握紧了拳头,眼睛瞪得大大的,等我说完后,她的身子晃了晃,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同样的强气流.
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忍不住用力抱紧她.我的宝贝,你这么容易受伤,将来可怎么办?你是一定会受伤的,而且刺你一刀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
因为从头到尾,我的故事就是一个粗糙的谎言.
见到雪溪那天,我刚刚被航空公司炒了鱿鱼.
其实他们的态度非常委婉,只是不再给我派任何活,飞行安排表上,我名字的后面是一段看不到尽头的空白.我知道,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我递了辞职信,一切进行得很快,从公司走出来时,我本以为天空会下场雨象征性地为我道别,结果外头是个大晴天.
真叫人尴尬.
南城原本是我要飞的下一站,结果取消了.我买了机票,坐在经济舱靠窗的位子上,第一次作为一个普通乘客而非飞行员完成一次航行.这种感觉有些奇妙,不用再注意仪表盘上的动静,两个小时里,我看完了一部爆米花电影.
我不知道那个夜晚郑重其事地为我准备了一个惊喜.
雪溪大概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奇迹,我原以为那样的舞蹈只能出现在梦里.
所以当我走到她的面前时,她开口问的是:“你为什么在这儿?”
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多年.
怕惊扰了这个“梦境”,我没有提出异议,我说:“今天下午刚飞到这儿.”
雪溪挑起眉梢:“飞?”
我自然而然地就说:“我是飞行员.”我心想,只不过这已经是过去式了.
她的眼睛亮了:“我从小就想坐飞机.”然后又重重地叹气,“可惜太贵了,我只坐过一次.”
“哪一次?”
“从南城到上海,去参加比赛,一年多以前.”提起这个,她的眼神暗淡了.
“你的舞裙很好看,是刚刚结束表演吗?你是舞蹈演员?”
许久,她漂亮的小脑袋向下一点,像是掠过湖面的水鸟.
“真遗憾.”我说,“要是早来一点,就能赶上看正式表演了.”
我没察觉到她松了一口气,因为新年就在这时来了.烟花在很远的地方发出轰响,现在想来,那余烬多像当时的我啊,抓住最后一点灿烂,不肯熄灭,叫嚣着从高空坠落,如断翼的鸟一样.
“下次还来吗?”我离开时,雪溪热切地望着我.
我脑子一热:“还来.”
“什么时候?”她体谅地说,“要等到下一次飞到南城来吧?”
我还真像模像样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告诉她:“嗯,大概是一个月以后.”
她笑了:“真好,我等你飞回来.”
说来有些丢人,我小时候看宫崎骏的《红猪》,有了飞行的英雄梦想,后来真的当上了飞行员,又开始盼望有一个人对我说:我等你回家.
所以,过了一个月,我又买了机票飞到南城去.
还是那家剧院,门口贴着一张很大的海报,花花绿绿的,旧式的那种.我在上面辨认了很久,没能找到雪溪的脸.观众散场过后很久,她才孤零零地走了出来.
没有那条舞裙,这姑娘看上去只是瘦瘦小小的一点.
我喊“林雪溪”,她眯起眼睛,发现是我后很欢快地朝我跄来,吸了吸鼻子说:“冷.”
我说请她去吃烧烤,转念一想:“你们跳舞的应该不吃这些吧?”
“吃!怎么不吃!”
结果她吃得比我还多,一点也没有身为舞蹈演员的自觉.她的嘴唇被辣椒辣得红通通的,大声问我:“江上,下一次你什么时候回来?”
起初我说一个月,后来一个月被我改成半个月,再到七天,当我说出“三天后就飞回来”时,我对自己说:江上,你还是栽到了林雪溪的手里.
不过,从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你就早料到会有这一天,不是吗?
后来,当我离开南城,更换手机号码,让雪溪再也找不到我时,我也无数次问自己:“江上,如果你知道今天会发生的一切,如果还可以重来一次,当初十二点在那条马路上,你还会走过去吗?”
一个声音痛苦而甜蜜地回答我——
“我会的.”
2015年年初,我和林雪溪分手,回到上海.
一晃已是2017年的年中,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女孩,她就是后来的徐玥.
隔着电话,她的声音里有种闹腾的烟火气:“江上?是你吗?”
“是,”我问道,“你是?”
她轻轻地笑了一下,说:“原来真的是你,我还以为是同名.”
然后她说:“我有件挺重要的事要和你讲,我们约在哪儿见面?”紧接着,她又像是忽然想起什么,抱歉地说,“还是我过来吧,你是不是……已经看不见了?”
已经很久没有人直白地对我说出这三个字了,以至于我恍惚了片刻.
上一回还是在航空公司,我被喊到办公室时已经有种不好的预感.顶头上司看起来忧心忡忡,早些年他和我搭档,他是机长,我做见习.
他对我说:“江上,我们没法给你安排工作了……”他犹豫地看我一眼,接着说下去,“你得去医院,你的眼睛出了点问题.”
他手里拿着的,是前不久出来的体检报告.
你看,梦想这种东西,有时候可能就是被几张薄薄的纸击败的.
和徐玥“见面”后,据她说,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几年前,她说那天是她人生中非常糟糕的一天,她参加了一个舞蹈比赛——至此我才知道她也是学舞蹈的,结果她输了.“虽然最后我还是拿到了那个第一名,但是我宁愿什么也没有.因为那比直接告诉我徐玥你输了更让人难以忍受.”她的背挺得很直,“那个下午,我一直坐在水池边上,是你走过来和我说,小姐你哭得太大声了,把我的鸽子都吓跑了.但你接下来安慰了我三个小时,后来你告诉我你怕我跳下去.”
我隐约想起是有这么一个下午,水池边有个抱着奖杯哇哇大哭的小女孩.
“江上,我们真有缘.”她说.
没来由的,我的心狠狠地跳了一下.
看见她的脸,已经是三个月后我接受了角膜移植的手术,起初还是模模糊糊的人影,后来就清晰了,我便能看到这个姑娘有着和林雪溪一样纤细的脖颈.
不,雪溪还要更瘦一些.
我接受的那副角膜是徐碉妈妈的,她在秋天因癌症过世了.
徐玥告诉我:“其实她只能算是我的继母,她是个很美的女人,有些人天生就是吃舞蹈这碗饭的.她说自己全身上下只剩下这双眼睛是干净的了,我明白她的想法,她是那种就算死也要很漂亮的人.”
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就想到了雪溪.想到初次见面时她的舞蹈,她的骄傲与这双眼睛的主人有些一脉相承.
是了,恢复视力后,我身体里埋着的那些对林雪溪的思念也跟着一并苏醒了,像是在荒原上头点了一把热烈的火,那种席卷一切的清晰的疼痛在提醒着我,我还爱着她.
那天在雪溪的小屋里,电脑屏幕黑下去的时候,我是真的以为我瞎了.
我想:完了,世界这么快就拉闸了,我还没做好准备和雪溪说这一切,它就猝不及防地来了.我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大声喊了雪溪的名字.
短短的几秒间,我的脑海里闪过很多念头,直到暖的灯光亮起,雪溪软软的手捧着我的脸.她刚站起来去开了灯,很紧张地问我:“怎么了?”
我搂住她的腰,我知道自己一头大汗,过了很久,我说:“雪溪,我害怕.”
她笑了,是一种银铃般的笑声.她蹲下来,摸了摸我的头发:“江上,你真可爱.”
雪溪,你不知道我差点就看不见你了.我身体里的每个角落都回荡着这句话.
她就任我那样抱着,一直到天快亮,她才小声嘟囔了一句:“江上,我的腿麻了.”
我就背起她溜出门去吃早餐.铁门在我背后发出一声轻轻的“吧嗒”,是和锁舌嵌上的声音,我忽然有种预感,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了.
坐在早点摊边上,我们点了两笼小笼包,还有稀饭.雪溪的手一直被我握着,她抽了一下,没抽开.进入冬天后,她的手就格外凉.
“吃饭呢.”她轻轻地抱怨了一句,然后又像是想到什么,拿出手机划了几下,随即带着阳光灿烂的表情对我说,“最近上海一直是晴天,飞行没问题.”
好多次都是这样,她查着那些子虚乌有的“目的地”的天气,要是有风她就要担惊受怕,如果是晴天她便兴高采烈.她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
雪溪,我曾经恨不得就在你这种温柔的目光中死掉,但这只是我的奢望.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真相,告诉你你眼前的这个人其实什么也没有,并且很快还会失去光明,因为医生告诉我“现在的情况只能等角膜捐赠”,你会二话不说就留在我身边.
也正因为我太了解你了,所以我不能这么做.
我相信你会明白尊严这玩意儿对我的重要性,尤其当它还和梦想扯着骨头连着筋.
新年的早晨,徐玥还在睡,我们之前就在机场附近找了个地方落脚.
中午我回去时,她应该是刚醒,揉了揉眼睛问我:“你去哪儿了?”
“去找了个人.”
“找到了吗?”
“算是吧.”
然后她的脸色忽然变得严肃起来:“江上,你怎么趁我不注意瞎跑呢!现在我妈的眼睛可在你身上.”我能感觉出来,她很爱她的继母.
我哭笑不得:“小姐,你这样说话别人听到要吓死了.”
她的脸红了:“江上,你大概不相信,我本来一点儿也不愿意我妈签这个角膜移植捐献书的.我想,凭什么呀,凭什么有人白白地就能受这些好处呢?后来在那份名单里看见了你的名字,起初我还不相信,现在我觉得……”
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妈妈最美丽的东西在你那儿得到了延续,这不是件坏事.”
我说:“命运这东西真玄,你说呢?”
她用力地点头.
雪溪,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似乎从没说过这个.
你大概不知道,你坐的那趟从南城去上海的飞机,我查过,飞行员是我.
这是我们之间发生过的第二个奇迹.
雪溪,生命多像是河流啊,亲人、爱人、朋友,这一刻会与哪条溪汇聚,下一秒又会遇见哪片海,没人搞得清.我载过那么多乘客,他们前往不同的目的地,我们起飞、降落,在气流中颠簸,在失重里体验飞翔是怎么一回事,算是“同生共死”过,却再没遇见过第二次.他们的脸像蒸腾的水汽,转瞬就消弭得不留痕迹.
我忍不住去想,这些年,我们究竟错过了多少回?
在那条被月光照亮的马路上.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对将来会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我们会爱得难舍难分,也不知道我们将因此饱受折磨,更不知道随口撒的一个谎往后得靠很多个谎来圆.
2018年1月1日清晨,南城2℃,无风,晴.
我在林雪溪家门口的那个旧信箱里找到了她留给我的信.
不长,七个字而已——
“江上,我不等你了.”
这样也好.这样也好.
就像——
我曾开飞机载你一程,你也只为我一人独舞过.
航班抵达,音乐落幕,该往前的不要回头,该留下的就此沉默.
江上往来人论文参考资料:
括而言之:这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江上往来人和江上方面的江上往来人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江上往来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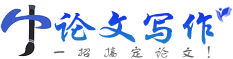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