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悖论与趣味:张爱玲的怪诞身体书写》
本文是疯狂的悖论及趣味类硕士论文范文跟张爱玲和悖论和怪诞方面论文范文资料。
聂成军
“疯狂”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词,更为确切地说, 张爱玲笔下的“疯狂”是小说人物行为的疯狂,他/她们不仅违背伦理法则,甚至违背自然原则,表现出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来.行为的怪异或不合常规,往往暗示着无意识力量的悄然涌动.在张爱玲小说人物的疯狂行为背后,潜藏的是资本主义式的计算逻辑、道家般的超然、“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1]、对个人主义的宗教似的痴迷以及对五四启蒙理性和20世纪30年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混杂交融.正是这样,张爱玲才在大家辈出的现代文学中,创造出自己具有独特审美意义和人性价值的经典人物来.即便是把她笔下的疯狂人物置于现代以来“疯狂”书写的谱系中,张爱玲的曹七巧、葛薇龙、聂传庆、罗杰安白登都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意义与价值内涵来.
具体说来, “疯狂” 在张爱玲的笔下至少具有三重的意义:首先是小说中“疯狂”的人物群像以及对疯狂本身的颠覆,行为的疯狂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并不意味着精神失常或精神超常,反而以其独特甚至极致的自我意识,对事实的“真相” 把握达到了“无情” 的程度.而其根源就在于他/她们缺少意识形态的依附性,结果只能依赖自身,或者说依赖自身的物质性,即身体及其行为.其次是这种疯狂所具有的美学意义,新旧交织的上海,作为“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2]为张爱玲的怪诞书写提供了时空背景和书写“奇异事物”的权力,置于当代的阅读景观中,其小说中人物的“疯狂行为” 不仅令我们心生恐惧,同时也在张爱玲冷静超拔、细腻睿智的笔触下散发出令人心碎的魅力.最后,尽管张爱玲一直回避和五四启蒙文学以及政治之间的关联,但是,笔者以为通过对张爱玲书写姿态和书写文本的分析,我们发现背后潜藏的是五四以来个人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隐性书写.
一
张爱玲的“疯狂”书写表现为人物行为的疯狂.如果说事物的存在本身具有自身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理性)的话,张爱玲则塑造了一系列不合目的,也与理性相悖的人物典型.这些人物处于福柯所谓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真空”地带,他们同时饱受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重规训,成为对于自身而言都是“异己”的存在物.换句话说,有一股力量源自自身,但它又是“异己”的.1943年5月,张爱玲开始在上海的《紫罗兰》杂志上连载《沉香屑·第一炉香》.小说讲述的是随父母从上海到香港求学的葛薇龙一步步沦为洋场交际花的过程.其行为的疯狂之处表现在明知道嫁给乔琪乔“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和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还是“心悦诚服”地嫁给了这个几乎和梁家每个女人都有感情瓜葛的“”男人.作为一个女人,葛薇龙清楚自己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当第一次和乔琪乔拥抱的时候,浑身颤抖的她甚至意识到自己所恐惧的就是自己.“我大约是疯了!” “我可不是疯了!你对我说这些无理的话,我为什么听着? ……” 葛薇龙如是回答乔琪乔.即便如此,她还是紧紧拥抱着位于前方的“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
《茉莉香片》里的聂传庆,这个旧社会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畸形人物,浑身散发着病态的压抑气息和性别倒错的行为模式.如果说对正向的事物的偏好是人类的本性,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确实根植于个体无意识深处的话,聂传庆则是一个十足的异类.他拒绝欢乐,拒绝阳光漂亮的同学言丹朱慷慨提供的友谊,无法正视中国文学史老师的批评,所以,他拒绝“启蒙”,拒绝正向力量的引导.如果这是特殊时代特殊地域(殖民地时期的香港), 以及特殊家庭(母亲早逝、饱受父亲的打骂挖苦、每日呼吸着弥漫有烟的空气……)造成人物的“逆向”生长的话,那么他病态地认同母亲年轻时候的“可能丈夫”、现在的老师、同学的父亲言子叶,并将这种认同转化为对言丹朱的排斥,最终幻想“取缔”言丹朱,还将这种幻想的瘟疫上升为杀人的行为,这一切就必须置于“疯子”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
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因为“判断人指的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3]那么,《第二炉香》里罗杰安白登的自杀则与哲学没有任何的关联.在他的世界里,自杀只是对靡丽笙丈夫的一种拙劣而彻底的模仿.所以,罗杰这个人物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他将最勇敢的行为(彻底否决自己的生命)与最懦弱的行为(逃避社会、逃避妻子愫细行为的后果)结合在了一起.但张爱玲书写之深刻就表现在她不仅试图为罗杰这种既勇敢又懦弱的自杀行为建构一个“无路可走”的社会困境,更把这个困境的起点安置在“无知”与“保守”上:罗杰太太愫细由于缺乏“爱的教育”,在新婚的第一夜,错把夫妻间正常的性行为视为丈夫“野兽”行径的表现,并在一路求救的过程中把丈夫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最终罗杰被学校开除,成了英国人在中国这个“异邦”的绝对他者.这种安排使得整个小说被一种“可笑”与“可怕”的阅读氛围所笼罩.
此外,在张爱玲疯狂人物行为的图谱中还有:许小寒对父亲的之恋以及父亲对同学的之恋(《心经》)、吕宗桢和吴翠远之间的萍水相逢之恋(《封锁》)、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奇异之恋”(《倾城之恋》)、赛姆生太太的之恋(《连环套》)……这些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是,他们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个体处于各种力量的撕扯之下,并表现出为常理所没法接受的行为特征.他们的表现远远超出了所谓“复杂人物” “复杂性格”所能包容的范围,因为就其审美效应来说,正是因为这些行为怪异到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我们才会称之为“疯狂的行为”.在福柯看来,疯狂之为疯狂是理性规训的结果,“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及整齐划一的要求”.[4]如果承认康德对理性的三分(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那么至少就表面来看,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的疯狂行为不仅违背自然理性、伦理理性,在审美意义上也是无法令人产生愉悦感的.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会发现潜藏在人物疯狂行为背后的,是一种资本主义计算逻辑和道家的回避主义哲学,而且其中还混杂有马克思·舍勒所谓的“怨恨”[5].
《金锁记》里的关键词依然是“疯狂的行为”,曹七巧生命中最核心的两个词是“”和“金钱”.曹七巧生命中有三个半男人:第一个男人是一种可能性,第二个男人是七巧的噩梦,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名正言顺的物质性存在,其结晶就是曹七巧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一儿一女.第三个男人基本上是七巧自己的臆想,因为依据小说提供的线索,即便后来姜季泽找到七巧表示爱意,但无疑他爱的只是七巧的钱.至于七巧虽然在小说中有两次表示了对姜季泽的“爱”,但文本根本无法提供“爱”的依据来.最后的半个男人是七巧的儿子长白.之所以不能把曹七巧与姜季泽之间的关系称之为“爱情”,是因为推动曹七巧“爱上”姜季泽的是物质化的肉欲以及肉欲的“增补”.整部中篇小说,其实都是曹七巧的物化与转喻,只是在两者之间不断地游移和相互置换,再加上小说冠名为“金锁记”,而且故事的最末部分以回忆和总结的笔调点明七巧一生都活在黄金铸造的枷锁里,所以给人造成的错觉是:金钱是七巧疯狂的罪恶之源.这样, 《金锁记》的主旨就会沦落为对金钱的批判,如果结合故事发生的背景,这种批判就会被限定为这样的结论:小说通过曹七巧在姜家的悲惨遭遇,无情地批判了沦陷时期彻底为资本主义金钱逻辑所统治的上海.尽管不能把张爱玲对金钱的态度强加于其塑造的人物之上, 但是, 毫无疑问,《金锁记》并没有批判资本主义对人心的腐蚀,毋宁说,它通过曹七巧的悲剧呈现的事实是,在这个无情无义的历史时空里,作为无依无靠的女人,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金钱.
需要注意,张爱玲留给文学史的这一系列变态的、病态的人物,远远超越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由于张爱玲书写的国际性背景(无论是上海还是香港,其殖民地的背景都意味着其“国际性都市”的混杂特色),她笔下人物的疯狂行为在异域色彩的笼罩之下更显怪异,但同时她也将之提升至更具普遍性的意义.也就是说,她并非如五四先辈一样,通过塑造违反常理的人物,通过他们卑贱的无法摆脱的苦难生活来控诉社会(封建社会和现代性社会)对人性的残害和压制.当然,这并非否认社会语境和文化传统对人物的行为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而只是表明,张爱玲笔下人物的疯狂并不具有教诲或启蒙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只是人的存在,人在特殊语境之下存在的极致的展示,只是由于他们选择了疯狂的行为模式而客观上具有了批判的性质.就其根本来说,他们行为的疯狂并非非理性的产物,也并非鲁迅的“狂人” 那样具有超越性的理性,更不属于当代文学谱系中那些天赋异能的“疯子”,[6]他们处于无意识与意识的之间,两者之外并不存在弗洛伊德意识地形学构成上的“超我”.所以,他们疯狂的行为背后涌动的是本能与理性计算逻辑之间的博弈,两者最终同谋构成了张氏疯狂人物的混杂魅力.
二
如何描述张爱玲小说的风格?一般我们喜欢用“苍凉” “凄凉” 或“荒凉”,如发现张爱玲的夏志清就说“中国旧戏不自觉地粗陋地表现了人生一切饥渴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我们可以说张爱玲的小说里所求表现的,也是这种苍凉的意味”,[7].这并非空穴来风,张爱玲自己经常用这个词语来描写自己的写作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这么形容振保对娇蕊的感情“其实也说不上喜欢,许多叽叽喳喳的肉的喜悦突然静了下来,只剩下一种苍凉的安宁”[8].但是,这个词语更多的是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的评价.在《自己的文章》里,她说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没有悲壮,只有苍凉”,[9]而且,张爱玲自己也承认“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10]
笔者认为,张爱玲的美学风格无疑建立在她书写的人物形象上,即人物的疯狂行为上.只有挖掘出张爱玲如何将人物疯狂的行为转变为具有审美效力的内在机制,才能论证其小说的美学风格.疯狂的行为在认知理性(纯粹理性)和伦理理性(实践理性)上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或者说本质上是非理性和理性之间博弈的巅峰状态.两者表征为文学,其在审美理性(判断力)上也不会令人产生“愉悦” 的情感.但是,张爱玲小说的疯狂人物形象,不仅对我们具有“愉悦和不快”相混杂的符合审美感受,更是通过与“”和“资本主义式的计算逻辑”相结合,把理性的三个层面杂合了起来.具体说来,张爱玲通过对疯狂的合理化、淡化与美化三种手段,使得原本令人排斥的对象转变成了具有魅惑力量的审美对象.
疯狂的合理化.人物行为的疯狂通常被归因于社会环境和个体内在心理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内在“精神的狂乱”必须借助于人物行为表现出来,所以,疯狂的行为最终无疑都是社会压力的产物.这种对疯狂的语境阐释就为理解疯狂行为本身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其最终的效果就使得原本由于行为违背理性逻辑而表现出的恐怖感弱化,从而在“怜悯”行为主体的同时,客观上实现了对特定社会的批判.
疯狂的淡化.任何的叙事都有其“聚焦点”,这个“聚焦点”就像“灯塔”一样把读者从茫无边际的阅读的大海中吸引向预定的方向.如果把疯狂作为叙事的聚焦点,所有的叙事动力都集中马力驶向疯狂的核心的话,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最终都会被这股强大的疯狂力量撕裂.所以,以疯狂为主题,或塑造疯狂的人物形象就需要作者采取一定的表现手段,时不时地在疯狂的叙述大路上把读者引向周围的风景,实现对疯狂的淡化或弱化.在张爱玲笔下,最常见的手段有两个:一个是冷漠而超然的叙事姿态,另一个是细节化的空间叙事.
张爱玲并不同情小说中的人物,她更在乎抒情和说理,以及由此带来的快感.这自然容易让人联想起余华的冷漠叙事.但是,余华的冷漠一则为了暴力书写的纯粹性,二则源自余华个人对现实强烈的“解说意图”.用郜元宝的话说,余华的这种解说意图“是一种观念性的解释世界的冲动和为世界制造一次性的图像模型的艺术理想的复杂混合.”[11]张爱玲也喜欢解说, 但是, 她的解说的意图是为了抒情,抒发那种被夏志清称作“‘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 和洞察人生处境的“老练”“悲剧感” 相混杂的情绪.[12]结果, 一是弱化了小说中疯狂行为对人的压迫性和悲剧性,二是分散了读者对疯狂行为及其效应的关注.
有论者指出张爱玲的小说,由于现代性的入侵而使得殖民地都市的日常生活呈现出对常规的偏离,从而造就出了“恐怖与怪异” 的现代都市体验.[13]这种空间叙事具有封闭性, 时间流被中止,小说呈现出叙述节奏的减缓,而变成“物”的展示.“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一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14]从创作的根源上来说,对于空间的强调是张爱玲书写的宿命,因为它们扎根在作者的“幽闭情结”中,使得小说的人物“缺乏现实感,自我构筑出心理围城,呈现出一种人生困境.”[15]
我们可能会提出“恐怖”, 这并非不无道理,张爱玲小说的许多场景,主人公都表现出了无所适从的恐惧感.但是这种恐惧感只是小说主人公或叙事者的感受.作为读者,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小说人物的感受,还接触到了描绘他们恐惧感的词语, 经过这样的“转述”,其结果往往是超越单纯的恐惧感,里面还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即对读者来说是排斥力和吸引力的共存.里面的恐惧不仅是小说中人物企图摆脱的,也是读者不喜欢接近的,但是张爱玲的书写却使得这种恐惧对我们具有了吸引力.正是在内容与形式的这种张力中,表现出了张爱玲小说的魅力和独特的风格.
疯狂的美化.虽然遣词造句只是小说的一部分,这个部分甚至不在传统小说三要素所考量的范围内,但是张爱玲笔下的文字,陌生化到足以独立构成自己审美效应的程度.这样的例子在张爱玲小说里俯拾即是:
“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川嫦本来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但是自从生了病,终日郁郁地自思自想,她的自我观念逐渐膨胀.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16]
“娄太太戴眼镜,八字眉皱成人字,团白脸,像小孩子学大人的样捏成的汤团,搓来搓去,搓得不成模样,手掌心的灰揉进面粉里去,成为较复杂的白了.”[17]
“欢喜到了极处,又有一种凶犷的悲哀,凡哑林的弦子紧紧绞着,绞着,绞得扭麻花似的, 许多凡哑林出力交缠,挤榨,哗哗流下千古的哀愁;流入音乐的总汇中,便乱了头绪———作曲子的人编到末了,想是发疯了,全然没有曲调可言,只把一个个单独的小音符丁零当啷倾倒在巨桶里,下死劲搅动着,只搅得天崩地塌,震耳欲聋.”[18]
甚至在某些小说中,我们会忘记其故事情节,而记住某个独立的句子.这得益于张爱玲式的睿智和老练以及对现实人生及其表征的“享受”心态.有论者指出这是西方小说(“毛姆等人的作品”) “唤起了她的感觉、印象、回忆、等多种感知,从而将现实世界与心灵中那些她无法表达的难以确定的东西结合起来”,最终写出了超越于她的年龄“却又直逼人性最深处的成功作品”.[19]刘绍铭曾称之为“兀自燃烧的句子” “传诵一时的句子,不依靠上文下义,也可以独自燃烧,自发光芒”表现出“的真理”来.[20]
三
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中曾对“意识形态”做了如下的定义: “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或认识的职能).”[21]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并非单纯表征为具有鲜明倾向的政治立场(例如左翼文学),或某时期主导形态的话语结构(如五四时期的“拯救国民性” 的启蒙主义),它更以隐性的形态在历史的潜流中发挥自己“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
由张爱玲小说在1943—1945 年创造的“传奇”、1957年在大陆研究界的“销声匿迹”,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学界引起的张爱玲“神话”,很容易见出她在中国文学研究界所引发的深远影响.仅就此而言,研究或拒绝张爱玲的小说本身就被卷入了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表象体系”中.应该承认,对张爱玲的任何诠释都必须依据具体有形的文本.置于本文“疯狂”及其审美效应的分析语境中, 我们认为,张爱玲小说对意识形态的隐性书写至少体现在如下两个层面:
首先,疯狂及其悖论所引发的意识形态.疯狂的根本原因里面透露出来的意识形态性.周蕾谈到张爱玲的“细节世界”:“细节描绘就是那些感性、烦琐而又冗长的章节” “是从一个假设的‘整体’脱落下来的一部分.而张爱玲处理现代性之方法的特点,也就在于这个整体的概念.一方面, ‘整体’ 本身已是被割离,是不完整和荒凉的,但在感官上它却同时是迫切和局部的.张爱玲这个‘整体’ 的理念, 跟那些如‘人’‘自我’或‘中国’等整体理念不一样.”[22]周蕾的上述分析用于张爱玲展现上海这座现代大都市的“妇女和居家”的生活细节无疑是十分到位的,甚至分析张爱玲的写作笔法也很恰当,但笔者以为这种细节描写并没有消解张爱玲作为个体的“人”“自我”和“中国”等整体概念,只不过她所用的手法是细部的,她目光所及也是日常的细部.而正是对于细部的近乎“病态” 的关注,使得张爱玲在非传统意义上和五四的个人主义和启蒙主义复杂地结合在了一起.
之所以说是“非传统”的意味着我们在分析张爱玲的文本的时候,必须扩大自己的分析语境,如詹姆逊在《辩证批评》里面所说的,我们与其说是在解决“困境”,毋宁说“在于将这些问题在更高层面上转换成它们自己的解决方法,并使问题自身的事实和存在变成新研究的出发点”,这种思维模式的复杂之处就在于,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发现自身愿意把原来是问题的东西当成答案,以将自身纳入问题的这样一种方式置于它原先的努力之外,不仅把这一困境理解为客体的一种抵抗,而且也理解为以一种策略方式部署和配置来反对它的主体的结果———简而言之,就是理解为确定的主客体关系的功能.”[23]
张爱玲的创作通常被看作完全迥异于五四文学革命式的书写,这样的结论建立在这样的表象基础上:张爱玲喜爱日常描写,张爱玲关注的是小人物的爱恨情仇,张爱玲的小说不企图启蒙和教育或者是为某种意识形态鼓吹什么.用柯灵的话说, 战争成就了张爱玲[24],这不仅是张爱玲书写发生的背景,也是张爱玲心灵的孤岛.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活在自己心灵的孤岛中,其幼年的经历,和母亲的关系和父亲的关系,尤其是父亲对自己长达半年的,使得张爱玲产生了“幽闭”的心理.[25]正是这种“幽闭心理”的存在才使得张爱玲以抒情和享受的笔调去书写令人恐惧的疯狂行为.
其次,张爱玲对“娜拉出走以后”道路的探索.张爱玲并非书写日常的第一个人,五四时期鲁迅就写过《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倾向的是个体和家庭之间的冲突; 《红玫瑰与白玫瑰》则是知识分子在情场彻底放纵的忏悔之作.鲁迅写过《伤逝》,后来在《娜拉出走以后》追问女性的命运,并做出了的深刻结论.张爱玲却不给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出路,如果说在张爱玲的文学世界里真有所谓女性的出路的话,这条路也是张爱玲自己所走的路.她的任性而为(离家出走,在香港,服装,爱情),但是其中回荡的是五四个性解放的声音.当然,张爱玲不可能像五四时期周作人所倡导的那样去继承五四的遗产,因为其写作的态度是为了“成名”,但是其成名背后的雄心却是五四的,即女性出走之后何去何从?如果说张爱玲以自己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和自己的写作态度偏离了五四的启蒙传统,形成了启蒙的第三种书写的话,[26]她同时也以自己独立特性的写作姿态回应着五四的命题:娜拉出走之后,可以选择独立自主.《沉香屑·第一炉香》里, 葛薇龙在热闹的人堆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面对这各种各样耀眼的货物, 她感觉“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还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惧”.她不敢想自己的未来,因为“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惧”,所以“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 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27]这种前途未卜的感觉不是瞬间的,它和外在的事物,外在的天与地,人与物,自我和他者融为一体,蔓延得没有边际.是一种绝望到极致的悲凉,抗争已经毫无意义,有意义的只是把力更多到“琐碎的小东西里”,张爱玲也许根本不认为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是“疯子”,人物之间复杂曲折的牵扯所造成的不合常规的行为,在张爱玲看来只是“制造麻烦”而已.在她看来, “是个故事, 就得有点戏剧性.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写小说,是为自己制造麻烦.” “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麻烦刚刚完了, 人也完了.”[28]张爱玲自己的写作其实都是“偏执” 到了“疯狂”的程度.无论是在小说还是在散文里,她对细节的玩味、对“琐屑”人性的琢磨、对自然景物和日用琐碎的家什的咀嚼都是细腻入骨髓的.晚年她更是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对自己影响最大的《红楼梦》上,把它当作艺术品或恋人般去把玩和品味,“这种对《红楼梦》的热爱,几近于一种偏执,一种‘疯狂’.”[29]
张爱玲的这种个人主义是极其微小的,在《中国的日夜》这个短篇小说里,张爱玲这么写道“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和脚都是年青有力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是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30]
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的“疯狂”行为背后,有这样深沉而寂寞的追问: “人到底是什么?”,在张爱玲的世界里,生命本该是美好的、享受的,可她目光所及,亲身经历,到处都是麻烦[31].具体说来,《金锁记》七巧背后是追问“人是什么”; 《倾城之恋》追问的是“爱情是什么”;在散文《说女人》和《有女同车》里,张爱玲追问的是“女人到底是什么”.
四
“疯狂” 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词,如果说阎连科发现了残疾、余华发现了身体的减法、莫言发现了身体的加法、同性恋书写发现了身体的混杂性、无性别书写发现了男性霸权,那么张爱玲发现的就是“疯狂”.当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并不缺少疯狂书写,具体说来,“疯狂”的写法通常有三种:一类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借“疯子”之口道出“正常人”不知或不敢道出的“真相”;二类通常被看作智力低下,是作为纯粹的“疯子” 或“傻子”,却天赋异能,如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土司的儿子“我”、贾平凹《古炉》里的“狗尿苔”,甚至包括王安忆《小鲍庄》里的“捞渣”、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32]; 第三类如曹禺《雷雨》里“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象征着“‘雷雨式’性格的”的繁漪以及在“宇宙”这“一口残酷的井”里不断挣扎却“终不免失败”的生存困境[33].在鲁迅开创的书写“疯狂”的传统里, “疯子”作为被看者,由于行为怪异而被看作疯子, 但他同时又是“看者”,透过他不为“正常” 世界所接受的眼光, 他看到的是令人恐惧的真相(“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34]).第二类和“寻根文学” 多少有些联系,但就其实质而言, 依然处于鲁迅开创的传统之内,只是“疯子” 被置换成了“傻子”或相对弱势的孩童.曹禺先生发掘的人的行为的“疯狂性” 及其带来的“残酷” 美学效应, 在十多年后张爱玲的《传奇》小说集中,得到了全新的演绎和独具审美意义的拓展.
从表面上看,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时常表现出超乎常规的行为.从正常的社会伦理和行为逻辑来看,将之归为“疯狂的行为” 当无异议,但是通过文本的细读,我们发现这些疯狂的行为背后隐藏的是高度的理性,一种近乎资本主义的“计算逻辑”,即是说张爱玲通过疯狂人物的疯狂行为颠覆了疯狂,使得疯狂发生了逆转.从文学的角度去看,需要分析的是张爱玲以怎样的手段将人物悖论重重的“疯狂行为”转化为一种都市“传奇”,从而在读者心中造成既“令人排斥”, 又“吸引人”的怪诞审美感受.如果继续追问,张爱玲笔下人物疯狂行为的美学转化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那么,置于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中,我们会发现,疯狂的人物群像,以及张爱玲本人对这种疯狂的表征其实根植于五四以来的个人主义传统和她有意识地对启蒙叙事的排斥,两者以无意识的状态隐藏在张爱玲小说的书写诉求中.
[本文系2015年高校项目“怪诞美学与批评理论” (15LZUJBWZY139)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页.
[2]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 《流言》,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3]加缪: 《西绪福斯神话》,郭宏安译,《加缪文集》, 译林出版社2001 年版, 第624页.
[4] [法] 福柯: 《疯癫与文明》, 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5][德]马克思·舍勒: 《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林克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6]南帆:《论当代小说中的“傻瓜” 形象》,《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8期.
[7]同[1],第258页.
[8]张爱玲: 《张爱玲全集》(第2 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
[9]金宏达、于青编: 《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10]张爱玲:《〈传奇〉再版序》,同[9],第175页.
[11]陈思和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1页.
[12]同[1],第257页.
[13]刘永丽: 《恐怖及怪异———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现代都市体验》,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
[14]张爱玲: 《封锁》, 《张爱玲全集》(第1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年6 月版,第159页.
[15]杨亚林:《幽闭情结:解读张爱玲的一个心理依据》,《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
[16]张爱玲: 《花雕》, 《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3页.
[17]张爱玲: 《鸿鸾禧》, 《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年版, 第41页.
[18]张爱玲: 《连环套》, 《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页.
[19]范伯群、季进: 《沪港洋场中的苍凉梦魇———论张爱玲的前期小说创作》, 第73—91页.
[20]刘绍铭: 《兀自燃烧的句子》, 《张爱玲的文字世界》, 九歌出版社2007 年版,第102页.转引刘俐俐: 《张爱玲研究的现状、问题分析及其思考》, 《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21] [法] 路易·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1页.
[22]转引自[美] 李欧梵: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
[23] [美]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辩证批评》,王逢振主编: 《新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4]柯灵: 《遥寄张爱玲》, 收录于青、金宏达编: 《张爱玲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5]同[15].
[26]罗慧林:《中国文学“启蒙现代性”的三种走向———兼论“张爱玲热” 的原因》,《文艺争鸣》2009年第1期.
[27]张爱玲: 《第一炉香》, 《张爱玲全集》(第1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51页.
[28]张爱玲:《论写作》,同[9],第83页.
[29]同[19].
[30]张爱玲: 《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出版社1977年版,第506页.
[31]同[9],第440页.
[32]同[6].
[3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414—416页.
[34]鲁迅: 《鲁迅小说全编》,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
疯狂的悖论及趣味论文参考资料:
上文点评,上文是大学硕士与疯狂的悖论及趣味本科疯狂的悖论及趣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张爱玲和悖论和怪诞方面论文范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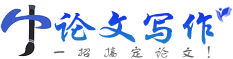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