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短篇)》
该文是有关循环论文如何写和短篇和循环类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银耳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的烟刚掉进了马桶里.当时我只是起身,准备去掏挂在墙上大衣口袋里的手机,嘴唇却抖了一下.那微弱的火星向下掉落,熄灭在我刚留下的液体里.我料到银耳会突然打来电话,我甚至彩排过我们该如何对话,但还是过于突然.我用无名指划过屏幕,指尖撑起手机,话筒那里先传来的却是她的哭声,呜呜咽咽,断断续续,一个音节贴着一个音节蹦出来,全是用汉字写不出的发音.我任着她呜咽,听着那些音节透过一个狭小的空间,传到另一个狭小的空间.
这不像她.但我没打断她,因为音节需要持续,而持续总是有限的.半晌,她才口齿不清地说出一句话,那句话是:“我爸去了.”
那半截烟头被强大的水流推着往更深处滚去,水流滚了一圈又一圈,环状的.最终,干涸的马桶发出了一声憔悴的嘶鸣.我有点疲倦,就像一幅并不满意的画刚画完,不是畅快而是疲倦的那种疲倦.我没有说话,只是伴着这嘶鸣叹了口气.
银耳把电话挂了.
玉田县似乎在衰败下去,河流夹在两边的楼里,显得无精打采.或许只是天阴的缘故,我的眼睛没钻进一点生机.事物总还是旧的事物,构成的元素总是那几类,但记忆不是.我回到玉田县的时候,银耳已经回广州了,她在微信里和我说,是因为双眼皮手术有一点问题,她打算回去做一个修补.再拖下去,夏天要来了,你知道的.她这样说.
是啊,我回复她.我知道的,南方的夏天.
我和银耳结识在南方的夏天,那里是银耳的舞台.银耳站在这舞台上,背对着观众,正对着我.我看着她全程咧着嘴笑,手挥舞得很用力,即使观众只能看到她的后脑勺.四个小时后,上台领奖的银耳终于面朝观众,她的脸在军帽底下很有风采,就像我偷翻到奶奶藏着的旧画报上的人物,意气风发,向着新生活挥手.她咧开了嘴唇,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没有人会去质疑这个笑容有什么问题,但我却看到了,她的笑容里有一道缝隙,即使她往这道缝隙填塞各种材料,还是有一些东西从这道缝隙里流了出来.
或许只有我看到了.四年后银耳躺在我身旁说,那天的合唱比赛,她一直很不舒服,因为他在底下.那天的合唱比赛,她上台拿的是二等奖,还仅是团体二等奖.这一切都被他看在眼里.
但我躺到她旁边,想起的是她在比赛时的笑容.她站在我面前挥着双手,我看到了有几个瞬间,她的嘴角松了,那是笑容太重,它却盛不住的瞬间;但很快,她又抬起了它.我那时候很好奇这个笑容,隐隐约约察觉到他的存在.他就挂在她的嘴角.
她曾经向我描摹过这个男人的长相,我借着她语言的笔在脑海画过几次肖像画.但在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却发现那些肖像画通通不对,它们和我眼前见到的男人几乎没有一点重合之处.
叔叔好.我点点头,弯下腰脱鞋,高帮鞋的鞋带被我打成了死结,此刻连累我在玄关处弯成一条不礼貌的虾.银耳走到我身旁,弯下腰,单膝跪地,冰凉的大理石在她膝盖下映着我的脸.她两只手飞速转动,帮我把鞋带解开.站起来时她摸了摸我的头.我的短发被她双手摸丢了形状.
我的好哥们,她这样对着她父亲说.
我看到那位身材瘦小的男人,微笑着在注视我,然后拎起烧开的开水壶转身,往两只玻璃杯里倒水.银耳的同学,来坐,来坐.他把茶杯端到我面前.我站在银耳家的沙发边上,决定坐下来.拿起茶杯时,我的手臂扫过密封的茶叶罐和擦得发亮的茶具,差点把它们打翻.我太过紧张了.
或许他也看出了我的局促,打开了电视.电视里的主持人和观众都在努力笑着,笑得让人莫名其妙.他掏出了烟,点了起来,配合着电视节目的声音,问了我的高考成绩和志愿学校.你们不在同一座城市啊.他在烟雾里抬起了眼皮,看了银耳一眼.鼻翼宽大,下颌微凸,银耳也有着同样相似的下半张脸.
是啊.银耳的语气里带着一点失落.一种合力演出却迅速被人戳穿了的失落.
在我走进理发店前的四个小时,银耳和我吵了一架.当高考成绩隔着一块布满斑点的屏幕跳出来时,我的手心却发凉了.我踏进了本一线,她被隔在了本一线之外,仅差三分.她在一道线的后面望着我,我站在线前不知所措.
我和她坐在玉田县的河边,没有说话,她一根接着一根抽着烟,在缭绕的烟雾里不再熟稔地掏出笑容,而是紧锁着眉头.我不知道她眉头里装着的是什么,或许有一部分是对自己的失望,也有一部分是对我的失望.像是我抢走了她那三分,我一直愧疚地低着头.银耳把烟抽完了,捡起地上的烟头,用力往河里抛去.它们没有重量,在空气中零零星星地画着抛物线,很快就落进了水里.
你来读最好的专业.银耳站起来拍拍双手,像在抖落掉到掌心的烟灰.跟我同校.别读设计,读金融,留在广州很好找工作.她看了我一眼:当然,我只是建议.我突然觉得此情此景,曾经原原本本在我的记忆里发生过一遍.就在我选择放弃艺考前.银耳拉住了我,她说,别读艺术生,你在浪费你的成绩,把美术当好,这样最好.
银耳唠叨了一整节晚自习,周围的同学纷纷向我们侧目.我们被赶到了楼道里.银耳坐在漆黑的楼梯上向我掰着手指算.我说过啊,我叔公和我爷爷完全不同,他们全家的命运也和我们全家不同.
我当时对高中日复一日的文化课感到厌倦.我游荡在另一个圈子里,它和银耳没有重叠.银耳对这个圈子嗤之以鼻.她说过很多次她不喜欢他们,他们没有前途.前途?我对银耳的这句话也嗤之以鼻.但我还是选择听她的话,中止了艺考的路线.
那年的高考人数有九百一十五万人,如果少了我一个,或许银耳就少了一个竞争者,可以选择的大学或许就更多一些.银耳为了我的未来高考失利了,我也应该为她而选择一所本二的学校.或许这样的逻辑更妥帖一些.
可是我还是想学设计.我说完这句话后,她没有直接回应我,只是在朝我眼睛深处看.我也没有转开眼睛,那一秒,我开始后悔了,因为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不好的信号.
果然,她的眼泪开始溢了出来,从眼眶里一点点往下落.我有点慌张,从口袋里掏出餐巾纸递给她,她没有接.半晌,她都没有说话.但我已经知道了,我不应该违背她,我违抗了我们原本约定好的逻辑.
随便你吧.银耳收起了眼泪,用这句话把我所有的话语都塞了回去.她直接转身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旁边淌着玉田的河.
我犹豫了一会,没有起身去追她.我继续坐在河边,拔着挠痒脚踝的杂草,过了一会,我起身走去理发店.我对理发师说,都剪掉吧.纤瘦而温柔的理发师有些惊讶地望着我,又问了我一遍.我说,全部,剪到和你一样的长度.出理发店时,我贪婪地大口呼吸外面的空气.经过的路人多看了我两眼,我却觉得脚步也轻快了起来.剪掉长发后,我报了一所长江边上的大学.
大地开始往上萌绿芽的时候,玉田县的空气里溢满了水蒸气的味道.我第一次见到银耳时,她的眼镜上正带着薄薄的一层水蒸气,遮住了玻璃后面的那双眼睛.我看不到她的眼睛,只看得到她的动作,她在操场上说话,动作夸张,她周围有几个女孩和男孩.她在笑,嗓音是磨砂材质的画纸.
我好奇地走近他们.银耳在说,四眼田鸡你见过吗?你吃过吗?周围一个瘦小的男孩钻到她身旁,四眼田鸡这么肥,只见过四眼肥鸡.他说罢,脚步轻快地跑远.银耳转身去追他,跑着跑着,却故意做出蛙跳的动作,激起周围一阵笑声.后来我才听到,他们正在叫她“四眼肥鸡”.只是一字之别.
银耳后来都没有吃过田鸡.她常常在看到泡椒牛蛙、水煮田鸡这类食物时,选择飞快地翻过这页,即便知道它们很美味.她只是直接说,它们很脏,全是细菌;仿佛多看两眼,那些细菌就会像春天玉田的水汽,蒙上她的眼睛.
只有我在玉田的夜晚捉到了正在奔跑的银耳.银耳穿着笨重的校服,戴着那副蒙着水汽的眼镜,在一片模糊的光影中向前跑去.偶尔她停下来,喘出的气息在夜色中成了一道烟,再化进了雾里.我坐在角落的单杠上,看着银耳奔跑的身影,她跑了一圈又一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
等到玉田的水汽都慢慢散去,玻璃也变得干净起来,我才逐渐看清了银耳的眼睛.她的头发越来越长,扎成一把薄薄的马尾.她在操场上跑步的姿势越来越灵活,马尾也随着后脑勺不断晃动,像白天那些跳动着的笑声.她终于也注意到了单杠上的身影,那是我.开始没有人叫她“四眼肥鸡”,那个外号就像青春期早期的潮动,来得快,去得也快,退潮时连带着岸边的石子消失得一干二净.
只有一块卷不走的礁石,永远立在岸上.银耳说,她父亲最开始在医院看到她的时候,差点晕了过去.这张缩小版的他的面孔,却安在一个女孩的脸上.他当时曾提议把我藏到乡下,好让我妈再生一个,谁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还是骂我.十四岁的银耳爬到了和我一样高度的单杠上,对着玉田的夜幕说话.
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他永远都只能有我一个孩子.银耳像在发表演说.
似乎作为报复,在厂里大院,三岁的银耳站在一群大人中间,在被询问“你爸在哪里”时,凭着直觉,她径直走向了厂书记,指着他叫了一声“爸爸”.最后是她父亲把她从地上用力抱起,在一片哄笑声中宣告他的主权.
那件事给他留下了心结,不管他承不承认.因为关于这一点,在她后来十几年的成长里被反复验证.她的称号一度被拉长为“没有良心的”五字,而她的名字,这个他看着地上那个塑料包装袋而取的名字,却被他弃之不用.他真这样叫你?我问.她点头.他怎么能这么称呼女儿啊?我扮演了一个不称职的听众,抛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句.
她父亲是家族里唯一一个只有女儿的男人.我第一次听到“家族”这个词时,吃了一惊.这么遥远而陌生的家庭指代.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银耳问我.这意味着家族到了他这里,就停止延续了,除非我招赘.现在想起来,这样的话语从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嘴里说出,带着莫名复杂的意义.在这个意义里,没有我的参与位置,我的存在,是一个意外里的意外.
那时的她就想得这样遥远,以至于她后来做的每一个选择题,都必须要往后做更远的逻辑推演,才能拿笔在括号里填上选项.我向来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总是在每个当下冒冒失失地选择,再冒冒失失地沿着前一个选择做后一个选择.
在家族的聚会上,银耳见到了她从香港赶来的大伯.他讲述八十年代他去广州做香菇生意的经历.那是村庄里大兴种香菇的年代,而大伯摩拳擦掌,大胆地做起了生意.那是广州,八十年代的广州,一天卖香菇就能挣二百多元的广州.已经是一家食用菌厂老板的大伯拍着银耳的肩膀:当年你小屁孩的爸没有胆量,就留在玉田进工厂,混了半辈子混不出名堂.
银耳听到席间另一个亲戚大笑.如果当时你爸也做生意,就不会有你的出生了.银耳的上身坐得笔直,只是把肩膀向前移了一点,让那只手落空,又自然地滑了下来.
你知道,大人有时候爱开玩笑.我说.
虽然他在克制自己的目光,但我还是看出了,他的目光一直落在我额头以上的区域.他大概没有见过这个年龄的女孩留一头这么短的头发.
他终于还是问了,语气拉家常似的.为什么把头发剪这么短啊?特有的玉田人口音,“剪”字短得缩在一起,“短”字却拉得很长.
短发好,凉快,叔叔.剪完头发后,我每时每刻都在同情留了十几年长发的自己.
你家里面不生气?
人家喜欢.银耳的语气里却带着急音.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总是喜欢挑刺,总是喜欢剥开一团和气,去看里面藏着的那点不和谐,继而再把不和谐捧出来描述.
您说得对,上大学我就留长发.我无所谓他怎么看我的头发,只是拉住了银耳.我以为眼前的他会对银耳的急音发怒,继而在我眼前上演一场冲突,就像她每次给我描述的一样.但他只是轻轻而尴尬地一笑,眼角的皱纹就像一朵缩在一起的银耳.
报志愿的那一周我和银耳没有联系.但只要我冷落她一阵,她就会想明白,接受我的选择.她每次都是这样,先主动向我道歉,我没有理由不接受她的道歉,因为那时我已经处于下风.何况,她也只是想离我近一些.她的逻辑战无不胜,我也会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最后推动着这个逻辑继续向下发展.
我以为那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夏天.整个玉田县都亮堂堂的,从高中大门出来,有一座桥,夹在那条闪着银光的河中间.站在烈日炙烤的桥边,我看到银耳没有打伞.她只是扒着栏杆往下望,水流湍急,带着六月涨起的水平线.银耳的两条细腿亮得刺眼,每一个走上桥的人都会朝她张望.我在桥头向她挥手,她在转头看到我的时候眼睛亮了起来,随后她眯起了双眼,露出了熟悉的笑容.
再见就是半年后.她又和他吵架了,拉着行李箱来找我.她打开箱子,露出了里面一袋袋米粥粉,冲下开水,就会盛满一碗.她说她专门买这些带给他,吃这些养胃,从广州带回来,他却看也不看一眼.活该他胃不好.
但我怀疑她在学校里也没有吃正餐,不过拿这些作为代餐.她比夏天看起来还要瘦.只是不到一周,我就看着她胖了起来,很久没有吃热腾腾的米饭,她盛了一碗又一碗,我看着她最后拿着锅勺吃饭的样子,狼吞虎咽一般.这又何必呢.
省钱.
她没有抬头,耳朵上有一点的光在闪动.
我知道她在大学里交了一个男朋友,那是一所装满有钱人孩子的大学,她像一枚糖,能融化在里面.我猜想,会有男孩子被她吸引,像午后需要喝一碗甜而凉的补品一样渴望她.但没有一个人会像我一样了解她,我们一年只能有两个季节可以见面.她的体型只有两次机会开始循环.
我曾经替她想过许多办法.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胶水,想涂抹,想粘合她和他之间的关系,最后都只能看着中间的缝隙在拉紧之后又绷开.我说你们应该沟通,应该坐在一起,好好地聊聊天,把心里的感受都和对方说出来,天底下百分之九十的关系,都需要靠沟通来粘合、来维持.她说她试过,从她妈妈离开时她就试过.他只会说我“不懂事”,说我“没良心”,我还能怎么沟通?
银耳躺在我身旁,大概知道这句话后面的力气,她转了个身,靠紧我的身子,像以前一样抚摸我的唇形.她曾经说过,这个习惯来自她小时候,记忆还未成形的时候,她就喜欢这样摸她妈妈的嘴唇.她的手指很光滑.
年初的时候她收到了父亲给她发来的消息.“住院了,医药费可能要几十万.”当时他没有和她说具体是什么病,有多严重,仿佛这句话抛给她,就是对之前二十年养育的陈述,现在把笔交给她,需要她开始阅卷了.她去找在广州的大伯,拎了一箱牛奶,手指被勒出了两条红印.
大伯被她的阵势吓了一跳,又被她带来的新闻吓了一跳.他跟着她赶回了玉田县.
胃癌.她又去联系五十年前在北京扎根的叔公一家,带着他转院去了北京.她停了几乎半年的课,没有一点能回到广州的时间.那段时间,她没有余力去思考我的存在,她开始在他的好转和恶化之间,承担着希望的燃起和熄灭.如同我在这里一样.
十月,玉田县才正式入秋.距离他的葬礼已经过去十多天的时间.我背着画板走过大半个玉田.我知道我和银耳一样,走再远也会回到这里.站在玉田县市区的那条桥上,看着浑浊而阴沉的河流,我突然想把他画下来.
那真是一幅难画的肖像,我只能凭着记忆,按着银耳的脸,去想象他的样子.我闭上眼睛许久,脑海里终于出现了他少年时的样子,眉骨高耸,鼻翼宽大,坚毅的下颌线.
那时的他正走在玉田县林村的山谷中.那个夜晚,高高的泥土路延伸进橄榄枝的山谷中,他走近家族的老房子,看到门前、道边挂着一张张竹席,上面晾着一片又一片的白木耳.他经过时,看到它们与月光交辉.他想到家人曾说过这给家乡带来富裕的东西,名字叫作银耳.他张口复述了一遍这个名字,银光闪烁,觉得好听得很,应当把这两个字放在心里,或许有一天能派上用场.
我又想起银耳新发在朋友圈里的自拍照,她和她的大伯正式和解.一群人坐在一起吃饭,她在最前头,举着手机,表情温柔地自拍.调整过的眼形让她的眼睛更鲜艳而明丽,和其他五官都拥抱在一起,包括她所携带的他的宽鼻翼.她的笑终于可以被这双眼睛盛住,而不是被缝隙漏光.
循环论文参考资料:
本文评论:本文是关于对写作短篇和循环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循环本科毕业论文循环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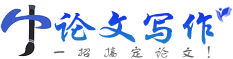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