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老鼠(短篇)》
该文是灰老鼠相关论文写作技巧范文和老鼠和灰老鼠和短篇方面毕业论文怎么写。
戴升平
下午出厂门口的时候,老王突然冒出来捏了一把我的胳膊.他问:“怎么样?”
我愣了愣,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胳膊又重又痒,但是这时候最糟的应该是我的心脏,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得突突的,好像要从胸口飞出去.两个保安就站在离我十来步的地方,眼睛直直地盯着出去的人.边上脚步匆匆,没有人看我们.但我还是很紧张,额头上的汗毛竖起来,渗出了细小的汗珠,手也变得滑溜溜的.我扫了一眼老王的眼睛,渴望寻觅到他疑问里的答案,但是什么都没有,老王笑眯眯的.
过了一分钟,我才慢吞吞地说:“唔,就这样.”
老王没再说什么,还是笑眯眯的,脸上却有种意味深长的表情.他拍拍我的肩膀,摇摇头,往外面走去.
经过阿勇小炒店时,他探头往里边看了看.往常的这个时候,那个女人是在门口的.她从老家来了没多久便在这做了服务员,顺便推销一种本地产的啤酒.啤酒推销员的制服是红色的,领口开得很大,右边胸前绣着那个啤酒的商标,是一座山峰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这身衣服穿在她的身上是紧身的,被撑得有方有圆.裙子包住了大腿以上的部位,但是又给人没有包住的感觉,两条粗黑的腿光光地立在一双黑色的高跟鞋里.她喘气的时候,身上那些粗大的毛孔似乎也在张着嘴呼吸.去这个小炒店吃饭的大部分是周边工厂里的人,男人们盯着她时,目光总是悄悄地从她脸上挪到啤酒商标的位置.今天,她不在,老王似乎有些失望,我也有些失望.
直到看不见老王的背影,我把自行车推到水槽边上,抓了把锯末和洗衣粉混合的粉末搓起手来.去推自行车前,我已经把手上的污油和铜锈洗干净了.自来水凉凉的,冲到手上时,我颤抖了一下,但很快便适应了.我又掬起一把水洗了洗脸.这个温度的水让我的心慢慢冷静下来.老王的表情还在眼前晃动,意味深长.他是话很多的人,却什么都没有说,这样,我反而更加不安起来.东西就在我的胳膊上,离他捏我的地方只差两公分左右,他肯定是发现了,否则怎么会捏我的胳膊拍我的肩膀呢?而且表情这么奇怪.他知道了什么?
洗好手和脸出来,厂门口已经空了.边上小卖店的老板娘又叫住我:“喂,老鼠,你还欠我钱呢,可别忘了啊.”我瞪了一眼老板娘,懒得理她,不就是两条烟钱嘛.我不喜欢别人叫我老鼠,灰老鼠,一听就觉得鼠头鼠脑,一副猥琐样.
我看着天空,天色还亮晃晃的,但一团团的乌云正渐渐从远处挪移到我的头顶.这些云团沉重慵懒,像随时会塌下来,压在我的身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手臂上的铜坯显得特别沉重,身上的那些痂壳也似乎变得格外坚硬,我觉得呼吸都有些困难了.我想,如果不是这身病,我也许照样不起眼,活在隙缝里.今天,我本来是想着不带铜坯出来的,但这个事情既然变成习惯了,一下子还改不掉.如果不是老王粗心,我也不会发现这个漏洞.这个工厂里,工人的铜坯是按箱领取的,交成品的时候却是按个数清点算工钱,废料都扔在废料筐里,并不计算.当我发现这个事情后,先是尝试性的,放一个做废的铜坯在口袋里,万一被发现,理由也想好了,就说是带回去研究下操作失误问题的,老王肯定不会再追究.第二次,我夹了两个坯料在胳肢窝里,那地方不会让衣服显得沉重下坠,也比较隐蔽,不容易被人发现.而且,我的衣服是特制的,即使不小心掉下来,也会落在内衣的松紧口里.多次尝试后,我在自己的袖子上加了特别用途的口袋.因为皮肤病,从冬到夏,我一直包裹得严实,这样的形态让人厌恶,又容易被人忽略,但是,这个严实给我带来了便利.
光头常常诱导我,让我多拿些铜坯给他,这种原料常常紧缺,又高,但我并不理会.尽管老王糊涂,但是有些事情做过头了他也会翻脸的.于是我谨慎地控制着节奏,慢慢把一个十公斤重的麻袋装满了再送去光头那里.
想到光头,我发现自己刚洗过的脸上又渗出了汗珠.
这个夏天特别热.生了皮肤病以后,每个夏天都特别热.我很想把衣服剥了,像马路边乘凉的大老爷们一样,袒露出雪白的肚皮凉快一下,让身体吹吹风淋淋雨,但是我不敢.那些红色丘疹常常突然从皮肤里层爆炸出来,从脖颈一直蔓延到肚子上.这些颗粒奇痒无比,除了吃抗组胺类的药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抓,等抓烂了溃出水来,才会结一层硬硬的痂.痂坚硬似鱼鳞,泛白以后会簌簌地落地.这样的身体怎么能给人看见呢.于是我就更加地小心翼翼,在人面前,从不会脱下自己的衣服.我一直在看病,医院的医生说我大概是因为接触了不干净的东西才导致的过敏,或者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寺院里的法师说我孽障未消.我知道他们都是骗人的,谁都治不好我.这身皮肤病黏着我,洗不净,也赶不走.
骑着自行车从工厂出来,我发现有一处河岸围了好些人,就停下来看了看.那些人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在说什么.听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们说那个人是趴在河里的,不知道从哪里掉下去,大概漂了一阵子,才漂到这段的,再漂出去就到海里了.洗衣服的人看到河里鼓起一件衣服,就用树枝钩了几下,后来才发现,衣服还是穿在人身上的.那个人太大太重了,好几个人才拉上来……我想起汛期时,从上游养殖场漂下来的死猪,却想象不出他的样子,那么黑的人突然被泡得白白的,身体还肿得很大……想到这里,我觉得胃里翻起一阵奇怪的味道,也是突然间,四周有越来越多的脚围过来,越来越多的鞋子踢着日晒了一天的尘土把我困在中间,天地都密不透风似地压着我了.我挤出人群,深深地吸了口气,却嗅到了一股更复杂的气味,咸咸的.
昨天中午的时候,厂里就有人在说这个事情了.我去交货,管装配的那两个女人对我瞪白眼,因为我打断了她们的闲话.她们当时就在说那个事情.那个脸黑黑的女人说:“男人打她了,在饭店里就打了.好多人看着呢!不会莫名其妙打的,肯定有什么事才打起来的吧……”
如果不是我把产品搬过去,她们就可以继续闲着了,所以,她们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说:“十三号,把箱子堆好点,堆整齐,这么远我们怎么够得着啊.”十三号是我的设备号,也是我的工号,作的工序是把两指粗的黄铜坯放在车床的刀口上钻出六角形的洞口.除了这家工厂,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我习惯了和机器相处,和各种各样的模具、坯料、成品相处.她们叫着十三号的时候,还故意在箱子上踢了一脚.铜件分量重,没有被她们踢倒,但是摆好的位置全都乱了.我于是蹲下去重新理了一遍.
她们都坐在小凳子上,没有动.另一个接着说:“也可怜的,听说这个男的一直想要个孩子,这个女人却总生不出来.看了好多年病了,也不知到底是哪个人的毛病.”
“为了这样的女人不值得,天天穿成这个样子,不招蜂惹蝶才怪.不过,这个光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为了这个事情打起来?然后跳了河?这种男人不像是会跳河的.”
“也难说的,好像是说酒喝醉了,走错路了,就滚到河里了.头都撞肿了呢!”她们摇摇头.
车间主任老王刚转到这里,看到我蹲在地上整理产品,他就批评那两个女人,说:“你们又为难小张了吧,认真点,干活认真点.不知道的事情别乱说了.”老王本来也是个多话的人,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对于这件事情,他却有些守口如瓶.
一股酸酸的泥腥味冲进我的鼻子.我背对着人群干呕了几下,却什么都吐不出来.
我想起某个夏天的黄昏,在后塘中学的墙外,那个胸部很大的陈冬雪在河边指着我叫“灰老鼠”的样子.
那天轮到我们当值日生,我就拎了个红色的大塑料桶去提水.前一夜下过雨,河岸边的泥地有些滑,我从墙脚踢了几块断砖当垫脚石,小心谨慎地走到河边上.学校里的值日生打扫卫生拖地,都要从西边围墙的小门出去提水.十三岁了,我还没有长个儿,连塑料桶都高过了我的膝盖.当我提着这桶水的时候,重心全落在右侧,膝盖被桶壁磕碰,走起路来就一拐一拐的,水也一路摇摆着洒出来.回到教室时,只剩下了半桶.和我一起值日的女同学陈冬雪是个大嘴巴,笑起来声音无比响亮.她一笑,前面的四个牙齿就露到了嘴唇外面,她说:“你这个小不点,真是没用,这么点水怎么够用?你快点再去提水,提水这种事情都是男生做的,虽然你个子小,但你总是个男的吧.别磨磨蹭蹭的,我还要早点回家吃饭呢,你再不快点我就走了,你想一个人打扫就一个人打扫吧.”我站在她的边上确实成了小不点,差半个脑袋还不止,像只细胳膊细腿的蚱蜢.班主任黄老师长得很威严,他在课堂上说:“给同学起绰号是不对的,不文明,以后别给同学起绰号了.如果发现有这样的情况,那就请这位同学站到我站的地方来,让每个人都给他起个绰号.”黄老师这么一说,班上的同学还真不敢给别人起绰号了.可是,他们私下里还是偷偷地叫我“灰老鼠”.
现在,她就站在河岸上,像一个母夜叉.她两只手戳在腰上,说:“灰老鼠,你在干吗?你有没有搞错啊?提水提个半天,还以为你掉河里了.你搞什么名堂啊?灰老鼠,你,你干吗呢?你想累死我让我一个人大扫除啊,有没有搞错?”我最恨别人叫我灰老鼠,看着她机关似的嘴巴,我突然觉得血往脑门冲,一股怒气快速地蔓延到全身各处.我提起打好水的水桶重重地往地上顿去,一把扯住她的衣领,凶狠地说:“你,你什么意思?你再叫一句灰老鼠试试?”她的衣领被扯落到肩膀上,露出雪白的皮肤,和她吓惨的脸一样白.但是,更糟糕的事情来了.我们一起滑进了河里.那时的河水真脏,除了一股很浓的泥腥味,还有别的说不出来的味道.这种复杂的味道,先是从鼻子进去,接着是耳朵,再是嘴巴.我的身体好像被什么东西拉扯着往下沉,往看不见的地方沉……
我俩被人拉上来时,我的一只手还死死地拽着陈冬雪的衣领,她的胸露出了大半,那是发育了的女孩子的胸.我怎么都说不清掉河里的事,或许是人们都愿意自由想象,而拒绝听我的解释,这个事件变成了一个有颜色的事件,同学和老师都对我露出了古怪的表情.也因为这次的事,我还感染上了皮肤病.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味觉也变得怪异,不管什么东西,总能闻出那种黑暗的泥腥味.现在,我又闻到了那种泥腥味.
我沿着河继续往前走去.
光头的三轮车还停在门口.三轮车破破烂烂的,上面插了一块很大的牌子,歪歪扭扭写着“收购废品”.车斗里是空的,大喇叭躺着,也没了声音.狗大概熟悉我的气味,它在门里大声地叫唤了几下后,声音变得温和了些.
我最后一次见到光头是那天晚上.
那天下班有点迟,出厂门口的时候,我的自行车不小心碰了一下那个花蝴蝶一样的仓管小郑,把她的连衣裙扯了一个洞.然后,她就大声惊呼起来,搞得全厂门口的人都朝我们看,好像我欺负了她似的.我怯怯地跟她说了句对不起,她还是不依不饶的样子,说我是故意碰她的.她要我赔,不然就跟我没完.但我没钱啊,掏空口袋给她看了她才信.然后,她就锁上我的自行车,把钥匙拔走了.我正沮丧着,听到光头在对面哈哈大笑起来.那时,他就坐在阿勇小炒店的门口.
看到光头,我有些激动.那时,他就一个人坐在饭店门口最边上的那张桌子旁,旁边就是小卖店了.光头的右腿提起来放在凳子上,表情古怪地盯着饭店门口.他看到我朝他走过去,却收起笑脸,假装没看见.他旁边还坐了两桌客人,我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和他说钱的事.于是,我就隔着一米多的距离轻轻叫了一下光头,我说:“你在这里呀,你过来下,我有话跟你说.”在后塘,除了光头,没人会收我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该把货卖给谁.今年一共交了三次货,光头都拖着没给钱,他说才这么点货,也得等卖了才能倒腾出钱来.我想,光头是做这个生意的,总得讲信用吧,欠着就欠着吧,等到用钱的时候,再去跟他算账.
光头瞅了我一眼,不慌不忙地咽下一口酒,清了清嗓子,他说:“你有话就说呗?什么事啊?”
这种话我怎么可能当着别人的面大声嚷嚷.见光头没有起身的意思,我犹豫了一下,没有动,却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事了.我想,光头也不是笨的人,他应该能猜到我找他的意图.现在都过去大半年了,他也该把钱给我了.
光头又喝了一口酒,这酒的气味很冲,像从地底下冒上来似地有股很大的劲.他见我没有走开的意思,就说:“来来来,先陪我喝几杯.”
我不喜欢喝酒,但是为了那一千多块钱,我就留下来了.
光头从桌子下踢了张凳子给我,凳子上有些灰白色的可疑污渍,我弯下来吹了吹.他的狗走过来,围着我转了好几圈,还在我的鞋子上嗅了嗅.原来是我的脚踩着几个虾头了,我把脚提起来,看着狗把它们都拱进嘴里.地上的东西吃完后,狗站起来,前脚搭到光头的腿上,像个人似地站得老高.狗不停地看看我,又看看光头,口水挂下来滴到了地上.光头看看我,又看看狗,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了句:“女人啊,他妈的还不如狗呢.”光头似乎也有些不高兴,有什么心事似的.但他没有提为什么不高兴,只是让我喝酒.我闻到他嘴里喷出劣质白酒的气味,觉得酒精已经渗进他的皮肤了.但是这个气味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还有狗身上的那股酸臭味也在不停地冲进我的鼻子,我觉得喝不下酒了,就转过头小声地咳了一下.
隔壁那一桌在划拳,有个人快爬到桌子上了,他扯着对面一个人的领子灌酒,另一些人跟着起哄,还有一桌热热闹闹嘻嘻哈哈的,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喝了几口酒就喝不下了,看着光头喝,看着酒瓶子里的酒慢慢少下去.
酒瓶空了,光头提起来晃了晃,扔回到桌子上,然后站起来,晃悠悠地走到饭店里.在里面,他好像和谁争执了几句.过了好一会儿,他提着一瓶酒回来了.
后来,隔壁那桌划拳的人起身去结账了.我就试探地和光头提了钱的事,我说:“哥啊,现在手头紧,你能不能把以前的钱都给我?别人也追着我呢.”
光头的舌头有些打结,他说:“钱啊,好啊,有什么急的.才几个钱呀!”
这时候,那个女人从饭店里出来了.但是她并没有看我们,而是径直走到了我们隔壁那桌,搞得好像跟光头没什么关系似的.我看着她迅速地清点酒瓶,记到账单里,又回到了饭店里面.狗看到她兴奋地摇着尾巴追上去,却被她喝斥了一声.狗似乎挺没趣的,眼巴巴地待在门口继续摇尾巴.
光头有些生气地叫狗:“阿虎,回来.阿虎,滚回来.”
阿虎转头看看光头,又看看女主人,站着没有动.
光头又要倒酒,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就劝他少喝点,但光头突然就发火了,拿起酒杯扔向远处.酒杯没有砸到狗,却洒了我一身的酒.酒冰冰凉的,渗到我皮肤上却是火辣辣的,我忍不住“啊”地叫了一声.边上的人都放下筷子,抬头看我们,光头的女人也从厨房出来,站在门边上看我们.
光头站起来,没表情地瞅了一眼周围的人,冷冰冰地说:“畜生,都是见钱眼开的东西.”他的声音大起来.听上去像是骂狗,却好像在指桑骂槐.
饭店老板阿勇还在厨房里忙碌,他的声音压过油烟机呼呼的风扇声到达外面,好像在斥责帮厨的菜切得不好.热油在锅里滋滋作响,接着是哗啦一声巨响,什么东西倒进油锅了,一阵鲜美浓郁的香味随着油烟飘到了外面,又飘进了我的鼻子.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安静得我有些难受.我忍不住摸摸自己的脖子,真痛啊.
待我回过神时,光头已经从他的座位上走出来了.他的手指头戳到了我的鼻子.手指肉乎乎的,我闻见五香花生和龙虾的味道,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味.他莫名其妙地冲我喊起来:“你说,你说,这算哪回事呀?”
我很纳闷,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他,我问:“什么哪回事?”
他挥着手大声骂起来:“人心啊,全都掉钱窟窿里了.你,你也跟我呢.你这臭小子,现在也长本事了,要到外面来了,这是哪出呀!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欠下多少账了呢.”
我的脸刷的一下红了起来,喝了些酒,我觉得自己的舌头有点麻,耳朵里也嗡嗡响着.还想解释下,却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见我不说话,光头更生气了,脸绷得紫红.他的拳头砸到桌板上,连桌上的碗碟都怒气冲冲地跳了跳.光头有些站不稳,身体晃了几下,他说:“你小子欠揍吧,有种你再跟我提钱看看.钱,钱,你们就,就知道钱.什么东西!”
情形越来越不对,我知道他已经醉了,就准备走人.但是突然,他像箭一样冲过来抓住了我的肩膀.他的手像钢铁一般坚硬,他一使劲,我就被推倒在地上.我挣扎了一下没起来,屁股摔得很痛,胸口还被什么东西狠狠地硌了一下.我摸了一下,发现硌到我的是那几只铜坯.
光头还在骂,蹦出的家乡方言也是醉醺醺的.狗也在叫.晚上这事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是谁得罪了光头,他把我当成出气筒了.我觉得很委屈,凭什么光头欠我的钱,我还要像个孙子似的?而且,这个事情又说不清楚,没人会为我主持公道.那些看热闹的人都在笑:“哈哈,看哪,看看这只灰老鼠,哪里有人样……”
那天离开阿勇小炒店后,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了,就垂头丧气地在路上走着.后来,我走到河边洗了洗脖子上的酒,洗了以后,我觉得身上没那么痒了.天已经很黑了,似乎要下雨的样子.我挽起袖子,取下衣服里的铜坯放在布口袋里拿在手上,又打开领口的两颗扣子,把衣服往下拉了拉,让身体稍微透下气.河边的树叶和野草被风吹动起来,有一些树叶的腐烂气息到达我的鼻翼,居然挺好闻的.
这条路是村子里的新路,路的左边是河,右边连着一大片荒地.往里走是村子,往外走便是一个新建的工业区,为了回收工地里的建筑废料,光头把他的废品收购站也搬去了那里.不久以后,我工作的工厂也将搬到那里.我太熟悉这条路了,甚至认得路边的每一块石头和电线杆.我一边小声咒骂着光头,一边往前走.在我走着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从我身边跑过去.空空的路上,只有她形单影只地跑着.在我前面一米多远的地方,她似乎停顿了一下.就在那个间隙,我分辨出了她身上甜甜的酒香,浓艳的脂粉味和复杂的油烟味.现在,她身上还多了一种特别的味道,咸咸的,苦苦的,像眼泪被风吹干后留下的痕迹.我盯着她的背影仔细看了看,认出那身红色的啤酒推销员制服.哦,我还想起来,她脖子上挂了条亮闪闪的金项链.我有点弄不明白,不知道女人为什么喜欢在自己的脖子上挂这么个冷冰冰的东西,一不小心还会勒着脖子.金子的颜色和黄铜的颜色真像啊,可是,我那么多袋的黄铜,却抵不上她脖子上的这条链子.我在心里骂光头,真不是个东西,不肯和我结账,却有钱给女人买链子.
看着她的背影,我突然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以前那些在外面晃荡的日子.有时,我躲在弄堂口;有时,我贴着一堵灰色的墙壁;有时,就蹲在河边的荒草里.因为我穿着黑色的衣服,很难被人发现.当我突然挥着手跳出来时,那些女学生会被我吓一大跳,或者把我当成鬼怪拔腿就跑,她们的惨样把我乐得手舞足蹈.那时,我开心极了.有个事情让我打发时间,我就觉得身体不那么痒了,夜也不那么难熬了.直到有一次,我遇到了个女中学生.她大概因为什么事情落单了.前面是个村庄的三岔路口,眼看着就要追上她了,她突然停下来,捡起一块石头往我砸过来,一边喊着:“砸死你,砸死你这个坏人.”她的声音在颤抖,但是嗓子却又尖又细,像针一样扎到我的耳朵里.我想不明白,那么好的年纪,这个小姑娘怎么会那么狠毒,她比陈冬雪还要坏.我还想着怎么对付她时,那个没有路灯的地方却突然吼起一个男人浑重的声音:“干什么的?”我赶紧逃跑了.这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跟踪过女学生了,也似乎忘了曾经有过这么个事.
现在,我没有想吓唬她的意思.她的高跟鞋不好使,我小跑几步就跟上她了.她似乎在哭,样子伤心极了.我离她很近的时候,她才转头看了看我,然后使劲地吸了一下鼻子.她吸鼻子的声音很响,好像有多少眼泪都被吸到肚子里了似的.我很想帮她擦擦眼泪再摸摸她的头,但是,我不确定她会不会接受.而且,她穿着高跟鞋,比我还高了半个多头.
她还在哭,但她和我说话了,声音还很悲伤,她说:“你在这里干吗?”
是啊,我在这里干吗呢?好像是在等她似的.我想了想,说:“没干吗,散散步呢!吹吹酒气.你是不是也遇到烦心事了?这么晚了还一个人在外面.”
她又吸了下鼻子,这一下吸得很厉害,把眼泪和鼻子都抽空了.她跟我说:“嗯,烦死了.那个死人,莫名其妙地来跟我吵,家里吵了不够,还跑外面来吵.你看看怎么回事?他就见不得我好.”我想起刚敢于在饭店前面那一幕奇怪的情形,有些听明白了,她骂的人是光头.
胸口还很痛.我也想骂骂光头,整个一无赖嘛.但是,我怕她跟光头好了后又要来骂我,就忍住了.我觉得女人都不靠谱,吵了打了,她还是要回那个堆满废品的家.我就劝她:“两口子吵架是常有的,别往心里去,隔天就好了.你看你还得回家继续过日子呢!”
她不再说话.天很黑,我们并排走着,偶尔走过一个路灯杆,灯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瘦,看上去,我也很长很瘦.走着走着,我就有点后悔起来了,觉得刚敢于就不该和她说话,只要悄悄地从背后窜过去一把扯断那条链子,再迅速地往更黑的地方逃跑,她就追不上我了.她太悲伤了,反应就会变慢.路上那么空,河边的荒地那么黑,她肯定也不敢进去找我.现在,更糟心的是,我觉得自己的心开始变软了.我犹豫起来,不知道还要不要干那个事,我甚至同情她,觉得命运对她太不公平了.金项链的颜色和我每天摸的黄铜颜色差不多,但是挂在脖子上就显得柔软些,有了优美的曲线.从脖子再往上看,我就发现她长得并不好看.汗水从她的发际渗出来,脸上油乎乎的.她皮肤粗糙,五官都显大,不精致,尤其是嘴巴,上唇有些往外翻.她还抹了猩红的口红,使红色的嘴唇显得油腻腻,像海报上常看到的一些外国女人.我没有像老王那些人一样盯着她胸前的啤酒商标看,我弯下身去系了系鞋带,顺便不经意地问了句:“如果不回家的话,你准备去哪?”
再往前走就是空荡荡的工业区,离他们的小窝很近了.她在我前面停下来,左脚蹭了蹭右小腿,大概被虫子咬了一口.她没有回答我,好像在想什么事情.
是她先听到狗叫声的,微弱的光影里,我看到她的肩膀狠狠地抖动了一下.于是,我的心也一下子凉下来,觉得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果然,狗很快就跑过来了,围着她转了好几圈后,停下来敌意地看着我.狗哈哈地喘气,口水从它的舌尖滴到地上.她紧张地转身看了又看,然后,蹲下去牵住狗脖子上的项圈,抚了抚它的脑袋.再抬起头时,她很平静地问我:“你,敢不敢帮我教训光头?”
我愣住了,支吾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光头至少一百八十斤的体重,凭我的个头,三个也对付不了他一个人.
她又问:“做吗?”
我看看狗,又看看她.她的眼睛里有种异常冷静的东西,仿佛是愤恨的结晶.我想起那个眼神亮晶晶的女学生,她们的神情如出一辙.愤恨到极点时,她们都是会和人拼命的.
夜还在往更深的深处黑着.我仍在犹豫,光头摇摇摆摆地从远处走过来了.他的眼睛瞪得很大,连说出来的话也是醉醺醺的,他说:“你,你们在干什么?”同时,他的手掌往我的脑袋挥过来,我敏捷地闪开,没有被他打到.但他自己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那个女人大概是习惯性地想去扶住他,却没有料到他发起酒疯的后果.她刚走到他边上,一个很响的巴掌就甩到她脸上了,响声把夜撕开了一条缝.然后,他抓住了她的头发,把她揪住.这时,那只没用的狗却不响了,趴在地上呜呜地低声唤着.
女人的头被揪歪了,再往上一点,她的脚就会离开地面.她嗷嗷地叫起来,用左手抓他的脸,又用脚去踹他的膝盖,结果都是徒劳的,一只高跟鞋飞到我的脚边,差点砸到我.我想着要不要弯下身子去捡起来时,她仇恨地盯了我一眼.光头已经醉了,嗓门大得更加吓人,却有些麻木似地打着结.他一边揪着她,一边吼着:“你,你这个,.什么东西啊?啊?就会,勾三搭四,你,你们背着我干什么好事?”虽然有些摇晃,可他的身体还是那么魁梧,脸盘也很大,圆鼓鼓的眼珠里露出和往日一样冷峻的凶光.
我想走过去劝劝他,但是又很害怕.我低声下气地和他说:“光头,你先冷静冷静,我们有话好好说嘛!我们什么都没有干!你听我好好跟你说,你,你先放手,好不好?先放手!!”
我这么一说,他似乎更气了,手上又加了把劲,狠狠地把女人甩在了地上.
倒地时,她“啊”地尖叫了一声,然后,一只手捂着肩膀强撑起了上身.那时,我又看到她的眼神了,眼珠子里射出一种冷光照着我,我浑身颤抖了一下.我看到她内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她想抓起那只鞋子,把鞋跟对准光头的后脑勺,狠狠地砸过去……
光头摇晃着脑袋走过去,弯下身子要去拉扯她.我没有去捡那只鞋子,我掂了掂布口袋,那几只铜坯的分量抵得上一块砖头了,金属总是比鞋子要硬一些.
夜越来越黑了,风也停下来.路上没有一个人经过.渐渐地,我们听到了流水声.
灰老鼠论文参考资料:
该文评论,这是一篇关于经典灰老鼠专业范文可作为老鼠和灰老鼠和短篇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灰老鼠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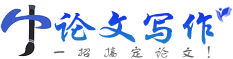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