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婚恋话语迷思》
该文是现当代类有关本科论文范文和婚恋话语迷思和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方面本科论文范文。
也许,像《霍小玉传》(蒋防)、《莺莺传》(元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冯梦龙)等这种始乱终弃的故事情节并非爱情文学的一种写作模式,它所昭示的其实正是爱情的某种深刻本质.因此,整个世界文学早期涉及的爱情主题中亦多盛行此结局.《克莱采奏鸣曲》(列夫·托尔斯泰)里的波兹内舍夫就是试图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证明所谓终生不渝的爱情“这种情形只有小说里才有,在现实中是从来没有的.在现实中,这种对于一个人超出于对其他人的爱恋,可能保持几年,不过这是很少见的,更多的是几个月,要不就是几个星期,几天,几小时”①.伏尔泰也说过:“有种种爱情,为了给爱情下个定义,简直不知从何说起.人们冒冒失失地把几天的虚情假意、有意无意的结合、缺乏尊敬的感情、登徒子的恣情纵欲、一种冷淡的习惯、一种浪漫的逢场作戏的举动、一种一试即罢的兴趣,都叫情.”②尽管它在五四时期正式成为一种启蒙话语之后,渐趋告别了始乱终弃的历史悲剧,但却也并没有就此彻底终结自身所制造的伤害.此时的作家们似乎大都尚未意识到,历来爱情最终撕毁的是彼此信任与忠诚的合约,并且导致的将永远是对弱小者的伤害;而既然在此种关系里处于弱势地位的总是女人,那么遭受伤害的对象便只能是女人.所以,不管艾玛(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在情人面前表现得有多么强势,最终被伤害的也还是她自己.子君(鲁迅《伤逝》)的命运不亦同样若此?恰是所谓的爱情将其逼上了绝路.再则,觉慧(巴金《家》)之于鸣凤的爱情又能怎样?对鸣凤而言,“但是他的爱也不能拯救她,反而给她添了一些痛苦的回忆.”最终,鸣凤仍只能带着这虚幻的爱情在孤寂中无助地死去.不难发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写作中,爱情从来就不是作为某种拯救或牺牲的力量而存在的③,例如祥子(老舍《骆驼祥子》)在拒绝小福子的爱情时竟然给出了这样充分的理由:“他还喜欢她,可是负不起养着两个弟弟和一个醉爸爸的责任!他不敢想虎妞一死,他便有了自由;虎妞也有虎妞的好处,至少是在经济上帮了他许多.他不敢想小福子要是死吃他一口,可是她这一家人都不会挣饭吃也千真万确.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在祥子眼里,爱情就是一件奢侈品,既然自己只是个穷人,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资格去爱小福子了.于是,他便可以眼睁睁看着小福子走向绝路.直至当代,这种历史情状依旧未见多少改观.如《黑骏马》(张承志)里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之间的爱情可谓纯真无瑕,但在索米娅遭到黄毛希拉的奸污之后,这种爱情的性质便随即发生了些许变化.变化首先是经由索米娅的眼神表现出来的.过去,索米娅的眼神是这样的:“黑暗中,她那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凝望着我,眸子深处那么晶莹.”而此刻,她的眼神却变成了这样:“她小心地、迟疑地盯着我,那眼光不仅使我感到陌生,而且似乎含着敌意的警惕.”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变化,就是因为在索米娅看来,丧失了的自己已不再纯洁,自然也就不配再拥有白音宝力格的爱情.对方的爱情价值是高贵的,自己的身体却已经没有了价值.漫长的爱情历史经验告知索米娅,她只能拿男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并且在其固有的单纯认知里,爱情从来就不是男人的牺牲和拯救;即使是牺牲和拯救,那也必是女人对于男人的牺牲和拯救,一如古老传说中的七仙女和田螺姑娘.命运似乎仅分配给了女人承受的权利,所以索米娅只能把男人的错误视为自己的错误.此外,她好像也没有爱的权利,而仅有被爱的权利.基于此,索米娅主动疏离了白音宝力格的爱情,她这样做其实不过就是在履行一个女人应尽的历史义务.也唯有如此,她才能够稍稍维护一下自己那点儿可怜的尊严.至于白音宝力格,他压根就考虑不到索米娅内心真正的痛苦,他所能想到的只是自己的痛苦和委屈,故此他仅存的渴念便是所谓的复仇.显而易见,白音宝力格更为关心的不是爱人的存在,乃是敌人的存在,因而此时全然占据着他心胸的只能是愤恨.结果,白音宝力格在索米娅最需要他抚慰的关头,却自以为无辜地收敛了自己的爱.这不计其数的悲伤爱情实例俨然是在向我们证明:爱情首先是利己主义的,而并非利他主义的给予.爱情只是令人们疯狂,主体会因占有和嫉妒的心理焦灼一度迷失自我.弗洛伊德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去认识爱情的实质的,在他那里,爱情始终就是一种变态的诉求④.伊格尔顿也一样是在病症的意义上来剖析爱情的实质的,他如此写道:“爱确实是一种疾病,它是我们本能中最邪恶、最不稳定、最容易出错的,而且其神圣与亵渎的方面如同物质与精神一样不可区分.”⑤没错,就是因为这种爱情,何塞刺死了卡门(梅里美《卡门》),奥赛罗勒死了德丝黛梦娜(莎士比亚《奥赛罗》).而且直到今天,爱情也仍旧从未停止过血淋淋的屠杀.这一追求完美的企图要么毁灭要么放弃,但是不管怎样,其结局都至少是一个人的大不幸.此外,我们也不难看到,在这林林总总的爱情故事里,婚姻常常是被排除在外的,它几乎被当成了与爱情全然无关的存在.于是,爱情自然固化为了非生产性的,以一种反生命的形式永远停留在理想的维度之上,甚至索性将现实的婚姻看作了死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所有已然步入婚姻的爱情,最终也都是为了消亡于婚姻之中.史罗华曾这样认为:“17世纪以来,欧洲兴起了一种强调权利与自发感情之间矛盾的文学,它把爱情的自由化与法律确认的婚姻对立起来.在中国文学中很难找到这类矛盾,即使存在着对‘放荡之爱’的兴趣和好奇之心,其性质也截然不同;‘放荡之爱’只出现在中国的小说之中,而且基本上没有感彩.”⑥在我看来,中西之间的此种不同,就其实质而言,乃是根基于自由意识的有无.诚然,爱情仅有作为一种自由的形式出现才是有其肯定性价值的,“正如人们看到的,体制初现端倪常常是通过压制爱情.”⑦爱情亦正是因此才有了被赋予正义反叛力量的可能,故而其意义必是出于对某种桎梏的反抗以及对个性权利的捍卫.也可以说,爱情只有以自由的面目现身时方是值得歌颂的,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中那力图挣脱世俗仇恨偏见的生死之恋,我们经由后世演绎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也应属此列.但在我们近代以降这迟到的爱情启蒙里,太多轰轰烈烈的情感实际上并不关乎这一主题,要看到,子君和涓生的爱情并没有夭折于对自我权利的抗争,而是自然死亡于婚姻的冷漠.当然,我们知道,鲁迅本就无意认同这样的爱情,可问题是,他也因此忽略了对于自由的认同.⑧
正是由于对爱情实质认知的惯有暧昧,使得我们总要翻来覆去地进行着不断的爱情历史启蒙.“鸳鸯蝴蝶派”对于爱情独立价值的确认还不等取得其合法性,便迅即遭到启蒙和革命文学的双重致命炮轰.每一个时代对于爱情似乎皆有着自己崭新的领悟,甚而让进化论变成了爱情思想的灵魂.可这一切又不过都是在挤抑婚姻的前提下启动的,一成不变的结论仍是喋喋不休地控诉着爱情无法在婚姻里存在.但是,这些激进的人们浑然不知,自己愈是乐于渲染爱情的纯粹、唯美以及高蹈,其实也就愈是表明其对现实的不满乃至憎恨.此种无根的爱情自一开始便注定了与婚姻不可调和的冲突,在他们眼里,爱情象征的乃是自由和幸福,而婚姻代表的则只能是奴役和痛苦.针对现实,他们一刻也不曾怀疑自我的理想也许是有失公正的.历经“”十年的爱情话语禁锢之后,人们只是试探性地思考了一下“爱情的位置”(刘心武《爱情的位置》),紧接着又迫不及待地重新审判起婚姻的羁绊来.《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就是这样再一次将爱情同婚姻毫不妥协地对立了起来,在婚姻面前,爱情显然是至高无上的.可以看出,作为文本叙述者的“我”还继续生活在封建专制的迫害想象里,她对爱情理直气壮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当成了一种反封建的现代性诉求.也就是基于这一原因,用爱情去挑战婚姻在她那里便成为某种毋庸置疑的革命性荣耀.为此,从头至尾,这位坚定的爱情追求者都能够毫不畏惧身为一个觉醒者的势孤力单.相反,她所流露出来的倒是颇有几分高高在上的沾沾自喜情绪:
也许我不必想这么许多,我们可以照大多数的家庭那样生活下去:生儿育女,厮守在一起,绝对地保持着法律所规定的忠诚……虽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在这点上,倒也不妨像几千年来人们所做过的那样,把婚姻当成一种传宗接代的工具,一种交换、买卖,而婚姻和爱情也可以是分离着的.既然许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为什么我就偏偏不可以照这样过下去呢?
这样的反问自然不是由于有了动摇的念头,而仅仅是想向人们交代一下自己那固有的“贼风入耳”所致的超凡脱俗“秉性”.当然,她比谁都明白,这样的秉性根本就不是什么缺点,恰是追索真理所必需的高贵品质.她的高高在上,她的沾沾自喜,也无不是与这种真理的追索息息相关.所以,她势必还要无休止地继续追问下去,所以,面对着自己的那个热烈追求者,她依然不能不问:“乔林,你为什么爱我?”随即,这位被追求者便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欣赏着对方“那宽阔的额头上难得出现的皱纹”,最后赐给他“一种怜悯和一种歉意”.接着就是“我的心被一种深刻的寂寞填满了”这种不无自得的伤感情绪,而这也是她能从对方的爱那里得到的唯一东西,爱带给她的仅仅是无以填补的空虚.无疑,爱在她这里不是回应,而只是等待回应,一种可以和她的呼唤在条件上完全相匹配的回应.可乔林的回应同她的呼唤却难以达成这样的匹配,所以她只能在曲高和寡的窘境中独自倾听着声声寂寞和凄清.她执着地期待着完美的爱情,因为她坚定地把自己想象成完美的了;虽然她很清楚自己在外在条件上并不完美,但也正是这种不完美反而刺激了她对内在条件上的完美追求,甚至因此可以无视外在条件上的完美,结果,仅仅在此方面具有优势的乔林就沦为了她借以表现自身清高的陪衬了.她的爱更像是某种基于补偿心理的待价而沽,内心的高傲严重阻碍着她爱的付出.爱之于她始终就是一种现实的难题,因为现实本身只能是不完美的.她不知道,恰是这种不完美才是爱真正存在的理由.爱一个人就是爱他的缺点,“由于爱人的缺点让我们能够接受自己的缺点,两个人由此才能够结合在一起”⑨.换言之,两个完美的人是不需要彼此相爱的,这就是爱的意义所在.爱压根不必像她那样一刻不停地唠叨着为什么,爱就是表达和行动,其本身便是答案.克尔凯郭尔说得好:“‘为什么’越少,爱情就越多,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此之中看见那真的东西.当然,对于那轻率的人,在之后确实会显示出这曾是一个小小的‘为什么’;对于严肃的人来说,这显示出来的则是一个极大的‘为什么’,这是让他高兴的.‘为什么’越少,越好.”⑩可是,这个爱情理想主义者所面对的现实本身永远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因为她在爱情当中寻求的自由必定会在现实所需的责任那里遭遇质疑.她越是痴迷于爱情审美性的自由,亦便越是疏离于现实伦理性的责任,而其后果则必是对此种自由的任性消费.正如作为文本叙述者母亲的钟雨,她在结婚之际难道不是自由的吗?然而,已经摆脱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命运的她却轻易就挥霍掉了自己的自由:“人在年轻的时候,并不一定了解自己追求的、需要的是什么,甚至别人的起哄也会促成一桩婚姻.”就这样,钟雨将自己不幸的婚姻完全归咎于年少时的无知,自己也因此就不必再为其担负任何责任了.在她这里,责任被从自由的整体结构中无动于衷地割离了出来.于是,一旦发现婚姻里已没有爱情,她首先想到的便是否定这桩婚姻,而不是重新去爱,去拯救婚姻的生命.她以为,爱情永远没有过错,错的只有婚姻.抑或说,自由没有错,错的只有责任.她的女儿“我”不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去认识爱情和婚姻的吗?——“而如果我们仅仅是遵从着法律和道义来承担彼此的责任和义务,那又是多么悲哀啊!那么,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问题的答案她自然清楚,她想说“有”,她想说“那就是爱情!”但对此她却疏漏了另一个“为什么”,即这种爱情可以是婚姻的开始,但它真能是婚姻的保证吗?此刻的显然无法让她拥有这样的预见:“为爱情而结婚的理想刚刚获得胜利,它的那些热情的支持者们便立即要求在爱情消亡的时候离婚的权利.”当然,这样的结局也压根不是她所愿意正视的,在她的观念里,爱情一定是永恒的,否则那便不是真正的爱情.鉴于此,所以她必然不能认可同母亲暗暗苦恋一生的那个“他”“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而选择的婚姻,尽管他的大义果断之举充满了崇高的意味.并且,尽管她也知道,对于自己的婚姻他并不是不满的:“逢到他看见那些由于‘爱情’而结合的夫妇又因为‘爱情’而生出无限的烦恼,他便会想:‘谢天谢地,我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可是我们生活得和睦、融洽,就像一个人的左膀右臂.”但她仍旧不会苟同他的这种看法和感觉,故此,这里的爱情被打上了引号,因为她坚信那不是什么爱情,就像她坚信爱不可能从婚姻里开始.所以,在她看来,他同那位遗孀之间的患难之爱不是爱,只有他和母亲之间那未曾表白过的爱才是真正的爱.
俨然,对爱情充满理想主义想象的她更期待为爱情所征服的那一刻怦然心动,她无法忍受爱情的世俗化,在她这里,生活之于爱情无异于精神上的阉割.然而她却并不清楚,被爱情征服了的主体已经彻底失去了自由,从而不得不屈服于那虚无缥缈的等待:“……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因为把婚姻等同于了可恶的世俗生活,所以爱情就只能悬置于空洞的理想之中了.而既然爱情必须远离生活方能得以保持其精神的存在,那么,这种绝对纯净的精神便成了非历史性的,即一种无法成长的存在.克尔凯郭尔说:“在人们征服的时候,人们持恒地忘记自己;而在人们占据的时候,人们则回想着自己,不是为了空虚地打发时间,而是带着所有可能的严肃.”这里的“征服”与“占据”所指涉的正是爱情和婚姻.相较于爱情,婚姻乃是一种时间上的拥有的状态,它创造着历史,成就着主体.而炽烈的爱情最怕冷淡,始终不敢面对婚姻生活里的平淡时光,诚如涓生在婚后对子君所说:“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还有:“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在涓生看来,如果没有爱情,婚姻即使是幸福的,那也是可怕的.对他而言,视觉上的观看总比内心的感受要来得更为真实和可靠,换句话说,双眼只能看到那不断运动和变化着的存在,而婚姻似乎委实难以满足视觉感官的此种期待.就这样,始终操心于外在和表面的眼睛不知不觉地就把主体放逐到了他者的位置,正如克尔凯郭尔指出的那样:“看,这就是你为什么畏惧和平和安宁和静止的原因了.只有在有着对抗的时候,你才处于你自身之中,但因此你就从来没有真正地处在你自身之中,而是不断地在自身之外.就是说,在你吸收占据了对立面的那一瞬间,就又会有宁静出现.因此你不敢进入这一瞬间;然而,结果就是这样,你和对立面相互面对面地对峙着,结果就是你不在你自身之中.”由此,克尔凯郭尔洞见到了婚姻的本质:“婚姻性的家庭生活就是如此,宁静、适度、低吟曼语;没有很多变化,然而又像水在潺潺流动,却只有着水流的旋律,对于那认识它的人是甜蜜的,对于他是甜蜜的恰恰因为他认识它;这一切都没有炫耀的光彩,然而偶尔一道光泽铺撒向这一切,却不打断那习惯性的进程,正如月亮的光线洒落在那水面上并且展示出它用来演奏其旋律的乐器.婚姻性的家庭生活就是如此.”较之于罗曼蒂克的爱情,克尔凯郭尔不能不更欣赏婚姻,即那深深扎根在婚姻形式里不易被发觉的宁静之爱.他以为,后者远比前者更具有审美性,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它才是历史性的真实存在:“罗曼蒂克的爱情在其自身之中继续保持处于抽象状态,而如果它无法得到任何外在的历史,那么,死亡就已经潜伏在那里等着了,因为它的永恒是幻象的.婚姻性的爱情以占据为开始,并且获得内在的历史.”罗曼蒂克的爱情所获得的历史是外在的,婚姻之爱获得的则是内在的历史,而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只有那内在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是,婚姻比爱情更需要持久,故而它有理由比爱情更懂得守护坚贞不渝的意义;至于爱情在此方面的表现则常常是极其表象化的,诚如拉罗什福科一语道破的那样:“爱情的坚贞不渝实际是一种不断的变化无常,这种变化使我们的心灵相继依附于我们的爱人的各种品质之上,给予其中一个以偏爱,又迅即转到另一个.因而,这种坚贞不渝不过是发生在同一主体中的一种停而复行的变易.”
毋庸讳言,《爱,是不能忘记的》所欲进行的婚姻启蒙是肤浅的,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它以自由意志名义对个体的合法性肯认因为背离了责任和历史,故而注定只能属于一场虚幻的追求.其主人公只知道婚姻必须自爱情开始,却不知道爱情也可从婚姻开始,更不会相信:“只有婚姻才能让爱情更显高贵.只有婚姻才能让爱情拥有恒久的形式.其他性爱的、美感的,以及所谓的初体验,这些东西总会销声匿迹.没有婚姻的证明,爱情也会悄然凋零.”她仅仅相信爱是唯一,爱是纯真,爱是永恒,可事实上,此种基于自我中心主义的非历史化想象不仅严重误解了婚姻,同样也严重误解了爱情本身.此种执着得近乎高傲的态度与真爱所需的谦卑情怀本已格格不入.要知道,被理想化了的爱情所关心的终是自我,它的付出首先是以对方的付出为前提的.在这种形式当中,真正的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两者间的交流也许足够顺畅,但那不过就是自言自语似的交流,因为交流在实质上乃是自我同他者的交流,这样的交流不追求顺畅,而更看重理解和宽容;它指向的是倾听而非倾诉,它以回应的方式同对方结成一体.依赖于彼此相互吸引的罗曼蒂克之爱则是排他性的,所有旁人以至连自己的孩子都可能是个搅扰,热恋着的双方只希望永久沉醉于爱的享乐.需要在此指出的是,这里的相互吸引必须是绝对的,仅有单方面的吸引则是万万不行的.我爱你的条件是你必须也同样爱我,否则,即使你回应了我的爱,我也不可能会接受.骄傲的爱者唯恐对方看低了自己,唯恐不够默契的交往会败坏自己关于爱情的完美想象.有鉴于此,我相信她们势必是理解不了萧涧秋之于文嫂(柔石《二月》)的爱的.在萧涧秋这里,令其无法承受的恰恰是完美的爱情.一方面,他爱恋着年轻美丽的陶岚,认为她“实在是一位稀有的可爱的人”;另一方面,则又深深同情于命运多舛的文嫂,为这孤儿寡母一家的不幸忧心忡忡.但相较而言,更能占据着萧涧秋心灵的总是后者,因为在品性上,“他是常要将他自己底快乐反映到人类底不幸的心上去的”.这个素来便有些忧郁的青年,每在陶岚的面前只能是更加的忧郁,而在从文嫂家出来之后,却可一反常态,“内心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微妙的愉悦”.很显然,对于文嫂的帮助无疑能够为他带来心安,同情令他的爱和固有的使命感初次在现实中结合在了一起;他的忧郁亦正来自这爱和使命感的无以落实.拥有使命感的爱赋予了萧涧秋崇高的存在感,因此,在一个寒冷和黑暗的时代,他终究不能独享一个人的温暖和光明,就像他在写给陶岚的信中说道:“我常常自己对自己这么大声叫:不要专计算你自己底幸福之量,因为现在不是一个自求幸福之量加增的时候.”为此,他同陶岚之间的爱情所能带给他的唯有歉然和不安.之前,在给后者的信中他还曾这么写道:“而且这样的社会,而且这样的国家,家庭的幸福,我是不希望得到了.”这个自认为“‘自由’是我底真谛”的人,同时也认为“家庭是自由的羁绊”.也就是说,此时此刻,爱情在他这里已然不是一种自由的体验,反倒甚至有可能成为自由的阻障.于是,在一个崇高者身上,幸福同自由发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那么,别无选择,萧涧秋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幸福.结果,爱只能变成一种痛苦,不过却是一种崇高的痛苦.之所以会痛苦,那是由于萧涧秋深感一个人爱之能力的有限:“我好似冬天寒夜里底炉火旁的一二星火花,倏忽便要消灭了.”事实上,萧涧秋的崇高也正是在这种悲剧性境遇中显现出的可贵光芒;面对无尽黑暗,即便自知无力驱散,却也绝不轻易妥协就范:“我是勇敢的,我也斗争的,我当预备好,待真的虎来时,我就照准它底额一!”萧涧秋所有的勇气和仇恨皆源于其内心如许深刻的爱,爱在他那里就是一场不用考量输赢的战斗:“人底全部生命就是和运命苦斗,我们应当战胜运命,到生命最后的一秒不能动弹为止.”他又说:“不过我是知道要失败才去做的.不是希望失败,是大概要失败.”此言表明的与其说是萧涧秋消极悲观的情绪,倒不如说是他对现实极为清醒的认知.为爱的命运所抉择的萧涧秋必须去战斗,但是,陶岚那里不是战场,他只能走向文嫂.在此意义上,文嫂就是他的爱.然而,坚信“除了爱情,人生还有什么呢?”的陶岚却难以理解这样的爱.所以,她不得不问:“你爱她吗?”即便得到了对方肯定的答复,她也仍然无法释怀,不仅是因为自己的爱,也是因为对方的爱;两种爱迥然相异,陶岚体量不出萧涧秋同情的深度,故而分享不了其爱之情感的升华.或许,她也可以为爱情做出牺牲,但这牺牲终究是为她自己的,它同萧涧秋为他人牺牲的爱相隔实在太远.
爱在萧涧秋那里没有为什么,只有果断的行动.他用实践诠释着爱是同情(sympathy)/共情(compassion)的真谛,就是这种情感使其有了不计后果的拯救:“莫非这样的妇人与孩子在这个国土内很多吗?救救妇人与孩子!”当然,不能不指出的是,萧涧秋并非一个基督意义上的泛爱论者,他对文嫂的爱绝非出于一时的冲动和偏执的理念.毕竟,文嫂与其不是一个毫无关联的陌路人,她为国殉难的丈夫本是自己的同窗.此种渊源当中存在着某种相似和共同的东西,也正是这种东西可以拉近二人彼此之间的距离.可以说,萧涧秋的责任感并不盲目,况且自一开始,他便非常注意提醒自己要把持住情感的理性:“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我接触了两种模型不同的女性底感情的飞沫,我几乎将自己拿来麻痹了!幸福么?苦痛吗?这还是一个开始.不过我应该当心,应该避开女子没有理智的目光的辉照.”对于萧涧秋而言,爱与心血来潮无关,爱与完美无关,“爱根本就是利他的,慷慨的,而根本就是自私的和索取性的”.这里没有施舍,这里没有可怜,这里只有平等和尊严.所以,文嫂不会以为萧涧秋的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赐予,虽然对此她也很有些许犹豫,虽然最终她选择了自杀,但那正如萧涧秋对陶慕侃所说的,“她为爱我和你底妹妹而出此的”.至此,我们终于可以看到这不是爱情的爱里所蕴涵着的超越一切个人之上的崇高力量.
这个曾经为了自由而不愿组建家庭的青年,却可以为了文嫂一家的苦难违背初衷,因为此时的爱就是他最大限度的自由.抑或说,他的自由就在同文嫂的婚姻里,而不是在和陶岚的爱情里.萧涧秋积极迎接了这个时代的挑战,找到了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存在价值;他明白,自己只有在对苦难的同情中才能够体验到真理的幸福.他用爱和痛苦书写出了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并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为崇高的人物,同时亦由此精彩诠释了“就其本质而言,纯粹的爱就是同情”这个道理.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读过柔石在同时期写作的另一个短篇《希望》,便可更能领会他之于爱情的理性态度,同时认识到《二月》所欲传达的爱确系有意为之.在前者那里,主人公李静文为了心仪的爱情甚至可以期盼临盆的妻子就此死去:“我虽不希望她死,可是她却真的死了,那我未来的爱的幸福,还有补偿的机会罢!爱情底滋味怎么样,我一些没有尝到过;恋爱的滋味,新婚的滋味,我真梦似的将自己底青春送过了.一个完全不识字的她,上字会掉头读作下字的,不,简直掉头也读出不出来!使我何等苦痛呢?”对于所谓爱情怀有的希望竟然能够使李静文变得如此冷漠绝情,显然爱在他的心灵里从来就没有同情的共鸣.这个“小脚而不识字的,简直不能同她在街上玩”的妻子对他来说,是压根不配享有其爱情的.毫无疑问,李静文爱的目光永远是望向高处的,他不可能俯身将爱给予真正需要爱的卑微众生.因为势利,也因为自私,李静文终究是无法像萧涧秋那样去爱的.他的爱情指向的不是奉献和拯救,乃是索取与谋杀,而这恰是柔石想要揭示给我们的爱情实质.
萧涧秋以其并不成功的经验告诉了我们:爱情是美丽的,但婚姻却是崇高的.“婚姻具有‘真理的力量’,可以让你看到自己的本相,看到你的一切缺点.”黑格尔甚至认为“婚姻本身应视为不能离异的,因为婚姻的目的是伦理性的,它是那样的崇高,以致其他一切都对它显得无能为力,而且都受它支配.婚姻不应该被所破坏,因为是服从它的”.婚姻比爱情更接近人生,爱情之花作为理想必须通过在婚姻里的成长结得硕果,而这也才是爱情的全部.爱情完全是个我独立意识觉醒之后的产物,它的自由是与快乐相生相伴的,它同婚姻契约的责任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发生了抵牾.当我们以爱情的理由谴责婚姻的时候,我们似乎就此否定了婚姻之爱的可能.其实,错误也许从来就不在婚姻,而是婚姻里的关系双方错认了婚姻的本质.过去,“婚姻无非是商业交易的法律外衣”;但在逐渐摆脱去封建权力的控制之后,我们发现,婚姻也并未因为爱情的自由而得以永恒.相反,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婚姻却由此加剧了解体的频率,或如贝克尔所说,“现代社会似乎成了一个多爱情婚恋与高离婚率并存的自相矛盾的结合体”.我们的婚姻始终存在着问题,尤其是随着女性自我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此种问题已然越发的突出.但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婚姻历史顽疾的一次集中性发作而已,它所意味的恰恰是疗愈的开端,而非婚姻死亡的征兆.只要家庭存在,只要我们继续信仰和依赖家庭的力量及其价值,婚姻就不会有消亡的可能.毕竟,“是婚姻起源于家庭,而不是家庭起源于婚姻”;家庭需要婚姻,婚姻因此必须是借以维系家庭利益的一种爱的形式;也只有在家庭这一空间里,利他主义情感才是某种最为自觉和见效的能量,并使个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庇护.此外,对于作为整体人类自身的持存来说,家庭的必要性亦绝非可有可无:“家庭存在是为了使社会存在,使社会像家庭一样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但是,与此同时,社会之所以存在,则因为在某一时刻出现了家庭.”家庭的重要性支撑着婚姻的重要性,既然我们不能根除家庭的存在,那也就不要妄想废除婚姻这一形式.或许就是为了弥合爱情与婚姻间难以规避的缝隙,黑格尔站在家庭的立场上否认了婚姻应该建立于爱的基础之上的观点,他指出:“爱既是感觉,所以在一切方面都容许偶然性,而这正是伦理性的东西所不应采取的形态.所以,应该对婚姻作更精确的规定如下: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这样就可以消除爱中一切倏忽即逝、反复无常的和主观的因素.”我以为,正确可行的思路应当是直面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重新审视家庭当中的性别伦理,甚至像巴特勒那样去考虑颠覆性别这一事实.必须祛除性别话语本身所固有的历史偏见,在一个平等的理性高度上展开之间的对话,让婚姻成为无可替代的伦理之爱的体验,而不是一种保障合法剥削和压迫传统的契约.必须清楚的是,对于爱情或婚姻,我们一直就存在着严重的误读,这进而一度深深阻碍了我们同家庭之间的血脉关联.五四时期以觉慧为代表的所谓“家庭的叛徒”的高调涌现,实质上便是对于伦理之爱的背叛,此种革命性姿态以个体自由权利的名义让家庭本身沦为了奴役的替罪羊.爱情也就是借助于此获得了高于婚姻家庭的权力.所以,陶岚可以光明正大地对萧涧秋说:“你只可否认家庭,你不能否认爱情.除了爱情,人生还有什么呢?”在时代自由主义精神的诉求之下,既有婚姻制度已然成为众矢之的,以致人们连婚姻本身都无法容忍了:“婚姻本也是古来传留、霸据、褊狭、欺伪的制度中的一种.但使吾们明白它的真作用,把对于它的心理改改,这种作万恶源泉的制度有什么不可去?有什么不该去?有什么不能去的?”好在当时亦有有识之士认识到:“过去之婚制,曰无目的的婚姻,曰嗣宗继业之婚姻.现在最流行之婚制,曰极端之恋爱自由的婚姻.未来之婚制,曰伦理的婚姻.”进而他大加倡导伦理的婚姻,称:“唯伦理的婚姻,所以使男女相对之爱情得其满足,世上数千载缔造经营之文明得其继续,万物中最高等生物之血种得其传衍.兼嗣宗继业的婚姻之善,而无其压迫自由与爱情之弊.兼恋爱自由的婚姻之善,而无其忽略传殖之弊.”可是,此时如饥似渴的自由爱欲已根本无心理会这明智的声音,离婚的现实潮流已势不可挡;不只是城市,也不只是男性,竟至连爱姑(鲁迅《离婚》)这样的乡下女性也主动要求离婚了.不过,情绪高涨的他们显然都还无法想象,在奋力冲出家庭的重围之后,自由爱情的结果又会怎样?其实很快,喜新厌旧的“围城”(钱钟书《围城》)心理便随即出现了:“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如今依然被人们奉为真知的片言只语难道不又是基于对婚姻的一种浅薄认知吗?它把主体的任性理解作为了自由完全可以原谅的冲动,结果势必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抛置了一边.而实质上,“义务仅仅限制主观性的任性……所以,义务所限制的并不是自由,而只是自由的抽象,即不自由.义务就是达到本质、获得肯定的自由.”从这一意义着眼,我们不能不说《围城》在此方面意欲传达的仅是某种似是而非的常识性感受罢了,它远不是什么自由真理的呈现.同样,终生以消灭离婚为己任的张大哥(老舍《离婚》)又真地明白婚姻的实质吗?他“楞拆七座庙,不破一门婚”的所有努力岂不皆是旧有“和”文化的历史惯性使然?而老舍针对这一形象的嘲讽,除了应和那一时代的强烈呼声之外,其之于婚姻所是又有几多可资借鉴的见地呢?
为了自由,人们宣称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离婚便因此有了充分且必要的理由.然而他们不知,爱情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不道德的产物;用道德指责婚姻,它暴露出的恰恰是离婚借口的虚伪和蛮横.再则,当自由与义务脱离关系时,人们的耐心底线将注定不断濒临挑战,从而会加剧蚕食着他们爱的情感.可是,由于迟迟认识不到这点,所以多年之后我们又重新站在了这个老问题的起点上.《爱,是不能忘记的》只是浅尝辄止地探讨了一下没有爱情的婚姻,随即《在同一地平线上》(张辛欣)便直接让离婚主题走上了议事日程.因为在此,婚姻能够给予女主人公的唯有对不公平境遇的发现:“在一起生活,他却什么也不能给我!他只打算让我爱他,却没有想到爱我、关心我.我觉得,他只要得到家庭的快乐和幸福,而我却要为此付出一切!”必须认识到,这位女主人公同丈夫倒是因为爱情步入婚姻的,但这爱情却即刻消失在了婚姻里.于是,没有爱的婚姻只能沦为一场博弈,沦为双方彼此斗智斗勇的算计.事实似乎是在证明,女人只有在爱情终止之后方能恢复理智的清醒.不过,没有了爱,惧怕亦随之到来,女主人公首先就感觉到了失去的不安:“不,等到我自己什么也没有了,无法和他在事业上、精神上对话,我仍然会失去他!当我没有把我的爱好和追求当作锻炼智力的游戏和装饰品,从开始到现在,我都无法保持我和他之间的平衡,无法维持这个家庭的平衡.我还是什么也得不到……”此种敏感的危机意识无疑是同女主人公相对弱势的心理有关,基于此,她在事业上的拼搏进取亦只能作为对这一心理的矫饰来看待了.而爱必须是建构于强大自我根基上的,否则它便无法采取果断的行动.那么,既然缺乏这种强大的自我,她的爱也就注定要沦陷于患得患失的矛盾挣扎之中了:
……我想起来,当我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我越爱他、想要依顺他,越会落入一种磁场偏离似的状况里,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呢?”“我上哪儿去了?”有时,我很想逃出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弄清属于我自己的全部思想、愿望和追求.
在这里,爱与自我之间竟然产生了难以调停的冲突;要么爱,要么自我,二者唯有其一.难道,爱不恰恰就是我们存在的一种方式吗?难道自我不正是通过爱才得以构建的吗?看来,她的爱已不是存在,而是异化为了占有,这也正是其婚后生活的真实情状,就像弗洛姆所指出的那样:
在求爱期,一方与另一方的关系还不肯定,爱着的人都在试图去赢得对方.他们生动活泼、富有吸引力和令人感兴趣,甚至可以说是美的,因为富有生气会美化一个人的面孔.这时,谁也没有占有谁,每个人都将其精力集中于存在,也就是说,去奉献和激励他人.
婚后的情况往往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婚约赋予双方占有对方的身体、感情和注意力的专利权.不用再去争取别的什么人了,因为爱情变成了人的占有物,变成了一份财产.依照弗洛姆的观点,所谓存在(to be)“是指一种生存方式,在这种生存方式中,人不占有什么,也不希求去占有什么,他心中充满欢乐,拥有创造性地去发挥自己的能力,以及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愿望”.而占有(to he)“这一生存方式并不是通过主体与客体之间一种有生命力的、创造性的过程建立起来的,它使客体和主体都成为物.两者之间是一种僵死的关系,而不是有生命力的关系”.由此说来,占有即意味着消费和失去;所以,不管是女主人公还是男主人公,婚后的占有关系决定了他们都必将在失去的恐惧中令共同曾有的深情归于死亡.即便那位男主人公看上去像个强者,他不也一样“总是在莫名的惶恐之中”吗?无论如何,惶恐的心灵里都不可能留有任何爱的余地.只要不改变这种相处模式,他们就永远不会拥有爱的能力.爱情对于双方仅仅是个开始,婚姻才是使其融入生活,成为存在的一种有效方式.就这一层面而言,他们的离婚是毫无意义的.毕竟,那不是缘于自由,乃是任性导致的结果.因此,他们的分道扬镳与其说获得的是个人的解放,倒不如说是甘愿奴役的公然招认.
当然,即使是出于双方自愿,离婚也总不会像结婚来得那么顺畅,一如《在同一地平线上》所呈现出的情景.于是,“第三者”的角色开始粉墨登场.公映于1980年代中期的影片《谁是第三者?》就是试图借助这个话题继续利用爱情向婚姻施压,并通过对离婚难这一事实的格外渲染,以实现对婚姻专制面相的揭露.不过,众所周知,离婚的动因和难题其实绝并不仅限于此.然而,或许也恰恰就是这多重困顿使得人们又凭空多出了一个“懒得离婚”(谌容《懒得离婚》)的理由.只是,这懒得离婚在生活态度上却要比离婚消极得多,婚姻主体已然在其中宣告了自己的死亡,表达的无非乃是对于婚姻的彻底绝望.但我想指明的是,此种绝望完全是基于习惯性的虚假认识,而并非属于主体洞穿婚姻本质后的一己之见.就拿主人公刘述怀来说,他对婚姻的认知遵循的仍旧是来自本能的寻常感受,即向惯有审美疲劳心理的投降:“我要说的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理想家庭,男女双方都需要一个乃至几个无话不谈的朋友.我说的是朋友,不是情人,不是时行的所谓‘婚外恋’.你想,夫妻二人,天长日久,昼夜厮守在一起,看烦了,听腻了,什么也不想说了……”因为固执地依赖着新鲜感,所以婚姻在刘述怀那里必定是没有任何魅力的.显然,他所需要的是,那么他又如何能区分所谓朋友和情人的不同呢?这不过就是五十步和百步的问题而已.事实上,由于内心真爱的匮乏,他压根就没有超越道德的勇气.可以说,刘述怀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弱者,他只会用抱怨替代心中的爱与思考.故而,他对现实的认知也只能是充满乏力感的:“唉!——我佩服那些离婚的人,他们有勇气,他们活得认真,他们对婚姻也认真.我嘛,虽说家庭不理想……咳,看透了,离不离都一样,懒得离!”不仅是畏于爱,同时亦畏于思考,刘述怀这种难得糊涂的婚姻状态令《懒得离婚》这部文本将中国文学相关话语的迷思几乎引向了绝境.但更为不幸的是,这还远非终结,电视剧《中国式离婚》将会在下一世纪以空前阴暗和冷酷的心理再次刷新诋毁婚姻的话语记录,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让婚姻关系正式跨入厚黑学时代.到此,我们对于婚姻的实质性理解依然看不出任何的进步,而是继续在互相伤害的迷途中遗忘着爱情的往事.我们照旧只愿为可能得到的爱情努力,却从不想为已拥有的婚姻再费心思.我们以为爱情是幸福,殊不知婚姻更是幸福,只是它比前者更需我们付出一生的努力而已.换言之,婚姻比爱情更需要爱;我们在其中所遭遇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自身已然变得吝啬于爱了.罗素说:“因此,有文化的男女从婚姻中得到幸福是可能的,但是他们必须满足几个条件.那就是,双方必须有绝对平等的感觉;对于相互间的自由不能有任何干涉;身体和肉体必须亲密无间;对于各种价值标准必须有某种相似之处.”总之,幸福的婚姻有赖于主体积极的自省和谦逊,它要求双方随时以理性保持着彼此交流的畅通.这是一条险情和惊奇并在的成长旅程.也许是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东方女性》(航鹰)曾试图借一个丈夫的出轨来唤起妻子对自我婚后角色的反思,以重建对于婚姻关系的信心.但是,这种信心仅仅是单纯建立在作为妻子的女性美德上的;她对自称“四十多岁了还像个年轻人”的丈夫背叛行为的原谅,体现出的与其说是爱毋如说是纵容.要知道,婚姻始终就是两个人的责任,一方仅因另一方对自己趣味的一时冷落便开始移情别恋,此举简直就是充满孩子气的轻率要挟,带有相当的耍赖成分.这位崇高的妻子最终可以感动迷失的丈夫,但却到底无法使其完成对于婚姻的重新认识,实现从自我利益向共有利益的关注.毕竟,她本人同样也有待对婚姻之爱的进一步认识.也正是这亟待提高的婚姻认识导致我们今天仍在不断向爱情做出让步,甚至企图用如“给爱情保鲜”这样的可笑方法去经营婚姻.而实际上,这完全是我们对自身耐心不足这一历史本性的虚伪妥协,它根本就没有可能将我们领向婚姻的幸福之路.我们应该明白,只要我们喜爱尝鲜的一贯口味不改,我们就注定品鉴不到婚姻真谛那永恒而深远的爱之喜悦.
海蒂曾经在她的调查报告中写道:“事实上,34%的女性相信:爱情关系不一定是生活幸福的首要因素.有的人还怀疑爱情关系是否真的必要……”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在今天会有何变化,以及国内的实际情形又是怎样?但我依然相信的是,这个时代的女性出路一定不是在她们的爱情关系里,她们必须认真考虑的是在婚姻关系里的权力再分配,而这个分配的原则所依据的只能是爱!■
现当代论文参考资料:
该文评论:上文是关于婚恋话语迷思和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方面的现当代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现当代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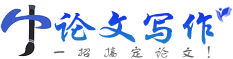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