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折不扣之锡林郭勒奥妮》
本文是不折不扣之锡林郭勒奥妮类有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与锡林郭勒奥妮和不折不扣和奥妮相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曾哲
曾哲 1956 年生于北京,早年从事诗歌创作,1980 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长篇小说《呼吸明天》《身体里的西部》《峡谷囚徒》,中篇小说集《一年级二年级》《藏北高原,我的羊皮袄》《一米二米三》,散文集《西路无碑》《离别北京的天》《转场·帕米尔高原的消息》,纪实报告文学《徒步·加德满都到拉萨》,诗集《远去的天》以及奥运建筑文学第一书《觉建筑》等20 余部.曾获第二、三届老舍文学奖,第三、五、六届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北京德艺双馨艺术家等三十多个奖项.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一级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他拉开栓,上膛.“啪……”声和旱獭子在空旷的绿野上倏地消失.马儿长嘶了一声.我和奥妮策马来到他面前,他却翻身跃马.三骑成“品”,草梢上飞鸟一般,驰向边境.牧羊犬大黄紧随,窜越隐现.在葳蕤的塔拉,连出一条虚线.奥妮沉静,不太专注的目光在颠簸中常常犹疑.偶尔扫上我一眼,目光交接,她的鞭子就在马屁股上炸响,破坏了“品”位,冲到最前.然后,又在不知不觉中与我并驾齐驱.
他,叫阿力克愣.今天没话,敦实的身体钉在马背一样.只有身后的,跳跳荡荡.蓝色的蒙袍紧束桔黄的布斯,黑马靴的皮腰儿映着一点夕红.刚敢于奥妮告诉我,太阳升起时,阿力克愣向她求婚了.
阿力克愣在等待,却把距离拉开.他说:她接受,就交给她.
20 年前写小说,折扣多.不敢写的只字不提,敢写的连篇累牍.有些事很敏感,敏感得好像躲不过去.我躲过去,到达了东乌珠穆沁旗.“不折不扣”是“解冻”,是精致,是填补.
额吉和奥妮央求我几次.好吧!我这一答应,从下午三点到晚巴晌,跪在蒙古包里的地毯上一通忙碌.搞定一百八十多个大水饺.馅儿简单:韭菜、肥羊肉丁、盐巴.成天介牛奶煮挂面,奶茶泡小米饭. 猛地来一次北京水饺,这晚饭,热闹了.
阿力克愣把父母接来.他家在东面十几里的塔拉.
奥妮撕了一张稿纸写了几个字,系在大黄的脖环,拍拍它屁股,狗儿钻出去,通知巴特尔也来就餐.三家到齐,晚上十一点.炉子中粪火熊熊,毡包里湿乎乎水气.饺子,每个人细细咀嚼,像吃山珍海味.击掌,伸出拇指.饭后.人们散去.马蹄声,消失在凌晨三点.
奥妮和额吉不想睡,俩人叨咕了一阵,举着蜡烛,打开佛龛下边的躺柜.我跟柜子一样,躺靠在一大摞被褥上.
奥尼眼睛水亮,盯住我.我感到手脚没了位置,就坐起来.
额吉拿出个沉甸甸的绸包裹,红一层,黄一层.
打开,是个单筒望远镜,两尺来长.年头久,上面的黄铜没了光泽.
额吉递给我说:这是奥妮爸爸的,是奥妮爷爷传下来的.传到奥妮这辈儿,没了男孩儿,就收着.筹谋,等奥妮领回个男人,再传.
我举到眼前,调着焦距.镜中,额吉和奥妮满脸的欣喜.欣喜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捂嘴;一会儿疑惑.铜质感,把历史凝固得凉丝丝的.手掌心很安逸,抱在怀里摸了又摸,爱不释手.
奥妮趴在我耳边:“留下吧!”
我心怀一紧,把望远镜轻轻放在地桌上.留给我?
我留下?
额吉开始为我铺床.两个褥子,很厚很软.
夜,悄悄静.一只大草鼠,在我脸上爬过去.
我真是奥妮从草原里领回来的.
奥妮说,那天她是在苏木供销社买完东西回家的路上.下午清亮的阳光,让白马上的她很愉悦.翻过一个塔拉她开始唱歌,第二个塔拉哼起长调,当进入又一个塔拉时,她没了心思.没了心思,松了缰绳,由了马儿信步.就在这时,她发现绿茵茵的草地里,蜷缩着一个人.腿脚边,立着军用大背包.浅棕色的上衣,像一团枯草.本来已经过去,奥妮也准备快马加鞭,半个小时到家.但她忽然觉得这事儿新奇.是饿死的?是路过打尖的?假如是路人,怎么走进这么深的草原来?管他呢,先回家再说.奥妮抖了缰绳,坐骑撒开花儿.
日头,突然被翻滚的乌云遮蔽,草原风吹来暗淡.
奥妮拉住马头,犹豫.她想那人不管死活,一定是外乡人.祭敖包的季节马上就到,一场雨会下好几天,气温骤降.独自路人没遮没掩,在雨中不冻死也容易迷失.这儿离边境近,再走到国外去.想到这,她又来了警觉,万一他要是北京跑出来的逃犯呢?
奥妮,掉转马头.
再次回到那个塔拉时,奥尼愣住了.没有,连个人影儿都没有.西面的黑云更加浓重,翻卷而来的云团,夹着雷鸣闪电.奥妮策马高岗,四周观望寂静.判定这是个逃犯,此人一定是在向西走.她一抖缰绳,飞马追赶.稀疏的雨点儿像大豆,砸在她簇新绿色的袍子上,噗噗做响.她有些后悔,后悔自己的犹豫不决.又一道闪电,奥妮看到了,她很得意自己的判断.可如此天气,那人却脚步悠闲,似乎对即将到来的大雨,毫不在意.
那人是我.军用雨衣的后背鼓鼓囊囊,形象是个大驼子.
奥妮驱马急停在我的面前,堵住了去路.雪白的坐骑被勒得过猛,前蹄腾空,然后落在草地,焦躁不安地踩踏着.一个在马上,一个在草地间.我先招呼,奥妮后发问.你一句,我一句,开始对话.
“你好!”“不用瞎客气,你是干什么的?”“走路的!”“去哪?”“不知道.”“真可疑,你没目的地?”“走路就是目的.”“从哪来的你也不知道?”“北京.”“那就是了.”“是什么?”“跟我走吧!”“去哪?”“到我家,躲雨.”“这雨一会儿就过去,雷声大雨点稀.不怕,谢谢啦!”“这雨保不其要下三天三夜,你会冻死的.”“能死在草原上,很安逸.”“原来你是来找死的.”“和你没关系.自己走自己的路吧!”“你是逃犯?”
“你才是逃犯.”我凶巴巴大吼一声,不再搭理,戴上雨帽准备离开.其实我不是很想离开,从西乌旗一路走来,喘气的都没见过.满眼只是绿色,连压缩饼干吃起来也是青草味儿.刚刚看到这么个同类,喜欢还喜欢不过来呢,更甭提可以在她家歇歇脚.可这位蒙古族姑娘不友好,说话带刺儿,惹不起躲了吧.但我估计难以脱身,看这丫头秉性不会罢休.没曾想,奥妮不仅没再言语,而且一动没动.我琢磨是自己的无礼吼叫吓住人家闺女了,就心怀歉意地低下头,想抓紧赶路.这雨真要下几天几夜,糟糕透顶.溜之是大吉.
我想错了.就在我绕过马屁股的时候,奥妮抓了马耳朵根儿一下.马儿尥起蹶子,仅仅一蹄子,把个五尺高的我踢翻在地,半个身子抽筋儿似的地疼痛.
我左腿的后腿肚子,被踢起一个大筋疙瘩.
就这样,我被奥妮掳到拜音图嘎嘎查塔拉,掳到她家.
塔拉,就是山丘之间平缓的草场.后来我在塔拉,放牧奥尼家的一千多只羊.是绵羊,并不雪白.两只牧羊犬大黄和小黄,做帮手.有吃有住,日子好过,我安宁下来.放羊是个闲散活儿,有黄狗看着,我常常骑马四处乱逛:南去石头城废墟;东到碧水清澈的淖尔;西边走马边境沿线.边境线上勒缰定神儿,这一带的牧草更好,但绝少放牧的.空旷的天穹,找不到太阳.
我知道,在单筒望远镜中,她一直注视着我.
说奥尼注视我,不如说我时刻在想着她.数十天的同吃同住,数十天的关怀照顾,我心里有一种东西在滋生.有情,有虑.
那是刚住进奥尼家的第三天,我躺在蒙古包里看书.前所未有,一辆吉普车停在南山岗.有人下车和背着粪篓的额吉搭话.额吉指指我这边,车子就飞速开了下来.全副武装的仨冲进来把我围住说,检查.我看了他们的,是旗局的,当然得积极配合.
过后喝茶时,我跟头头讲:一听额吉说我在蒙古包,你们就该打道回府.为什么?简单,这儿离边境二三十里,逃犯要越境早没影儿了,还等着你们?头头说:是是是,有道理有道理.整个旗都在传说,一说北京,人人敏感.核实一下,不是逃犯最好.他应诺谦卑得可疑.我正琢磨,他下巴掂在我肩膀说:您没问题,这家人有问题.传说他家有一杆德国毛瑟,女子是神射,百发百中.这还了得?私人持,犯国法.您看到过她拿吗?我很干脆:没有!这不是谎话.他笑容可掬:也是,您刚来还不熟,多住几天.北京人有觉悟,细观察,回到旗上来揭发.酒我请,政府给您披红又戴花.再有,咱的话保密.走了,留下我一肚子心事儿.
我住的时间不短了,准备上路,继续流浪.
傍晚巴特尔快马来找我,说明天是阴历六月初十,大吉大利,他要结婚.行吧!难得凑到的热闹.奥尼和额吉也去.
三十多里地,不经我黄膘马跑.太阳儿刚在头顶上打斜,已经看见碧绿的塔拉六个雪白的蒙古包.坐北向南,扇面排开.这里盛行喝草原白酒,六十五度.我不知哪来的勇气,来者不拒就喝高了.大概凌晨四点,接亲队伍出发.趁乱趁大家都顾不上我,晃晃悠悠踉跄出来,晕头转向地钻进一个安静的毡包里,倒头大睡.醒来,再瞧四周,全是妇女小孩.哄笑中,我羞愧地爬出这专门为妇孺准备的住处.
我躲闪开,蹿到另一个毡包.见里边人坐满,便蹬上门槛,蹲着借火点烟.突然有女人大吼,紧接着我后背,实实在在落上了重重的几拳.刚敢于的尴尬还没过去,我跳起就跑.那女人疯子似地追打,直到我逃进草地,直到看热闹的人帮助奥妮把她拉走.
我一屁股坐进草丛,活该是我忘记了告诫:门槛不能踩,是规矩,是风俗.成吉思汗手创的《札撒法典》记:“如有人被食物噎住,立刻拉出杀掉;如有人脚踏门槛,亦处以极刑”.当我再回到蒙古包前,一名壮汉正用马鞭子抽打刚敢于捶我的那个妇女.女人的袍子已经抽破,一只垂在外边.我劝,男人大吼:打我的老婆,是她打了我的客人,碍你哪道沟子事!我抬胳膊去护,也挨了火辣辣一鞭子,那汉子才停手.再看女人,还在怒视我.
婚礼回来,我继续放羊,同时收拾行装.奥妮像变了一个人,和我形影不离,但不言声.
终于有一天奥尼问我:“你是从北京跑出来的逃犯? ”
我猜测,她是在婚礼上听到了什么.“不是! ”
说完又加了一句:“不信我,马上离开.”
“我信!”奥妮的脸色缓和过来.
这天深夜,牧羊犬叫得狂风一般.羊圈里,也炸了窝.十几只草原狼,在月光下,蹒跚于草丛.我大喊大叫,扔石头,挥舞铁锨.狼们却稳住阵脚,不慌不乱,私毫没有却步.
羊圈门太低矮,我是挡不住的.咋办?我不知咋好.狼群闪动的眼睛,愣使草原明亮许多.我甚至看清头狼嘴巴,横叼着一根儿雪白的棒骨.额吉说过,叼骨头的狼最凶猛,一口能咬死一头五岁的牛,只咬不吃.一根儿棒骨在嘴,能活十五年.我以为是传说.
我心里发慌,两腿僵硬.但不能让奥妮她们瞧不起,我坚持着嚎叫着挥舞着.即便叼骨头狼突然加快了脚步,飞速地冲向我时,也没撒丫子逃跑,铁锹照样高高举着.全身僵硬,僵硬得几乎没有能力放下.我似乎已经感觉到,尖利的狼齿在撕咬血肉的疼痛.
“啪! ”一声响,从我的耳边似乎带走了我一绺头发,射向狼群.不偏不倚,正好打掉头狼嘴里的骨头.我激灵一下,像被什么东西点化了,玩命地冲向前去.仅一,狼们溃乱.一骑马的女子,从我身边跃过.提的姿态,月色勾勒的身影.奥妮,真帅.
过了一阵儿,奥妮策马返回来,跳下抱住我的胳膊:“没事儿吧? ”我没话,没话是因为我惊魂未定.为了掩饰,我撒手铁锹,摘下奥妮身上的单筒望远镜,假装寻觅.黑咕隆咚,啥也看不见,看不见也看.我的思想和眼睛,在浓浓的夜色里,寻找奥妮刚刚奔驰的英姿.心下说:这个女子,太神了.神射,不是讹传.
那根儿头棒骨,坚硬无比,沉重如铁,而且雪白光滑得像被打磨过一样.我要留下当个纪念,奥妮摇头.我不解,待要问时,被一脸严肃的额吉拿走.我诧异:“额吉这是拿哪去?”
奥妮笑答:“送到草原里.”
“为什么?”
“那是它们的信物图腾标志,还给它们,没必要结仇.”
巴特尔说,这根棒骨,是狼祖先的大腿骨.有它,就有牢固的狼群,如同蜂王跟蜜蜂的关系.失去它,狼儿们就会得上瘟病,成了疯狂的散兵游勇.白天黑夜地在草原上四处乱窜,不仅咬羊咬牛咬草原上所有的生命,人就更不放过了.
我还有疑问:“那奥妮把它打掉,仇就已经结下了啊?”
“是,这个仇大了,我们这一带的牛羊会在几天内都被咬死.”
“还给它们呢?”
“头狼叼走,带着狼群远离.最起码这几个塔拉,今后不会再见.”
果然,在未来的日子里,狼群没再骚扰.
告别.
“回去吧! 不用再送了!”我勒马侧身说.
“送!”奥妮很坚决.
“老话,送君千里…….”我强笑.
“你真不是逃犯? ”奥妮问.
“不是! 怎么又问?”我皱皱眉头.
“那你非走边境线干嘛?”奥妮又问.
“看看!”我轻描淡写不愿多说.要分手了,别不愉快.
“不许越过边境,草原没有差别! ”今天的奥妮,严厉如初.
“没看,怎么知道?”我随意应和.其实我已经去过两次了.
“送你这个.”奥尼说着勒住马,摘下单筒望远镜.
我打转马头接过,左肩右斜.同时注意到,那杆长,挎在了奥尼的鞍子上.赶紧嘱咐她:“要收起来,像单筒望远镜收在柜子里一样,再不要使用.”
“望远镜别总是老背着,常看看,迷不了路! ”
奥尼诚心.
“迷不了! ”然后我话题一转大喊“阿力克愣,你怎么想?”
此时的阿力克愣,有意识躲着,马不停蹄地往前.
跑着跑着,又不情愿,划了弧线,拐向右面的山岗上站定.
奥妮大声地问:“阿力克愣,你怎么想?”
我举起望远镜.晴好的天空下,阿力克愣双眉紧锁,一直在盯着我.脸沉沉的,和阳光,和湛蓝,很不协调.
“我走了你们就结婚吗?”我回头问奥妮.
“你还回来吗?”奥妮反问.
“婚礼选在秋季的比较多,是吧?”我岔开话题.
“你这么走下去,到哪儿是一站?”奥妮也不为难我.
“下一站就是一站.要注意的是,赶紧把藏好.”我强横地说.
奥妮不再说话,若有所思.太阳打了几斜,三匹马被一道耕翻了青草的土地拦住.我从望远镜中瞭望,耕土像一条黑色的鞋带,东西延伸,无始无终.“做什么用?”我问.
悄悄过来的阿力克愣抢着回答:“边界线.”生硬,但终于说话了.
可惜! 人类的界限,也殃及到大自然.真不如蒙古先人,以石块堆起敖包,标志疆界.但我更有惦记:“阿力克愣,你要帮奥尼把藏起来,要不麻烦就大啦!”
阿力克愣:“归她了,我不管.”
“没辙,听天由命吧!奥妮问你,我是什么人?”
阿力克愣沉默着.奥妮追问:“他干嘛老说,真是逃犯吧?”
“绝不会!是逃犯的.”阿力克愣声调怪异.
我向阿力克愣,伸出大拇指.
“你怎么这么肯定!?”奥妮笑了,笑得很轻松.
“逃犯,他不配.”阿力克愣的话,狠巴巴的.
“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不配当逃犯?”奥妮收敛笑容.
“他不配.他不敢承担.”阿力克愣一副蔑视的眼神.
天,连个逃犯都不配!我差点儿栽下马.赶紧告别,别太僵.
我挥挥手,催马.顺着犁翻的黑土地边沿儿,向南.转过一个土丘,回头瞅瞅没了他俩,才信马由缰.漫步,独享分离的个中滋味儿,想一想阿力克愣对我的评说.我是不敢承担吗?我是!不敢承担都市的嘈杂、不平、寂寞、枯燥;不敢承担奥妮的热情和爱的挽留;不敢承担普通平凡的生活.不仅不承担别人,更不承担自己.自己什么都承担,却让大自然、让草原、让善良的人们、让骏马、让无休止的路,承担我.
我——是逃犯,不折不扣.
逃犯和越境孪生.我反应过来时,响了.啪——,我的右肋,像被铁棍子拦腰狠狠击打了一下,浑身酥麻震痛.震痛下行,穿过脚蹬子抵达指尖儿;震痛上行,直戳脑瓜顶儿.马儿嘶鸣马儿惊了马儿不听了使唤,在草原胡乱狂奔.我腾出手抡起马鞭的刹那,看见东土岗上,奥妮正端着.
我勒不住,鞭打也没用.马儿不顾一切,一会儿西,一会儿南.
马儿跑累了就回来了.在水塘喝了一阵水,便轰隆倒下,把我甩进淖尔.我爬上岸,仰面躺在草坡.
凌晨,我在露水中苏醒.倒伏的黄膘马,已冰凉僵硬.我把被奥妮的打烂的单筒望远镜,挂在它的耳朵上.
没再回头,我继续赶路.
责任编辑:潘 灵
不折不扣之锡林郭勒奥妮论文参考资料:
该文总结,此文是一篇关于锡林郭勒奥妮和不折不扣和奥妮方面的不折不扣之锡林郭勒奥妮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不折不扣之锡林郭勒奥妮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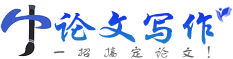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