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年鉴》
本文是年鉴类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和秋天年鉴方面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柿 子
柿子红了.2017年深秋仅记一笔.五株柿树,由皮口镇山中移栽,移栽前一番举棋不定,拖延,以为天寒仍需等待,至春再深一层,譬如谷雨,大地暖透,农田播种之时,尔耳.其实是出于无知,园林工亦哭笑不得,大呼太晚.七九河开,雁来,而惊蛰二月节,蛰虫惊走,树木转醒,根系活动旺盛,移栽正好,至于北方春日迟迟,亦不可拖过谷雨.于是仓皇补填新土,柿树蜂拥而至,挤满小庭院,晚清明十日有余,眼看便见谷雨.树木扎根抽芽,随后蜡质般花瓣绽开四片,一簇簇藏在厚实油绿的叶片间,想是去年的汁液,陈年老底,不可用尽,便翻遍油绿,花果逐一除去,以续养元气.园林工亦怀揣担虞,再三告诫,不可把新树累着.心知肚明,但手下稍稍留情,花朵便迅速逃逸,迅速在暖风中坐果,尤其够不到的枝头向天而立,柿子偷活,由小及大,由青转红.喜鹊耐心守候,午后人影皆无便是大好时光,林木间跳跃挑剔,大快朵颐.柿子红软,身上留下伤口.
见过一幅小画,始终不忘怀.仅一个桃子,红艳饱满,搁张皱纸上——包装纸,还是刚刚用过的废宣纸?说不清归说不清,但觉着万般皆好,都很有时光有质感,留有人体特别是手的温度,否则人真是寂寥.桃子在天在地,在大自然,何尝不是人心所爱,人爱一枚桃子,如同爱南瓜,爱白菜,爱鸭跖草,路边车前草,其实也是在爱他所遗失的,他所渴望,爱它与我们的并列,平等.画心上方留白,重墨题诗,亦十分触目:“桃栗三年,柿八年,达摩九年,我一生.”是日本小说家武者小路实笃的笔墨,保有他一贯的风格,拙朴诚挚.因止庵先生采用,此画印在其随笔集《旦暮贴》封面,我由此有幸目睹.前年秋人在彦根,木村先生免费教授日语,每周三晚课,穿过金桂花芬芳馥郁的清凉月夜,我去上过她几堂课,还尝到她家庭院新摘的柿子,“柿子”,她用日语教我说.课间闲聊,讲起儿时,她母亲在院子里栽下一棵柿子树,柿树八年结果,“柿八年”,她再用日语教我说.年复一年充满期盼,特别特别着急.听她讲述时,我看到柿树那八年不疾不徐,丰盈自在,止为自身的开花结果而从容准备,始终都是,在要着自己的结果.八年也是把钝剪刀,缓慢裁剪一大把童年光阴,待果压枝头,已别豆蔻年华.以万世之久,已身之短,旦暮一遇,何其不易.
柿树八年,中国也这样说,我对木村先生笑语.2017年秋,柿子自由地红了,春夏叠加,也不过三季.被喜鹊吃过,也还红下去.从山中移栽庭院,之前柿树已有几年?之前我所不知道的,可否算它们的前世?或许它们怜我,知晓我没有那么多的八年可待,便把时光偷换,哪怕主干还不及碗口粗,枝杈低矮伸手可及,早在仲秋前,有两株树便张灯结彩了一般,红彤彤果实绚烂于枝头,天空也由此更加湛蓝,远远向后退去.春夏更迭,北方持续高温,大连仅几场细雨或零星小雨,不湿地皮,五月下旬《新商报》载,降水量为二十八年来同期最少,入夏小水库干涸见底,长到中途的农田大量遭放弃,草黄于七月,而月入,高温这根病水银,头卡在温度计刻度上线,不死不活降不下来.其间七月,我们的一个兄弟死了,有诗歌为证,他辞世之地,入夜开始落雨,通宵达旦,漫天细雨,在唱安魂曲.都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过悲其所悲耳.亦知他并未从生命树上真正跌落,他是木守,悲伤便减.那一夜辽南大地,高温中旱,统统照旧.日本古诗有句,大意为:“昨天还见过的人,听闻他死了虽然惊讶,然而我不也在这长夜的梦中.”夜梦中也醒着的人,真是凤毛麟角.而渺小如我,常常只是说,生,就是千万般的眷恋.但不过,不可生得不成样子.可以想象柿树细小苍白的根须,于陌生土壤里醒转来是怎样地急切而用力,一寸寸寻求生长,饮不同来路水,不同质地水,地底深处蒸腾的水汽,太阳落山后水管子偶尔浇注的自来水,已有根系不足,又生出新的幼须,渴呀渴呀渴死了,每一枚叶子都在空中大喊,不出声的叶子是因枯作一团,拿不出力气,呼喊是粒砾石,它们举不动,这些都在催促根须加倍地工作,以纤细如发的幼须——小小的脊骨——穿透泥沙,摩挲粗粝的岩石,与后者争锋夺路.你看到吗?看到它们的内部,它们隐藏的深处,不可知的黑暗,无法剖开亦难以历数的年轮,处处藏着微物之神.即便障碍如岩石者,亘古而来,不知年岁,身体里同样住着不死的微物之神.生长极其缓慢,更难丈量植物的离离戚戚,最矮那棵柿树亦远远高于我,供我在树下伫立,穿过树木的呼吸,猫跑过来,在地上打滚,用沙土洗澡,月夜虫鸣之音渐稀,只知道寄寓的这块地方,彼此那么接近,眉目相接便是心爱,没有哪一个更高,也没有哪一个更低.我学会了细目低垂,不尽欢喜,怀着一点微凉的慈悲,也面带微笑.
木守.微博有朋友说,日本人称最后没被摘走的秋柿为木守.庭院里看见受伤的木守,也许千真万确,生,就是千万般的眷恋.哪怕你死了,哪怕你很老.
急急如律令
陪父亲返乡拖在中秋过后,动意已久,各忙各事,始终文齐武不齐,突然空闲就来了,就都说不早不晚,趁着秋色.我们都带上莱卡相机,好多存储卡,还格外备下棉衣.城市不知季节已变换,我想自己已足够敏感,而且身边的事是,二十四节气,每逢交替,微信朋友圈诗赋画墨,酒食药茶,一波比一波来得殷切,虽说由虚拟之手传递,但全都在提醒你.要烙春饼啊,要吃饺子,要饮菊花酒.自立春到惊蛰,再到处暑白露,清冽自然,脚步细碎,节气乐章每拍打一拍,我便觉得慢了下来,悠然见南山,真好似回到从前农耕时代.然几经递换,堆积下来的节气中,惊起而长嗟的感觉更甚,更欺身,只是太快了,一切都在飞转,心下转而更是迷失,不知所向,若皓皓白雪,广漠无垠.毕竟不是幼时家中墙上挂的日历头,一张张地撕,撕下的那一页那一日,都存在了心里,撕到最后,也还知道薄厚,知道万物的有增有减.
一入乡下方才知道,我们都是在唱歌,用文字唱,用喉咙唱,用千娇百媚没处安放的身子唱.苹果等在枝头,玉米等在对面背阳的山坡,全都急声豁豁,苹果红皮,玉米黄褐衣,也着了火似的.于是深悔这疏忽而冒失的还乡,心中暗感愧疚,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不知道说什么为好.自知天性里的倔强羞怯向来狠狠集中在嘴巴上,要是由嘴上功夫而定,我是天下最坏的情人.所以世人曾一致认为我是眼睛最好,生得最美,诚挚情深澄澈如水.但现在沧桑降临,双目已老,早已学会漠视,声色不动,我只看小叔叔一眼,便把目光移开,不再看他,尤其不再看他那双手,那十指每一处骨节弯曲有如树瘤,要是伸手去摸一摸,恐怕比石头要硬.正当寒露,景象深秋,却是寒气暗生,半月后便是霜降了,说农历九月十五一过便进入晚秋,那多半在指南方,在北方,霜降冬即开始,霜白水寒,急急如律令,全在高喊要抢下这档空隙,苹果不摘,玉米棒不掰,终年汗水便付之东流.要是仍旧月夜捣衣,那阵阵砧声此时肯定急促,寸寸紧逼,只为乡间的粮食和蔬果,而不关良人,无涉征衣.这么简单的常识,我们生活在城里,根本想不到.
以一道山谷为界,北山玉米,南山向阳坡果树遍布,从山脚直至半山腰,仰头极目望去,红绿色交织层层叠叠,不见尽处.山静似太古,却并非日长如小年,风急云滚,人世的日子全在这里.我们中午抵达,上午小叔叔全家人还在山里,一家四口劳力,计划好用十天摘下苹果,农人的额头,无不箍一圈季节的符咒,轻重缓急,生死一线,他们用额头内的那个痛点来碰触时令.叔叔心中担忧,明天后天,哪日一旦变天,草黄果坠,全不值钱.粮贱果贱同等伤农.玉米可以先不管,余下几日再收,唯独苹果,急急急.堂弟两口帮忙烧好午饭,米饭未沾又急忙进山,上午摘下的一堆苹果等待装箱.午后我们进山,在果园四下转过,上上下下,始终未见他们身影,只闻远处人语隐约,时断时续,婶婶说,是他俩在那边干活,在装苹果.女人负责剪去苹果把,一只只剪好,装箱时果才不伤.全家早先议定,卖苹果钱归小辈,玉米钱归老辈.昨夜落雨,今朝太阳照样升起,我心说这可真好.这些钱大半攥在老天爷手里,它要是不想放,什么都是空.往山下走去,叔婶前后相随,不离左右.更远处,山峦松柏苍翠,其间夹杂十几行几十行落叶乔木,正是秋叶转色,红黄赭褐,层层尽染,铺陈出几道彩带如火如荼,又肃穆苍茫,我们回身远眺,竟没拍照.
山谷底自然踩出小径,沿山脚边伸向远方.路边陈年积叶腐质土烂泥杂处,黝黑不辨,雨淋日晒,它们像不知时月岁岁发酵,散发出草叶熟烂的浓烈气味,溪水隐藏其间蜿蜒流过,一片片在腐叶间跳动,水星闪烁.发现草丛间一辆不带轱辘的巨型手推车,不,形制和大小更接近阿拉斯加那种狗拉雪橇.这家伙可定名为铁雪橇,横竖几根粗铁管焊接组成,我以两手相抬,纹丝不动.运送苹果另辟出一条专道,但毕竟山路过陡,面包车上不去,就赖这辆自制铁雪橇,不过上下全凭人力,肩扛手拉,跌爬滚打,道路也已深深拖出两道沟壑.早有苹果坠落在地,每一棵树下,三五成群,但并不准备要它们了.我随手拣个,硕大而红艳,人转出了山脚,苹果还没吃完.每咬一口,清凉沁心,果汁甜得叫人眼里几乎涌出泪水.婶婶曾伸手要抢,要摘压弯枝头的苹果给我吃,被我拦下,手头这只够好,即便着地,一点伤没有.小叔叔六十岁出头不久,十多年前因为祖父丧事同处几天,现在看突然发现他矮了,已不是高个头,从脸颊到手腕,皮包裹又瘦又硬的骨头,唯脚踝偶尔露出的皮肤仍旧白如新雪.他浑身几乎没肉,上下一套迷彩服,农忙时在野,农闲时人都歇了,他还打乡间零工,父亲说他是个好艺人,邻里泥瓦活木匠活,样样不得离他.这么拼命,已不是一年两年,七年八年,十年二十年.我知道事情不至于特别糟,但还是心揣不该有的不忍,觉得多吃树上的一个苹果,就是在多吃他身上的肉.往山下去,苹果在左,玉米在右.邻田已开始广收玉米,雇工每日一百块,包一顿午饭.婶婶说太贵了.她家大人四个,苹果入箱后,就去掰玉米.Q下山时说这样做格局太小.我下山时说钱就是命,命就是钱.父亲下山时,什么也没说.
清早辞别.车已启动即将上路,后备箱塞满,不劳而获的两箱苹果,两大袋山梨,四长串还没晒透的山梨干,还有在城里买给母亲的她渴念之物,一大堆绿茄子.山梨干是父亲指名所要,他儿时零食,秋冬在手,而今太多年没有吃到,胃早已老了,断舍离还很远,只记着年少的那几口.堂弟夫妇起早进山,留老两口送行.小叔叔立在车外,几步远外,用那张树瘤指节手在脸上撸过一把,又撸一把,羞于给我们看到他的眼中老泪,却又想看我们.汽车绝尘而去,好让他们快快上山.
还 乡
父亲的词典里,有很多词语我不会用.比方说,沙胡鲁.幼时常常听他说,沙胡鲁炸酱吃,极好.其实就是小花泥鳅,长大后我弄明白,沙胡鲁为满语.乡下泥鳅各种吃法,诸如泥鳅钻豆腐,城里则孩子贪玩,每年夏天都从浑河里摸几条泥鳅,带回家养在罐头瓶里,瓶太小,鱼盘在瓶底,动也不动,不吃不喝,不居泥土,也可以活上很久.泥鳅原是最种皮实的鱼.中年早过,颓唐便无事乱翻书,又知道满语还称泥鳅为船钉鱼,惊讶有多少名词叠加.这在中原眼里,一定会被视之为鄙野.雅者如《诗经》中《鱼丽》,千古吟诵,那时沙胡鲁船钉鱼,都在哪儿呢.“鱼丽于罶,鲿鲨./君子有酒,旨且多.//鱼丽于罶,鲂鳢./君子有酒,多且旨……”宴飨宾客时,就这样唱,雅正有度.鲿鱼鲨鱼鲂鱼鳢鱼鰋鱼鲤鱼,鱼在竹笼,历历录录地跳;酒也是,美而且多,多而且美,美而且不尽.丽,是说鱼跳的样子——历历录录,真是生命里的大活泼.父亲50年代末曾进省城沈阳看齐白石画展,有幅画上面几条小鱼和一只钓鱼钩,老人题道:“大鱼小鱼都来”,字迹歪歪扭扭,父亲虽非没齿不忘,也曾深情写进文字里,止因它恰好投进了父亲始终童稚未泯活泼泼的心影.
火炕.倒不陌生,但听说也是鄙野的,我便常觉羞愧难当.先驱章太炎曾专门著文论北方火炕,“北方文化,日就鄙野,原因非一,有一事最可厌恶者,则火炕是已”.睡火炕不好,“终日炀火,脑识昏聩,筋络弛缓,地藏本寒,而女子发育反早,未及衰老,形色已枯”.先生特别想化导北方,以为“以屏去火炕为亟”.父亲1946年随父返乡,1950年进城求学,寒暑假返乡下老屋,思想感情版画创作早属于乡村,2017年秋他皓首还乡,最先对付不了的,便是火炕.有些词语还可以弃之不用,可做动词练习,火炕却好似谁也去不动的,它词性稳固,只有火和泥,火转化为泥固定下来,恒久温热,熨帖尽日操劳疲惫不堪的血肉筋骨.不幸的是,身体也有忘性,或者说忘性本来自于身体.父亲已八十有三,动身前曾几度悲从中来,自叹这将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回归故里,沿途秋色变换,他深处自身的激动之中,亦根本没顾得上想起父母已逝,冷静一点说,他在返还的,将栖身的,其实是其弟弟——我小叔叔的家.火炕变得半生半熟,身体完全不适,烙饼似的翻来倒去,彻夜辗转.被褥应该从炕头撤到炕梢,第二天临睡前他才想起,才一夜好觉.
不眠之际,如烟往事全挤在路上,纷至沓来,白日山坡摘的一小捧覆盆子却跌回到过去,在光的旋涡里急遽地倒退.来来往往,无始无终,唯独人例外,找不到老屋那扇门了.实际早不是老屋,祖上房基地前后分建两宅,老少分住,亦难怪爹爹糊涂.
抵乡那日中午,在村边道路好一阵兜转,像三个迷路小孩,指不出家门在哪儿.父亲指挥还该在前,我反驳说不,记得一进村口便是,可村口在哪儿?道路以西满目玉米,那块良田一望无际,十二年前秋天还是水稻.循父亲微弱的记忆继续向前,但是错了,又折返再寻,路上不见来人,选一条胡同里进去再问.有家院落停两个男人,往蹦蹦车搬货同时说话,我在院外门口站住,问谁谁谁住在哪儿?我小心翼翼,谁谁谁是小叔叔大名,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说出这名字,三个音节,又硬又涩又苦,从来不允许我用嘴巴说出来,一说出来就是这村庄的敌人,我几乎喘不过气,下意识感到害怕,怕一听到这名字即有鞋子飞过来打我.但是没有,年轻男人笑着说,他就住后街,西头第二个门就是.不过他不在家,在山里正忙着呢.我才意识到,时过境迁,时代到底翻篇了,我借身旁门框立稳,暗自松口长气,为着他的那张笑脸几乎要哭了出来.记忆深处里小叔叔,出名的“地富反坏右”子女,小学四年级被撵出校门,开始劳动,遍做乡间活计.母亲常说:“小叔叔长得多好看,大眼睛忽闪忽闪的,长睫毛,白白净净,伏在炕沿上看你.奶奶撵他走开,刚从外边进来,看寒气冲孩子脑门上……”说的是我出生时,母亲去乡下坐月子.
父亲夜里要解手.新屋楼上楼下,依旧是旱厕所,独在院门外.父亲起夜披衣踏出院门,一抬头,竟是满天星斗,繁花似锦.他记起东北农谚,大毛楞出,二毛楞撵,三毛楞出来白瞪眼.三个毛楞是三颗星,东北“鄙野”,用土话给天宇星命名,且辈辈以口相传,以至于没法与天文学术语对接互文,对世界解释不了哪个毛楞是哪颗星,最后没法清晰交代,毛楞星便愈渐熹微.毛楞一词很难描述,多用于人行为处事上,是指懵懂冒失,凡事一头栽进去自己尚丈二和尚,其实是一种状态.满语说毛楞二怔,父母常用来责骂自家小儿.也有睡觉睡毛楞了,小儿从床上一头惊起,睁大眼睛不辨这世界,父母便又要心疼,煦风微雨,告诉他你在哪里.毛楞里有点爱.
父亲明白正值子夜,该是二毛楞当空,他在繁星中久久寻找最亮的那颗.虽说星垂平野,二毛楞到底没法确信,其时万籁俱静,农人沉睡.次夜父亲睡个好觉,为三毛楞星特地早起.他穿戴整齐,手执相机.大毛楞在西,三毛楞在东,毋庸置疑.他早知三毛楞是启明星,是金星,就在自身东方偏南,隔过人家屋檐,远处前山山角,眼见一星独照,其时晨光熹微,慢慢三毛楞星即将隐没,皆因天下大白,故知东北何以戏谑它白瞪眼.
启明星即长庚星,出西名长庚,出东名启明,在昏为长庚,在晨为启明,故《诗经》有曰:“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大毛楞三毛楞,同一颗星矣.二毛楞呢,有说是天狼星.不考.
父亲说农事依天象,决起.农人辛苦劳作,长庚出西熄灯睡觉,启明星在东,家家户户已冒起炊烟,饭后下地就田,世代早睡早起.年根底日子才红火,可以歇息得一时慵懒,清早马车进城置办年货,小孩尽日期待,晚上能得两根红蜡头,几粒白沾果红沾果.沾果,北方零食,白砂糖衣,裹熟花生,我们幼时呼之花生沾.补记.
由大毛楞星想到昴星,二十八星宿之一.昴星曰髦头,又曰旄头,唐人李贺“秋静见旄头”,卫象“辽东老将鬓成雪,犹向旄头夜夜看”,可借来存象.旄头稳坐,与行星无干.再记.
锈 带
我儿时尝语“他们乡下人”,为父亲喝住.你祖父曾祖高祖下至我,都是乡下人,你也是乡下人.祖父曾祖高祖再往上天祖,都生在乡下,殁后葬在乡下,我心说我不是.早些年在长青墓园买块地,父亲阻拦,说他身后将要回乡下祖坟,我说你不在这,我以后去哪,一闻此言,他便作罢.还乡途中父亲第一次说起,我在后座悄悄湿了眼眶.父亲烈祖自河北束鹿迁徙抚顺,再没离开.人生时离乡,死后注定离乡.我本想自己死了骨灰撒向大海,远一点,从土地离开,可父亲作罢,我也得作罢.无意中,一句话就成契约,所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Q曾说北方人实诚.恐怕连我的心都是泥做的,真不好.
说我是抚顺人.以浑河划界,我曾住北岸,Q住南岸,年少我们不曾相识,我是北方之北.浑河流向自东向西,两岸为河谷冲积平原,但楼宇密集高低参差,道路纵横犬牙交错,后来者,早已无从记取平原的面容.说回抚顺,也只是寻访旧地.没有家了,在这儿.头夜住进酒店有些晚,掀开房间窗帘一角往外看,黑漆漆,压得眼睛生疼,我手捂住眼,盲人般摸回床上,埋首拱进大枕头里.说是旧地,也一样迷路.一样是昨天的秋日,剪得极圆,薄薄贴在灰蓝天幕上,不那么明亮.套件毛衣嫌冷,多加一件又热,只见路上行人个个身穿棉袄了.不去打量面孔,知道不会熟悉,在外三四十年,认识的人也不认识了.连我自己都老了.穿过兴仁街市场,两排一长溜灰铁皮房,一面门上剩半块玻璃,肮脏得很,照人尚且可以,别嫌太糊就行,我驻足细看几眼,认不出自己.
转来转去,在找一栋不复存在的红砖楼.二十年前,红砖楼早已拆除,重起了新楼,找是找那块地方.连名字都叫不出的地方,看哪哪像,又哪都不像.红砖楼也有剩残,一口块块锈膏药,还没被揭去,贴在灰色楼宇间,倒都像是外来户,病容满面的样子,看着总有几分似曾相识.灰楼新起也显着老,一幢幢身躯岂止是庞大吓人,才二十来岁形色就枯了,该不是火炕睡的吧.拣着道逼仄进退,眼前件件敝败得这样子,心里踉跄厌烦,又怀着希望.折身重回到兴仁街市场入口,让一栋栋红砖楼旧地复演,在记忆里倒推,历数,不信变得(忘得)那么厉害.终还算得来,疑疑惑惑,找到了那块地方,所谓旧地,只见上面横陈一幢七层民居楼,灰色又像是橙白色,铝合金窗框,家家蓝绿色玻璃,东西数数,共十个单元,我小时候是五个单元,一目了然,现在翻倍了但基本看不见门洞,车库一排大龅牙似的向前突出,咬合住地面,楼门被咽进去,卡在嗓眼里不出来.听说有儿时玩伴仍住在楼里,大半生没动窝,早晚在牙缝里进进出出,心里该有多灰暗.秋草明亮,沿车库房檐簇簇耸立,秋风起了,还未转黄,似乎找对了地方.
有一样很奇怪,在楼角转弯之际,本来无风,一股熟悉的臭味生起,我人已走过去又返身,见是马葫芦,四周一堆下水粪便不知掏了有多久,黑乎乎满地散落.一时间竟觉自己没有长大,仍旧独自站在儿时的大院里,天寒地冻,掏过的粪便水结成冰,男孩子在上边划小冰车,巴掌大一块板,下边铁片滑刀,只一片刀,故叫它单腿驴,两根细铁钎左右手支撑,以脚尖蹲在上面,飞速转圈,相互追逐.极有难度,我弟弟玩不来.转身离开之际,想臭气不变,马葫芦依旧会堵,依旧有人在掏.
离开后走有一刻钟路,到底又拦下个妇女确认.果然她领我们又回到那幢楼,远远指着说,就这块地方.脑里便想起曾读过的一首诗,男人手指脚下说:掘开它!Q追问道,就是这地窝子吗?我第一次听说地窝子这词,第一遍没懂,听女人跟着重复,立刻无师自通.什么都能拆除,地窝子似乎例外.
红砖楼在身体里成疾,去岁冬月在金泽,傍晚回酒店,路上远见一幢红砖楼醒目孤立着,斜阳把一整面红砖墙全部照亮,遍镀金箔似的,同时所有窗子灯火通明,两下光辉相接相映,静穆亦饱含温情,刹那间心下特别感动.张爱玲说红砖似是外来的,英国德国最普遍,因为看到台湾仿佛一直在用红砖,她猜大概是因当地的土质.一言蔽之,用抚顺土话说,全是两和水,台湾的或我曾蜗居过的.少时红砖楼,样式照搬苏联,烧砖就取高尔山脚下泥土,而今屈指一算,苏联解体二十六年.
一首歌名叫《Sugar Man》,小糖人,一度听至沉迷.在夜深人静时,看到70年代底特律街头一家小酒馆,这首歌在烛光中摇曳,微弱而不安,歌手嗓音澄澈,但越澄澈越绝尘,人越被彻底放逐,想要回来时,找不着路了.旧本抄写下歌词,找出来翻到那页,“小糖人,请快一点/因为这一切已让我疲惫/给你这枚蓝色硬币/你能不能帮我带回/我五彩斑斓的梦境/你带来了银色有魔法的船/我们跳跃着,喝汽水/还有甜美的玛丽珍”.一首现代诗.有一种迷离,或者说是光怪陆离.情境色调曲调,各处都可坐下来,在里面待一阵.从疲惫到逃离,到梦境,从蓝色到五彩斑斓,到银色,从恳请到虚弱的幻象,生出了一百只脚似的,来回跳跃着,给人以不安,又拽着人使劲地往下,坠落,沉沦.我曾跟Q说:“其实这是嗑药.”纵是喜欢,也不敢多听.回忆也是个小糖人.
抚顺煤都.煤在西露天矿大坑底部裸露.黑金子.马可·波罗在狱中这样向同伴口述道,定义他在中国所见的煤,一个词足够.乌黑发亮,从皮肤到心,怎样的燃料,驱逐饥饿,黑暗,寒冷,烤干雨雪打透的厚衣裳,在深夜读诗.但黑金子是修辞.大坑是的.日本人攫取抚顺煤炭四十年,他们站在黑金子这边,还是站在大坑这边?1901年井工开采,1914年露天开采,1938年日人大露天计划完成,西露天矿大坑有多骄傲啊,在中国乃至亚洲雄居首位,50年代大坑步入旺盛期,有统计说,共和国后,累计开采煤炭1.9亿吨,90年代大坑终于累坍,资源枯竭,借一句《红楼梦》的话——渐渐露出下世的光景.
小学时作文,下笔动辄写“三十里煤海”,大脑空白,根本不知三十里坑究竟多广大.西露天矿博物馆记:矿坑东西长6.6公里,南北2.2公里,矿坑总面积10.87公里.大坑曾部分回填,故笔下的三十里煤海,仍作数.秋高气爽,大坑竟看不真切,恐高症发作,离大坑坑边几步远,还是怕自己掉下去.是在大坑西,相机让人束手无奈,莫说全景,取半都难,只眼前一角,收进镜头.大坑在镜头外兀自斜行,扩张,大坑低海平面400米,形成深壑,且壑中有壑,沟壑层叠,很多“之”字形排列跌宕曲折,像很多节旋律,一节急促,一节舒缓,形散神不散的样子.其间铁轨土路交错密布,铁轨尤其抢眼,层层盘旋下行,术语描述是盘道,一盘道二盘道直至十三盘道,若是层层盘道立满地灯,在黑夜亮起,我们定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宇宙天体,比行星轨道还要多一圈圈环绕,真是像的,椭圆形的轨迹,流动飞行最为优美的弧线.只是说大坑深广.还有竖梯天梯,Q年少时,有段时间放学后,常顺竖梯独自下到坑底,拣泡线或废铁,曾经一度泡线成奇货,家家拿来编帘子,夏天挂在门上挡苍蝇,人外进内出,门帘子一绺绺摔下来直打脸,现在想,那要拣多少泡线才够呢?并非遍地泡线,他人又瘦小,一下一上要整个下午,好在坑底遇见工人,也给他喝碗消暑绿豆汤,去得就更来劲了.
坑底人小不见,几辆翻斗车零星作业,运煤车橘红,甲壳虫般从坑底沿土道向上缓缓爬行.俯瞰大坑满眼黄绿色,是绿色页岩,又一层油母页岩,色呈黄褐,岩层次第排列,尽头便是煤,快燃尽了.绿色页岩油母页岩及煤,距今皆四到六亿年,几亿年全堆在眼前,无遮无拦的,好像把心也掏了出来,捧着它对我说,看看吧,我就这些.是,我也拿不出更多,站在厚沙砾上,心木木的,无悲无喜,身子倒是觉着有些凉.只是老而已,百年击败了几亿年,我希望大坑不死,给时间立据.橘红色甲壳虫身背最黑最亮的老煤,缓缓爬到地面,驶上马路去.夕阳西斜,大坑灰绿绿不见尽头,金色余晖薄薄落下,锈味从灰绿色上泛泛浮起,东一抹西一抹的.知道了,大坑是一座倒扣的山峦.
大坑在浑河南,我在浑河北.金秋,我半世说自己抚顺人,出生以来始见大坑.
【责任编辑】 宁珍志
年鉴论文参考资料:
上文总结:此文是适合秋天年鉴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年鉴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年鉴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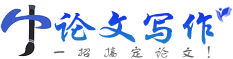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