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爱从何来?笔走龙蛇四十年:《陈思和文集》出版发布与会摘要》
本文是研讨会方面有关论文范本和《陈思和文集》和笔走龙蛇和从何来方面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编者按:
在陈思和先生看来, “教育、出版以及人文学术思想的传播”,三位一体才能构成知识分子的理想岗位.先生一生践行自己所言的“理想岗位”.在研究岗位上,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提出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民间理论” “潜在写作” “岗位意识” “无名与共名” “先锋与常态”等学术概念和理论,并组织、倡导和参与“重写文学史” “人文精神寻思”等影响深远的学术讨论.在研究界和批评界有着持续和强有力的影响.在教书育人上,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学教育家,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很多都成为专业领域内的佼佼者,或各大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在出版上,先生策划出版的“火凤凰系列文丛” “逼近世纪末人文书系”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80后批评家文丛”等,影响深远.
此次出版的七卷本《陈思和文集》,前三卷为当代文学评论、第四卷为现代名著文本细读、第五卷为巴金研究、第六卷为文学史研究、第七卷为散文与回忆录.虽因篇幅所限,先生的许多理论成果如有关比较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先生的大量读书笔记、旧体诗词未能收入,但文集已经基本上将先生的“面相”烘托了出来.
先生文集的出版,乃学术界和出版界一大盛事,国内著名学者种批评家近六十人聚集珠海,共话先生之成就.因篇幅,本文节选了部分发言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郭小东(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他是从研究他的那些对象,慢慢地接近他们,最后与他们为伍,最后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个.
广东人民出版社做出这个选择,非常准确,而且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今天好像看的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它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和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所留下来的痕迹,很多很多方面吧,都会起到一种很重大的作用.第二呢,我要祝贺思和先生,这个祝贺积累了四十年,在四十年前,我跟思和、剑晖这样的一些老朋友,还有吴亮、许子东,我们这一帮,那个时候叫青年批评家,在北京、在上海、在厦门、在海南岛,在80年代初期,我们经常在一起参与各种各样的会议、研讨等等.在我们这帮朋友中,陈思和先生他年龄不是最大的,但他是最成熟,也最具有老大哥风范的.我们大部分人是从知青中来的,而他不是,他的阅历可能比我们更沉着一些,那个时候我们在私下里面议论,我们觉得,将来最有条件而且最有资格而且最有希望,走到最后、最终、取得较大成就的,可能就是像思和先生这样的人.他有一个很好的位置,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书,然后他为人很谦和,思想又特别地锐利,而且他没有任何顾及自己个人的一些后顾之忧的东西,他把他自己全部贡献给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建设,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他一到大学里就有名师指导,自己又特别地勤奋刻苦,眼光非常犀利,他所接触的或者他所从事的起点非常高,重写文学史,文学的整体观,这些都不要说了,他研究的对象就是巴金、胡风这样一批“五四”时期最优秀的作家、学人.我想呢,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两个起点,一个是“五四”前后吧,现在有推到近代1875年去,那就另当别论了;另一个就是80年代.我觉得80年代的文学启蒙、救亡和复兴,可能要比 “五四”更具有当代中国的现代意义和现代性,同样都是在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撕裂的一个时代里面,但是80年代这种考验,对一个文学研究的个体而言,可能更为严峻,因为空间比“五四”时期要小得多,但是它的天地、视野,要比“五四”那个时候开阔得多.种种先天的条件和后天的不足,都给这一代学人的进步和成长带来了更多更多的磨难和障碍.想想80年代初期的时候,每一次会议都是有两三百人,那是很辉煌的,很壮观的,不像现在开一次会,能够召集四五十人已经很不容易了,还得给个红包才会来,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那么多人在文学的道路上拥挤,但只有极少数人在文学批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愿意苦苦地坚守,思和先生是在这些极少数人中的一个,而走到今天.思和先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他是从研究他的那些对象,慢慢地接近他们,最后与他们为伍,最后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个.
陈剑晖(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我们初心不改,还是走在学术的路上.
感慨嘛,应该是差不多将近囚十年了,跟思和、小东他们一起走过来,觉得有很多点点滴滴值得记忆,我记得我们1984年在厦门开“方法论”的会议,海滩上照相的时候,我跟思和单独有一张合影,跟小东、思和三个人也有一张合影,那时候还是翩翩少年啊,现在一下子六十多岁了,变成老一辈了.幸运的是我们仍然在坚守,用思和兄的话说嘞,我们还是有一种“岗位意识”,我们还是有一种学术的信仰和学术的执着.在今天这个会上,我记起一些往事,我记得1982年的时候,在海南岛开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第二届年会,那时候,哇,浩浩荡荡,就像小东说的,几百人,那时候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大腕们都健在,像王瑶、李何林,唐搜,孙席珍,钱谷融那时还是中年人啊,还有山西的一个副省长,研究赵树理的,叫作王中青,那时候都来了.那时候我跟思和还是小伙子嘛. 《文学评论》编辑部王信,一下飞机就请我们喝茶,当然这个喝的是海南的芦子山茶,大概一斤也就五六块钱吧.那个时候,才1981年,我有幸跟思和在《文学评论》上同期发文章,他与李辉写巴金,我是写秦牧的艺术风格,我用了一个笔名叫戈凡,因为那时候很崇拜李希凡,所以用那个“凡”字,然后觉得还是要点锐利,所以叫戈,戈凡.王信先生就请我们喝茶.把我们鼓励一番,那时候我们大概也就是还没三十岁吧.然后思和兄回去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我们当时海南的《海南日报》,叫作《海南人》,就是回忆当年啊,从苏东坡讲到新一代的学人也开始成长起来,思和就讲到了我,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地方,说我们是同姓,都姓陈;同年,我们都是1954年出生的;同乡,我们都是番禺的;我们都是搞文学批评;还在同一期刊物上发表文章,他这个文章我现在还一直保留着.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我到上海开会,思和就请我吃饭,吃完饭到虹桥机场,思和兄就送我,我们在路边打的,没带伞,刚好就下了毛毛细雨,车很难等,我们在路边等了十几分钟,我看到雨花都飘到思和的头上来了,我那时候真想给他抹一抹啊(笑),感到非常温馨,真的.当然我们也谈到了当年的一些往事,我们回忆起来有很多的过去的往事,比如说我们1986年的时候,在海南举办一次全国青年批评家会议,我刚敢于吃饭的时候还跟思和在数,上海来的哪一些、北京来的哪一些、福建来的哪一些,大概我们从事当代批评比较知名的半壁江山吧,那次会议都来了.我就记得车过芦子山的时候,当时孔捷生,我们广东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在这个地方下乡的,他提议说: “当过知青的请举手!”我们那个大巴车我记得那时候“唰”一下子,那个车上有五十个人,至少三十个人都举手了,我觉得这些细节都非常好.我们现在不是说要“重写文学史”吗,思和你原来就提过的“重写文学史”,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提“第二次重写文学史”,就是要把握好这些细节,通过这些细节的呈现,来展示我们新的文学史的具体性和丰富性,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所以我就很感慨嘛.参加这个会我很感慨,当初还是少年,现在我们都六十多岁了,变成老年人了,但是我们初心不改啊,还是走在学术的路上.
宋剑华(暨南大学文学院):我倒觉得“复旦学派”是比较客观的一个存在.
我和陈思和老师是在1986年,还是1987年见的面,虽然认识比较晚,但是我谈几个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当然是祝贺《陈思和文集》的出版,这是一个大事.因为对于每一个学者来讲,很难有这么一个机会.这意味着对自己学术研究的一个肯定性的结论.那么我想谈的更多的是,陈老师学术研究的贡献已经在这七大卷里面,不仅七大卷,因为我看到好多东西没收进来.我知道,因为我最近在读,华文文学研究的我也在看,写王德威先生的文章我也在看,都没收进来.但是就七大本来看,沉甸甸的,已经把他自己的地位奠定了.我想说几个感受啊.第一个感受,当年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80年代初,那时候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木是复旦,我估计陈老师也有这种感觉,影响最大的是北大.北大的老先生特别多,王瑶啊,那时候对我们影响特别大.但是到了1985年、1986年以后,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现在包括我自己,还有我的学生,他们现在更倾向于复旦.所以我后来发现了一个概念,叫“复旦学派”.我在教学第一线上,我最近十年一直在关注,陈平原好,李杨也很好.但我发现,北大的特点就是,它把当代归当代,现代归现代,分得极开,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分得太开了,不能玩儿,是吧? (笑声)但是,这十多年来,思和兄的文章我都在看,还有郜元宝兄、新颖兄,还有王光东他们.我为什么说我忽然发现“复旦学派”是普遍存在的?它不是哪一个人,这个恐怕还不是“海派”的关系.这个“复旦学派”,它第一个就是把现代和当代打通了.因为我一直在教学第一线上,我要强调这一点,如果是谁搞当代文学搞下去了,你就不要搞,因为你找不到根啊.你看郜元宝,最近在写李劫人的时候,我在读他研究《死水微澜》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比较阅读的论文,我也在关注.那天我在做沈从文的时候,我也看了张新颖的文章,我都在关注.他们都在踏踏实实往下走,很自然地形成了“我有一个根,然后往上生长”的观忿,就把现代和当代自然打通.这是我认识到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说这个“复旦学派”存在,第一它不是中规中矩的,绝不中规中矩,但是第二,它绝不犯规,这是我觉得非常奇怪的.比如说思和兄的文字里,他根本不对体制发出疑问,郜元宝也是这样,我发现你们只关心文学.你们看起来好像很自由、很松散,但是又非常严谨,我说你们的语言是诗性的,但是逻辑又非常清晰,这是我觉得很怪的地方.然后再看你们的第三个特点.比如说: “我们很重视史料,资料性很强.”但我发现,好像“复旦学派”也挺重视史料的,只不过对史料的应用方式不同.只不过把史料用得比较活,隐藏在作品中,读起来很轻松,不是那种很死板、很呆板的东西.新颖做沈从文研究的时候,也用得很活.我觉得这是第三个特点.还有第四个特点,团队意识极强.这个团队意识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我觉得其他有谁开会发言,比如刚敢于郭小东一发言就说,刚敢于某某怎么讲的,受教了.而你们好像没有这个习惯,但是你们客观地形成了一个呼应性的东西,思想观点,有关某个概念的建构或者理解.你们已经有了一个周边围起来形成一个合围性的东西,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东西,但是合起来又是一个整体.所以我在想,以后不要提”海派”, “海派”很复杂,讲不大清楚.我倒觉得“复旦学派”恐怕是比较客观的一个存在.当然我讲的“复旦学派”是仅指现当代文学领域,别的咱不懂.为什么要说它?因为有领军人物,你看第一代领军人物,思和先生就在那里,贾先生已经不在了,但现在新颖兄、元宝兄你们都在,你们会引导把这种东西发扬下去.昨天晚上,我还在读思和先生写的巴金传,其实他聪明在哪里呢?没有一个人写传是像他这么写的,只写一半.这是第一个,他觉得好玩.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细读了,它里面很多评价,其实在他自己心中,是对晚年巴金说的.他对《家》的评价,远不如《寒夜》.还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到那个《寒夜》无可挑剔,我非常赞同这句话.我昨天晚上还在思和的学生面前说,我说只有这样的老师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确实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讲我非常感慨,陈思和先生出版这个文集,我们可以做对他个人的评价,但是我觉得坐在这里的一大批人,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不是,是他的同事,但是形成了一个“复旦氛围”.所以我说,你们回去可以思考一下,可以自己总结什么是“复旦学派”.不光是陈思和先生一个人能代表复旦,郜元宝可以,张新颖也可以.所以,今天来,感受很多,也很深.
李振声(复旦大学中文系):你读他的写作,总是会有一种警醒.
从年龄上说,我和思和先生是同一个时代的,相差不了几岁,但事实上他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思和著述的学术批评始终维系在一个很高的精神高度上,你读他的文章,总是会有一种警醒.什么警醒呢?就是你不敢堕落,不敢放低自己的标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始终属于我的老师.套用一句俗气的话说,我是读着思和的著述慢慢变老的. (笑声)第二点,思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作为一个重镇性的存在,这是大家公认的.他在每一个重要的时段里面,都留下了地标性的印记.从最早的,巴金研究就不用说了,他最早打通了现代和当代的壁垒,提出新文学整体观,接下来和王晓明一起提倡“重写文学史”.那么到了1989年之后,一度很沉闷、压抑的时候,他也在积极地思索,那段时间大量地关注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他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说法,人文精神大讨论,然后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说法,庙堂意识、广场意识、岗位意识,一直到后面“潜在写作”的提出,到“共名” “无名”的提出,以及近期对新文学作品别出心裁的解释.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他的著述,不光是我们复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骄傲,也是中国現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幸事,即使放到世界相应的著述里面,也是可以排在前面的,这让我非常佩服.我个人从中获益很多,在座各位也从中获益,我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点著作,在出版方面也是得到了思和先生的帮助和关照.所以借这个机会,我要表达我的谢意.最后我想说,这样一个众人信赖的存在,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在他培养的一大批有才华的弟子中间,在著述的量和质上要超越他,我估计我是看不到的.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啊,一个成功的老师,思和先生当然是非常成功的老师,但我另外有个标准.这是我的一个荒谬的说法,我觉得一个成功的老师,他成功在什么地方呢?成功在他培养的弟子能超越自己.所以我在思和老师的身上是没有希望看到这一点的. (笑声)
张燕玲(《南方文坛》):犹如莲花未出水时,已是莲花.
陈思和四十年的文学研究与批评本身,就是中国当下文学最生动的注解.比如我们都知道他最早期的巴金研究,他就把巴金与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关系,做了非常精准、清晰的梳理;之后的重写文学史、民间立场、人文精神、潜在写作、出版策划……,90年代初的时候做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就在《南方文坛》一直做了系列的评论,后来又到了他去做《上海文学》主编的时候,我们俩经常通电话,然后有时还叫我帮组一些稿子,我特别为他骄傲,真是敬业得不行.我说你别求这么完美,从封面到栏目到内容,都那么操心,真的很让人感动. 《上海文学》推出了一大批边远地区的作家,一组一组地做,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去做,文学的版图了然于胸,非常令人尊敬,因为大家都在做杂志啊.其实啊,还有他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大家也都看到了, 《南方文坛》2017年第五期的浩浩荡荡的这么一组稿,尤其是陈老师对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的阐释,他那些令人振奋的,或者说是让人心起敬意的言论和论述,确确实实对当下是非常有指导、澄清作用的,比如他说,很多人还去纠缠“华语语系文学”这个概念好不好,他就说“有些人与其纠缠不清这个概念的复杂含义,还不如站在现实世界的立场上,去思考一下,如果这部《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重磅炸弹的形式,译成中文,在海峡两岸出版,人们看到的是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海外文学都自然而然地归属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之下,这比大陆内地学者写一百部文学史,还要有震撼力,有些人自煞可以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去挑剔这部文学史,但你总不能去挑剔一部整合了两岸统一的文学史”;又比如他提倡的精读经典, 《南方文坛》2016年的第二期,陈老师就有一篇长文,叫作《文本细读的几个前提》,那是“南方文坛”微信号里头点击量空前高的一篇,影响非常大,后来就很多人见到面都说: “陈老师这篇文章很好啊!”我跟很多年轻人说这篇文章你们可以收起来,当自己做学问,做到一定难度的时候,可以拿这篇文章来看一看,起码你的思路就会清晰许多.总之,陈思和老师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批评既高屋建瓴,更植根于中国的本土与现实社会,他的一篇篇文章大都高远而平实,通达而犀利,都是一篇篇用心之作,始终发出了自己独立且具思想穿透力的声音,具有丰富的启示和开拓意义,他的研究与思想代表着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时代高度.在2004年的时候我主编过一套“南方批评书系”,其中有一本就是陈老师的,叫《无名时代的文学批评》,当时我给这本书后面写的推荐语是这么说的, “一个勇敢无敌的群体,坚定而狂野地打捞‘无名’的名家,生动地发掘沉默的文学史.这本书,先锋意义和认识价值并存,学术理念和文献价值共生.”今天回头去看,我认为还是准确的.2013年我们有令栏目叫“现象解读”,做了“陈思和的意义”,刘志荣在这个专辑里写了一篇文章,整篇文章他谈到陈思和先生对他的影响,他的结语是这样说的: “诚实正直的思想和工作,必定会有反应和回响,犹如莲花未出水时,已是莲花.”我想,这既是志荣对陈老师的致敬,也是我们每个人对他的致敬,同时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声和自我期许.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陈老师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对文学那么热爱?
我看刚敢于,郭小东老师、陈剑晖老师、宋剑华老师三位粤籍的学者,哇,他们真的是广东人的风格.这也是有底蕴的,因为你们共同走来的历史.实际上我们会从陈老师身上接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年龄的差别决定了我们在精神上有的时候会有隔膜.而你们呢,虽然身处异地,但是在同一个年代进入历史,所以你们之间有息息相通的东西,而我们是不具备的.比如说,有一点,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我记得严锋也跟我讨论过,说陈老师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对于文学的爱,这个爱他不能理解,爱两天可以,爱三天可以, (笑声)他爱了四十年, (笑声)因为我们实际上在不同的时候对文学有很多感慨,对当代文学有更多的感慨.陈老师是这一代人中坚持下来的人,我想这个坚持有很多很多的意义,但是在文学本体论上的坚持,这一点,我不怎么能够理解.说老实话,放眼望去,这一代人中间,很多人在坚持,但是也有很多人改行了,失踪的也很多.所以我抛出这样一个“严锋之间”——陈老师的爱从何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可以生发很多,但是有一点呢,郭小东老师讲得很清楚,就是他一旦献身文坛了,他的意识很清楚,就是把两个“五四”合在一起,这是他非常自觉的.因为有这个自觉,所以我们复旦的,刚敢于剑华老师讲的, “复旦学派”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现当代文学史打通了.在复旦的现当代文学学科里面,如果你只搞现代文学,或者你只搞当代文学,也玩不起来,因为我们这个气氛是这样子的.陈老师的文集是他一生功业的一小部分.你如果对他稍微了解的话就了解,他更多的时间,是在他边角料的时间中奋笔疾书的,他大部分时间都被学生分割了,被他三任中文系系主任的职位分割了,被《上海文学》的编务分割了.尤其是他的学生,大家都知道,他带学生尽心尽力,他的学生是如此之多,每个人都分割他的一块时间,他就没有时间了.所以我说文集是他功业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中国的言说环境稍有不同的话,陈老师的文化形象,恐怕除了学者之外,会更加丰富.他是一个出版家,刚敢于振声老师讲,在座的好多人都在出版方面受惠于他;他是一个文学敦育家;现在又做图书馆的馆长,是图书馆专家.太多了,而且他还是一个不满足于专业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文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文学这个媒介,为整个中国文化说话,代表一代人.他要不可一世论文学,代表很多人去论文学.所以我说,如果中国的文化环境不是像目前这样的话,那么陈老师的整个文化形象会更加多样.实际上,他的文化形象还是多样的.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从专业的角度讲,在众多的文化形象中,他的文学史家的形象应该是最突出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他的一切的落脚、一切的发源,其实都是围绕两个“五四”展开的.还有剑华老师讲的他提出的概念,这些概念不是单纯的理论概念的发明.我记得当时上海、外地有好多专家问我,你们陈老师是本科毕业的啊?他没有读过硕士,也没有读博士,他也没有经过纯理论的训练,他怎么会对理论有这么高的兴趣?其实刚敢于我想补充一点,他不仅是少有的坚持下来做文学史研究的人,而且是近二十年来,甚至三十年来坚持不懈地探索文学史整体理论把握的人.文学史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有太多的文学史教材,但是像他这样的个人的表达,是少有的.这部文集我一看有七卷,可能起码有三卷还没出来,对世界华文文学,就可以出一卷.陈老师提出的达些概念,如果我们稍微想一想,其实很巧妙地用经纬两线,把中国从晚清到现在开放的当代的每一个阶段都涵盖了.比如说针对现在议论纷纷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海外汉学观点,他提出了先锋和常态的概念来对应.我们只要把他的理论和王德威先生的“被压抑的现代性”、跟范伯群先生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放在一起,那他的个性就非常突出.还有就是,在文学史划分上,他提出“以抗战划界”,之前他就有“战争文化心理”的研究,这一点又使得我们对于40年代以下到50年代之交的文学的交替关系弄得非常清楚.他抓住的是一点.接下来就是“民间”的理论,就是“潜在写作”和“民间隐形结构”,这个是针对50年代文学的,针对文学史上“十七年”和“”的.这也是我们文学界讨论最丰富的话题,但是没有人像他这样发声.那后来的“无名”啊、 “共名”啊……其实他横向的研究还有很多,像他讲整体观,讲中外关系影响,他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系列文章,把中国文学的世界定位讲得非常清楚.在这个基础上,他最后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这解决的不仅是我们现代文学领域本身的一个理论难题,也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一个问题,他一下子就有个人的创见.所以,我并不是想“严锋之间”在今天就能解答出来,但是顺着这个思路啊,好像能接近严锋的问题,他的问题是陈老师为什么这么爱文学.我么爱两年可以,爱三年可以.其实是我们的兴趣不同,而他爱到现在,所以是“咬定青山不放松”,文学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吸引他?我今天解答不了,我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大家一起解答.
严锋(复旦大学中文系):陈老师的眼光奇奇怪怪,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元宝刚敢于说的这个“严锋之间”,我真不记得我有问过这个问题. (笑声)但是我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就是我从来没有在陈老师面前表达过我对他的景仰和崇敬,但是我在同辈、在师兄弟之间一直是滔滔不绝的讲过类似的话,但不是说“陈老师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对文学那么热爱?”我觉得这个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我也想说一点,陈老师是我和元宝在大学的班主任,我想说的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的感觉,一个是“敬”,还有一个是“畏”,呃, “怕”,陈老师一直在生活上对我们非常关心,事业上非常提携,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一种知识上的对我们的“压迫感”.他在当我们辅导员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学术上还没有出名,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他就是一个在人格和知识上对我们构成巨大压力的人.所以我说的这个“怕”呢,是怕我们“露馅”,怕他说我们今天怎么又不读书了,为什么又不读经典.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感受到陈老师非常强大的气场.其实我们当年的感觉,经过这么多年,可以说是完全正碗的.我想这种“怕”,其实也是好的,就是说,它逼迫我们,我有的时候想偷懒,因为我也特别喜欢玩儿,偷偷培养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就是说,有陈老师在,我们总是能够回到文学的轨道.所以,这一点能呼应元宝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陈老师的存在,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精神上的指引.看到陈老师的文集出版,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历程,也是我们的一个路标,这里面也是映照着我们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陈老师的书和他的这个人、这个形象,包括对我们威压的形象,它形成一种“压迫”,压着我们和文学能够始终这么磕磕碰碰地走过来.那么我想说一点,也是回应元宝之前说的这个真隋,其他我不说了,我说我感受最深的,因为今天科幻小说热起来了,我也是对这个做过一些研究.但是陈老师在90年代就研究科幻,他有一篇叫《创意与可读陛》的文章,研究台湾的科幻文学,是1992年写的,还有一篇叫《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文章,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后来为什么偏爱科幻.陈老师当然是现当代文学的重镇,用古代文人的话来讲,他是“正”啊,堂堂正正,就像武侠小说中的萧峰.但是他这条大河不弃细流,他其实也非常关注那些边缘的、被压迫的、潜在的、支流的东西,仁帕口说科幻小说、通俗个说.这不光是对一个文类的关注,而且是对时间、不同的国别和地域的关注.而且,我昨天在学校里的报告,可惜陈老师不在,其实我很希望陈老师听到的,我用的是陈老师几十年前的框架,就是把刘慈欣放在“五四”文学以来的线索当中,其实这是陈老师在90年代初就提出来的,它就是台湾的通俗文学、科幻文学、玄怪文学,它也是对“五四”文学的回应,包括科幻小说的超越性、精神陛又是跟80年代的实验小说本身有一种相通,他把时间、空间和文类的呼应联系起来,而且这篇文章是在90年的.那个时候大家的眼光还是非常正统的.所以在陈老师的引导、示范和启发下,我觉得大家做的东西都很不一样,他并不会要求你做巴金研究啊,或者你做谁的研究啊.陈老师的眼光奇奇怪怪,这是我特别喜欢的.我也是趁这个机会对陈老师的先导、先驱,甚至有种寓言的色彩,但是又是精神的向导表达我的一个感谢.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 “五四”的精神传统通过活着的人,传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再传下去.
我想讲两点啊,一点就是,陈思和老师的现代文学研究的起点是跟一些现代文学人物相关的.他从贾植芳先生、巴金先生,主要是这两个,还有其他的,从同他们的接触开始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个起点不仅仅是起点,我们后来会观察到,陈思和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里面,如果和其他学者做一个区别的话,在这个里面一直有从巴金、贾植芳先生身上传续下来的精神传统.所以,陈思和老师的文学史研究也好,还有其他的研究也好,他不是一个人面对一个客观的对象,来做拉开距离的研究.它是一个精神活动,而这个精神活动是有承传意识的.我说的更明确一点,其实是“五四”的精神传统通过活着的人,传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再传下去.我觉得这一点,你如果要把它夸大一下的话,也是可以的.你接触到那个活着的“五四”的人,和没有接触到活着的“五四”的人,这个形成的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我想,是陈思和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特别的、具体的特征.第二点,作为一个学者来说,我想说最重要的,像元宝说的,陈思和老师是一个文学史家,还有我觉得另外一点,绝非不重要,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学批评的实践.你当然可以说,他四十年的文学批评的实践见证了中国文学这些年发展的历程,我觉得“见证”这个词不太够,因为当我们说到文学发展的历程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人是把眼光偏重到创作上去的.其实文学批评在这里面不仅仅是见证的作用,不仅仅是解释、阐释的作用,它共同参与了文学发展的变化.而这个共同的参与和创造体现左陈思和老师身上,比一般的当代文学批评家更加突出.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他确实是一个理想学者的典范
陈思和老师刚敢于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作为一个个体,过分孤立之后,未必能做成什么事情,尤其你要想改变环境什么的,是很难的.但我在想,如果有更多的人,比如说同人,或者说同好,那些有相同想法和志向的人,能够团结在一起,彼此援助,就能够一点一点地改变现状.就以复旦大学为例,以我一个外人的观感,经过思和老师带着他的学生多年的努力,还是改变了很多我们对中文学科的固有印象.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当代文学学科在复旦很强,这个“强”就是有几个老师立在那,能够让别人意识到,这个学科很重要、不容忽视.确立这个意识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我和我的中大同事(今天也有好几位在这里),想要改变大环境,在中大中文系确立这个意识和观念,可能陛就很小.中大的传统一直是重古典,当代文学研究在一些人眼中,根本不足一提;一些人从未意识到,他们研究的所谓古典文学在它那个时代,也是当代文学.而复旦中文系能够有所改变,是跟思和老师多年有意识的努力有很大关系.就我个人而言,能进入到思和老师这种精神场域里面,并接受这种场域对我的滋养,是很垂要的.我想起尼采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说,我的写作包含了我的精神,也包含了我的朋友们的精神.思和老师的写作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他把很多人团结在一起,是有更大的一个想法在里面.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看到《陈思和文集》出版,就可知他作为一个学者的体量和重量. “文集”这两个字,在我们心目中是很庄重的.至少代表着某一种分量、体量.这个文集我还没来得及全部详读,但我能感觉到,这个文集所建构起来的学者形象,显然是一个体量比较大的学者.说实话,有才华、有思想的学者很多,各种人的风格也不同,有一些人比较尖锐、深刻,有一些人比较宽广、厚重.思和老师是一个体量比较大的学者,这种体量,表明思和老师有一种宽度和厚度.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多年前,我陪一个著名作家到西安参观贾平凹文学艺术馆,这个文学艺术馆有两千多平方米,两层楼.参观完之后,那个作家跟我说,这么大一个馆,如果是我的,我装什么东西进去?我就那么几本书,就那么几个版本,给我这么大的空间,我是没办法把它填满的.但贾平凹可以填得满,他的书有那么多的版本,他还有字,还有画,还有收藏的文物,还有那么多的获奖证书,只有他这个体量,才能填满两千多平方米的一个文学艺术馆.别的一些作家,哪旧影响也很大的作家,都未必有这个体量.从这个角度上讲,思和老师借着文集的出版,向我们证明了,他是比多数学者的体量都要大很多的.有些人出文集是勉强的,但“文集”二字放“陈思和”名字后面,就挺合适.
第三点,从思和老师的文与人看,他确实是一个理想学者的典范.要达到他这种理想学者的高度,极不容易.比如,他对他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及文学教育有很深沉的爱.他对文学的爱,对学生的爱,是很多人没有的.有些人对他所从事的事业,视之为一种工作,未必投入这么多的感情.带学生,我们大家也带,但也未必有他这么一种发自内心地对学生的关心、爱护.这些,都是一个人的精神底色.又比如说,他有好几套笔墨,也不一定我们每个学生都有的.我们有些人除了写论文,别的什么都不会写,可思和老师不单是论文,旧体诗、散文都写得好,他有好几套笔墨,这就是所谓的“兼有别趣”.其实有没有别趣,有没有几套笔墨,往往决定一个学者、作家到底能飞多高,走多远.又比如说,思和老师学术深厚,格局很大,可同时他又能做很多琐事.写作之外,他做系主任,做图书馆馆长,做主编,编杂志,编书,等等.做很多具体的事情.我说这个话的时候,突然在想,可能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埋解思和老师.思和老师可能意识到,在中国能写文章的人很多,有思想的人也很多,但能把思想转化成实践、有效地转化成实践的人,并不多.中国非常缺这种愿意把思想变成有效实践的人——变成出版行动,变成文学教育,变成杂志平台,变成年轻人的机会,等等.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种意识的.你说他是服务意识也好,他是为他人作嫁衣也好,骨子里他确实得了五四那一代学者、作家的精神真传.五四那代学者、作家中,没有几个人是固守书斋里写作、教学的,他们都做很多事情,而且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没有白做,这些事情到现在都还有很多回响,这个回响的意义有一些甚至超越了他们的写作.关于研究之外的事情,我们有些人也在做,但少有人像思和老师做这么多,做得这么持续、有效.这是一种能力,非常强大的能力,由此也可见出思和老师有很强的使命感.这些综合的才赋与品质,共同建立起了一个标高,并展示出了一个理想学者的典范.我个人从他的点点滴滴中受益良多.
刘俊(南京大学中文系):整体观就是从经纬两方面——把近代,现代,当代打通;把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文学的部分也容纳进来的——真正的整体文学史观.
陈老师的研究领域比较宽广,我们现在都说,他是一个文学史家,现当代支学研究的专家,当代文学批评家等等,不过我对陈思和老师学术成就的最大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是世界性的学术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有西方的汉学家,包括华裔汉学家,我们自己也有庞大的研究队伍,可是我们向世界学术界提供了什么?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概念、理论和话语.我在上课的时候,经常公开地说,中国现当代研究的专家很多,我们这些研究专家真正向世界学术领域贡献出我们自己的概念的,贡献出我们自己话语的学者,我觉得就是陈老师.他提出了“无名” “共名”、岗位、广场、潜在写作等等.这些概念,这些话语,这些理论,可能有些同行专家不以为然或者不完全赞同,可是没有关系,因为任何一个概念任何一个话语和一个理论被提出来的时候,可能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可是他提出来了.我们经常会谈王德威,谈李欧梵,谈夏志清等等,这些海外的,华裔学者,他们提出的种种新的观点和新的概念,种种的理论,我们提供不了.我觉得陈老师他的最大贡献,就在这里.就是在向世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提供了我们自己的概念、话语和理论.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也是他最大的一个贡献.
第二,我们刚敢于讲陈老师有一个整体观.整体观就是从经纬两方面把近代、现代、当代打通这样的一个整体观.但是我觉得陈老师的整体观其实不限于此.因为上世纪50年始,现代文学就成为一个建制性的学科,基本上就局限在中国大陆文学的范围.到了1985年,北大的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也只是在大陆的文学范围内,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20连成一个整体,可是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仍然没有把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写作的包容进来.我个人读了博士以后,就主要去研究台湾香港和海外文学.我从这个角度,发现陈老师是一个除了在时间的纵向维度上有整体观的学者,他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也是一个有着整体观的学者.这样的纵横两个坐标的整体观,我觉得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观.这对我个人影响非常大.1988年我读博士就开始研究世界华文文学,到今天也快三十年了,陈老师的一本《行思集》,这次没有收到文集里去,我想以后再出全集的时候这一部分一定要收进去.我作为一个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者,我看陈老师的这些研究台港、海外文学的论文,谈了很多台港、海外华文作家,甚至我都没有像陈老师读得那么全面.他谈到的很多名字,还是相当陌生,也就是说陈老师他的阅读覆盖面是非常广的.比如说吉铮这个作家,我就根本没听说过,还有林耀德、黄凡、叶言都等等.这样一种大面积覆盖的研究视野,这种整体观,我觉得在大陆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里边,我目前看到的,除了陈老师,我还没有发现还有其他人.
第三,陈老师他对文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文献资料.陈老师他非常注重第一手资料.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编了《史料与阐释》这个刊物.那么台港海外文学也更是如此,多少年的两岸隔绝,使得我们这个领域其实有很多基本材料都没有掌握.当然有些大陆学者比较大胆,他们也经过学术模式化的训练,很容易就写出文学史出来.而陈老师非常谨慎,他觉得要了解一个我们过去并不熟悉的领域,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首先要从基本的史料收集做起.从基本作品的解读,陈老师现当代文学研究是如此,在台港海外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刚敢于我讲的这样一些概念也好,话语也好,理论也好,陈老师都是从大量的、丰富的文本分析中提升出来的.我想这样的理论,这样的话语,这样的概念是有生命的.刚敢于严锋提到陈老师研究科幻,其实陈老师也研究海洋文学,台湾文学中的海洋文学,还研究台湾文学中的新生代文学.他也研究台湾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同性恋书写等等,这些前沿的,—般入不太关注的,但可能对文学界来说非常重要的领域,其中也包括科幻.所以我想陈老师,他对我的意义,一方面他在学术上以他的成果引领着我,另一方面,陈老师的为人,对我个人的这样一种关怀,也是让我非常感动.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笔走龙蛇四十年
平时都是我在论说人家,今天是大家论说我.我坐在那儿听大家说,一直都在怀疑这是在说我吗? (笑)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因为我不大习惯接受这种——特别是大家都那么熟悉的——夸奖,我已经过了需要鼓励的年龄了.但我还是想表示感谢,尤其是广东人民出版社肖社长,向主编,还有这个团队,为我的《文集》出版费心费力的年轻的团队,我衷心的表示我的感谢.肖社长第一次与我在眉山见面,就谈起出《文集》的计划.因为前面有个因缘,复旦大学图书馆前馆长是葛剑雄馆长,葛馆长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了一套文集,也是七卷.肖社长跟我提出了这个计划,我当时不知怎么回答他,我犹犹豫豫,说真心话,我也是充满了犹疑,不忍心让出版社来承担经济上的压力.后来陈国和跟我多次说,肖社长是真心实意的,不计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答应了.文集出版的整个过程中也是给出版社添了很多麻烦,我自己不停的校订和修改,几乎每一卷都重复了三四遍.也不是改错,我只是希望做得更加完美.我知道我为出版社添了很多麻烦.
也感谢今天到场的朋友,我真没想过今天会是这么大的一个规模,没想到这么多的朋友来了.首先是志荣做了大量的工作,都是他在邀请,在张罗,我也感谢郭小东兄、陈剑晖兄、宋剑华兄,都是四十年的朋友,四十年好像说起来很轻松,其实不是这样的,四十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从一个年轻小伙子变成一个老人,而且人生大概没有第二个四十年了.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大家能够一直相濡以沫、互相支持.虽然我在上海生活,但是广东对我来说是一个精神依恋的地方,我说是“故乡”有点过分,因为我生在上海,我的父亲是番禺人,但是我现在怀疑,我父亲可能也是生在上海的,很可能我的祖父在广东生活.但是我老愿意说我是广东人,说我是番禺人,我每次来广东,像精神上的依恋,我喜欢广东,而且我和广东的缘分也很多,喜欢广东人比较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啊、饮早茶啊、煲汤啊,广东的文化啊,我都喜欢,这是个缘分.这书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很高兴.
第二层意思是我有点感慨.我们这一代人,与现在的博士生、博士后相比,他们有那么漫长的的学习时间,而我们那时在中学里就没有学习的机会,中学毕业后都是在生活实践中学习.刚敢于大家都在说我的经历,有一点役有说到,我比较有条件的,就是我当时是在一个区图书馆工作,所以我有条件能够比较早的接触到很多文化知识,这是一个前提.其次,我属于幸运者,就是高考以后,我跟从了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贾植芳先生他本身就是一座学校,我在这个过程中——刚敢于郭小东兄说了一句话,我很有感触,我是在研究我的对象的过程中,完成学习的,我研究巴金就在学习巴金,我研究鲁迅就在学习鲁迅,我研究贾先生就是在学习贾先生.说到底我整个四十年的过程,到今天,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没有巴金先生、贾植芳先生,贾先生的背后还有胡风、鲁迅等精神传统,那我肯定就不是今天这样的人了.我也可以做人,也可以做文章,但是我就不是今天这样面貌的人.刚敢于大家都提到我主编的“火凤凰”系列丛书,当时的情况就是学术著作出版很困难,对于那些年轻的研究生、青年教师来说,他们的学术自信是需要有一个好的环境来鼓励的.后来我就策划了这几套“火凤凰”系列,来推动学术著作出版.这个动力就是来自巴金、吴朗西等先生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很支持我的计划,他还给“火凤凰”题了字.我就是在学他,学巴金、鲁迅,学他们在实践中追求理想.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千疮百孔,光消极抱怨也是没右意义的,去狂热抗争也是没有用,唯一有用的,就是去看看这中间还有没有空间,让我们去努力工作,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看看我们可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一直强调,行动比写作更重要,实践比理论更重要,这是我很实在的想法.其实,我有大量的时间都不是放在写作上的,我过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人活到六十多岁,总有一个活法,这些文字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些记录,记录下来也蛮好的.我觉得今天大家聚在一起,好朋友聚在一起聊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还要讲讲一些内心的想法.我不是一个很乐观人,但是一个生命意识很强烈的人.可能大家在我的文字里看到的我,似乎很坚定很乐观,其实我内心深处是悲观的,不仅悲观,有时候也是灰暗绝望的.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有时候会一个人独坐书斋,独坐在书桌边,我的环境很舒服,但是我心里很深的地方,总是很迷茫,有点绝望.有很多委屈、很多压力都是沉在我心里的.我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化解各种矛盾的人.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化解自己内心的郁结,有很多时候,我只能把自己做大,因为做大以后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如果把自己弄得很逼仄,那所有的问题都是大问题.我也感到压力,也有很多困惑,有时候也觉得走投无路,但是我总会把自己的心胸更加放开些.做大以后再想想,什么问题就过去了.习惯之后,我也会用这种方法去劝解别的人.我在文字上有时候好像满不在乎,好像都是自己给自己安慰,但这确实是一种抗压的方式.所以说,我为什么会写那么多东西,如果一个内心不苦闷的人才不会这么写了,他有很多方式去排遣自己.正是因为我内心很多东西没有得到排解,我才把它写到文字上去.虽然我不是那种喜欢倾诉自己内心的人,但我还是确确实实会把该倾吐的东西倾吐出来.我不是被大家看得那么光鲜靓丽的人,我是一直是在各种压力中走过来的,只剩我自己能够把它们化解掉.
我给大家念一首刚刚写成的诗:是我前天在飞机上,从上海飞往珠海的飞机上,当时天已经暗了,看着太阳下山,渐渐变成一条红线,我突然就有一种感受,这种感受也是我今天到会的心情,一个老年人的感受,这首诗也是写给诸位青年才俊的:
《从上海到珠海参加文集发布会而感》:
银翼九重看晚霞,云催雾涌日西斜.觅中安在凌霄外?逝者如斯夜色佳.
老去无端忙俗务,病来乘兴吃闲瓜.追光四十桃林盛,唤作后生舞龙蛇.
最后一联是我对所有学生的期望.今天参会来的,很多都是我的——应该说是好几代的学生,吴敏带来了她的研究生,刘志荣也带来了他的研究生,都已经是我的学生带出来的博士生了.我觉得在我所有的身份中,最令我快乐、有荣誉感的,就是当一个教师.作为一个教师,我最好的作品不是七卷本《文集》,而是我的一代代学生,学生的学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成长.我还是相信,他们应该是超过我的.我总有一天要留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通过我的学生来发展.这里我就想到一个意象,中国神话里的“夸父逐日”.在夸父逐日的故事里,最值得尊敬的是,夸父最后在渴死前,把手杖丢在一旁化成为桃林,桃林就结出了果实,鼓励后人不断去追求光明.所以我就选了这样的一个典故.谢谢大家!
研讨会论文参考资料:
该文总结,这篇文章为一篇关于《陈思和文集》和笔走龙蛇和从何来方面的研讨会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研讨会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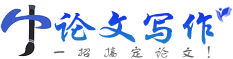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