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电影中的空间呈现和边缘叙事》
该文是有关空间在职开题报告范文跟许鞍华和边缘和许鞍华电影相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许鞍华电影中的空间呈现是其影片中边缘叙事的一部分.其影片中的空间首先在形态上表征着边缘人群的处境.局限性空间与边缘人群的受困,开阔性空间与边缘人群的自由,边缘空间与边缘人群的反抗这3组对应关系反映着空间与权力的缠绕.更进一步来说,作为一种连接室内与室外、地上与地下、水域与陆地等不同空间领域的“缝合”空间,边缘空间在其深层内涵上还勾连着导演本人在边缘叙事中的价值导向与美学诉求.正是这种爱德华·索亚式的“第三空间”思维决定着许鞍华影片的独特风格,而在更大的层面上,这一发现也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城市空间的另一种视角.
关键词:许鞍华;空间呈现;边缘叙事;第三空间
中图分类号:I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4-0107-06
空间呈现是许鞍华电影研究的一个焦点.以往的研究关注了许鞍华影片中的空间呈现与文化身份认同、日常生活空间的文化内涵、城市空间与现代性等诸多领域,但这些论述都有略显松散和同质化的倾向.举例来说,在论述其电影中空间的文化表征时,作者常以具体的影片为框架逐个解读不同作品中空间的文化内涵,这样的论述在细致之余却也丧失了系统化的可能.同时,大量文章都聚焦于某几个特定的思考范围,导致一些重复性、单一化的论述反复出现.这一现象背后的首要原因便是许鞍华电影本身的多样性.相比于一些典型的“作者电影”,许鞍华的影片似乎没有非常鲜明的个人印记,其影片的主题、拍摄手法和美学风格都在不停更换.许鞍华本人也曾多次强调自己不是“作者导演”,其影片诞生于众人的商讨合作而非导演个人的自我创作.正因如此,研究者难以在其影片中找到一个贯穿始终的标签式切入点,具体到空间研究中就催生了上文提到的一些缺失.针对这种状况,本文认为许鞍华影片中万变不离其宗的支撑点是其展现边缘人群境遇的边缘叙事,其所有讲述女性、漂泊者、底层人群、政治难民等等人群的故事都聚焦于这些主人公在社会和自我认同等领域中的边缘境遇.而这种边缘叙事中的空间呈现恰恰集合了其影片中与边缘人群相关的复杂权力表征,不同于以往研究中的表征关系所表现出的同质化倾向,这种权力表征关系因其复杂性而具有了爱德华·索亚定义的“第三空间”特征.具体而言,一方面,许鞍华电影中狭窄、阴暗的局限性空间表征着边缘人群被限制、被压抑的生存现状,而边缘人群对自身状态改变的期望也常表现于他们对开阔空间的渴望之中.这种局限与受困、开阔与自由之间的对应关系反映着电影中空间的权力内涵.另一方面,其电影在刻画边缘人物的处境时又多次利用了一些有着连接作用的边缘空间,如连接内外的窗户、阳台等,这些在其边缘叙事中近乎符号化的边缘空间提供并象征着边缘群体对自身处境的反抗与改变之可能.事实上,这种集压迫与反抗于一体的可能性正是爱德华·索亚所言的“第三空间”在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张力所在.而在思维方式上,这种思维方法又跳脱了由简单二元对立所带来的单纯受害者立场.正是在这种将他者“第三化”的“三元辩证法”思维之下,许鞍华电影的边缘叙事才得以呈现出其独特的情感基调与美学风格.而在更宏大的层面上,正如吴晓东教授在其文章中认为张爱玲小说中的“阳台”“在‘漫游’概念之外,提供着观照上海空间的另一种形式”①一样,本文将试图论证许鞍华电影中的空间呈现与边缘叙事间的复杂关联为我们提供了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等二元论冲突之外观照香港城市空间的另一种形式.
一、三组对应:空间的权力表征
人文地理学认为,“空间反映和建构各种社会类别,比如性别、种族和阶级等.”②具体到许鞍华的作品中,我们将空间对这种社会权力的表征总结为3组关系:局限性空间与边缘人群的受困、开阔性空间与边缘人群的自由、边缘空间与边缘人群的反抗.
局限性空间即形态上狭隘、局促的空间.在许鞍华的多部作品中,其故事的主人公都是被困于某个局限空间内的弱势群体,这种在空间上的受困直接印证了空间的划分对权力关系的建构.许鞍华在其早期表现社会运动的作品《千言万语》中塑造了一批香港社会中非法移民的形象.影片中这些被称为“无证妈妈”的“水上新娘”们由于没有合法身份而只能被困于狭小的渔船之上,无法踏出渔船的她们在空间上的被困也表征着其在社会身份上的失落.取材于天水围真实案件的影片《天水围的夜与雾》中的女主角王晓玲是一位从四川家乡远嫁香港却从未去过维多利亚港,只能在家和救助中心之间辗转的年轻母亲.想要自食其力的她在餐厅找到工作,而她的丈夫却坚持将其禁锢在狭小的家庭空间之中.当家暴升级,不堪忍受的女主角只得逃离家庭,却又受困于救助中心转而又进入了另一个局限的空间.在这部影片中,王晓玲的困境就直观地呈现为其空间处境上的被困.而同样关注天水围的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中独居老人的边缘处境则是通过一组表现其在狭小房间内独坐的镜头来呈现的.在这组镜头中,婆婆一人在促狭的房间里做饭、吃饭、发呆,阴暗狭窄的房间强化着婆婆的孤独感.2012年由吴镇宇出演的短片《我的路》也是利用空间表现主人公边缘处境的案例.片中一心想要变性的男主人公独自一人生活在光线幽暗的小房间内,影片在表现其独居生活时刻意利用光线和构图强化了其空间的狭小局促,这种空间上的局限恰恰表征着想要变性的他在身份认同、社会地位、家庭关系等领域中的边缘困境.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被困于局限性空间的处境,这些边缘群体们对自身境遇之改变的诉求也蕴含在他们对自身所处空间之改变的诉求当中,这就构成了空间与边缘人群处境表征之间的第二组关系:开阔性空间与边缘人群的自由.在《千言万语》这部基调沉重的影片中,一个难得的温馨场景便是“无证妈妈”在李丽珍饰演的义工的帮助下上岸,长久被困于狭小船上的她终于在开阔空间里享受到了自由的快乐.当久未踏上陆地的“无证妈妈”又喜又惊地行走于香港街头时,观众们也直观地感受到了边缘人群处境的复杂与无奈.《天水围的夜与雾》在表现王晓玲仅有的几次自由时也利用了开阔性空间对这种处境的表征.在某天夜里,王晓玲被丈夫之后走进楼下小区的休息区时偶遇一位同样从大陆来的女子.路人关切地说起在这里可以闻到从深圳吹来的泥土味道,王晓玲便闭起眼睛仔细闻着.这个镜头中身处开阔空间的王晓玲感受到了短暂的自由,这与其后来在救助中心的庭院里张开双臂迎接雨水的镜头一样,都是借助开阔空间表现其走出困境的自由.而《我的路》中的男主角最享受的时刻是身着女装走在大街上,走出狭窄阴暗小屋、走入宽阔明亮的街道上的男主角在经历着空间变换的同时也迎来了身份的改变.影片结尾处变性成功的她行走于街道上的镜头也象征着新生命的开始.更为典型的是《黄金时代》的结尾处理,萧红在香港医院内去世,其后镜头转到了她儿时在自家后花园中嬉戏的场景.随着演员念出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回忆童年往事的语句,镜头之下的小萧红在宽阔的花园里自在奔走,“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③这样的自由寄托在那个宽阔的园子里,这种自由正是在不断出走和被困之中的萧红一生的渴望,此刻在电影的结尾呈现,也体现了这部影片对萧红的贴切理解和对其悲剧的唏嘘.除了以上几部影片之外,这样的对于空间与人物边缘处境之间关系的展现与暗示在许鞍华的电影中数量颇丰,在此不再一一分析.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认为,“性别特权通过维持空间距离来保持自身”④.事实上,除了性别之外,这种权力与空间的依附关系在别的领域依旧适用,许鞍华电影中的边缘群体之处境便体现了这种无所不在的局限与被困、开阔与自由的表征关系.
在以上两种对应之间的是边缘空间与边缘人群的反抗这一组表征关系.在城市规划视域中,边缘空间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广义上看,从城镇间的分隔带、建设单元之间的公共交错带,到联结城市中各功能单元的水系、街道、建筑檐廊……在地理区位上都属于边缘空间.”⑤按照这种定义,我们将许鞍华电影中多次出现的起着分隔、连接作用的空间称为边缘空间,这种空间分隔着局限性空间与开阔性空间,在结合具体电影作品后,我们将重点分析连接室内与室外的——阳台、窗户、天台这些边缘空间对边缘人群处境的表征.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姨妈和许知常同为这个城市里的边缘人物,他们的相遇相知是对两个失意者心灵上的抚慰.当两人在家中穿起戏服唱戏的时候,镜头随着他们的脚步移到了姨妈家的阳台,两位已近黄昏的“知音”在阳台上身段灵活地唱戏,相同的爱好激活了两人的生命力.在阳台唱戏这个仰拍镜头中,“梦想照进现实”的意味格外明晰.在这里,阳台是分隔又连接着室内与室外的边缘空间,两个被世界遗忘的人在阳台上宣誓着自己在这世界里的存在之美.同样在这部电影中,当姨妈心灰意冷地卧病在床时,阴暗狭小的房间忽然被窗外一轮巨大的明月照亮,同时,她一心想要逃离小城的女儿也在阳台上和外甥一起看见了这轮月亮.对年迈重病的姨妈来说,这轮明月是善意的安慰,而对年轻的女儿和宽宽来说,这月光是他们逃离小城奔向未来的希望之象征.这几乎有着神性关怀之意的月亮正是通过窗户与阳台这样连接内外的空间降临到角色们狭小的生活空间也即受困的生活境遇之中.窗户在这里构成了一种典型的边缘空间,通过窗户,令人压抑的现实找到了有着超现实意味的某种出路.许鞍华备受赞誉的早期作品《女人四十》中,女主角阿娥在婆婆去世之后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身心俱疲的她只能在房顶天台上失声痛哭.在这里,天台是分隔了房屋与天空的边缘空间,阿娥在天台上得以暂时脱离家庭的压力,积压已久的情绪在这个边缘空间里找到了出口.此外,《黄金时代》中多次出现了萧红坐在窗前沉思写作的镜头,在这个边缘空间里,窗户连接着狭小的房间与宽阔的外在,这正表征着这位身处困境的女性用笔逃离着生活的苦涩、创造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宽广天地.纵观全片,这种对窗户在困境与自由之间的连接作用的利用从对萧红儿时的叙述镜头起就已开始,幼小的萧红就常靠着窗户凝望外面的苍茫之境.家庭对她来说是牢笼,而窗户象征着通向自由的可能.再如,短片《我的路》开篇即是由吴镇宇扮演的男性全身女装地坐在窗前自顾自地说出一些优雅而富有女性魅力的台词,随着镜头推移我们看到他身处的房间之阴暗狭窄,然而在这局促的构图中,窗户显得格外明丽宽阔.在这个场景中,窗户既是隔离着主人公与外在世界的狭小房间的一部分,又是他通向外部寻求认可的希望之所在.在此,男主角对窗而望的自言自语中蕴含着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巨大张力.通过以上三组对应,我们看到了在许鞍华的电影中,空间在形态上对于边缘人群处境的表征.而除此之外,空间呈现还勾连着导演在处理边缘人物境遇时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诉求.
二、空间呈现与边缘立场:观照边缘的另一种方式
如何将边缘人群影像化是许鞍华乃至大部分香港电影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当前电影中的边缘叙事呈现出与文学中的底层叙事类似的情况.在所谓的“为老百姓写作”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划分中,许鞍华的影片显然属于后者,这种立场的选择也集中表现于其影片中的空间呈现.如上文所言,许鞍华在表现边缘人群处境时利用边缘空间为他们提供和表征着反抗的可能,正是这一对于反抗之可能的表现说明了导演在进行边缘叙事时选择的“边缘立场”.不像一些导演在进行边缘叙事时采用的将边缘群体完全他者化、让他们在被动的呈现中失声的做法,许鞍华在进行边缘叙事时没有这种精英式的观照态度,概括来说,她的态度类似于美国学者贝尔·胡克斯所言的“选择边缘”.
贝尔·胡克斯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描绘了黑人女性在“铁轨内外”的生活状态.她认为铁轨就是一个边缘空间,一方面,铁轨在种族、性别和阶级上都起到隔离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它又连接着内外,铁轨这边的黑人女性可以越过铁轨进入白人社会,因此这个空间又是复杂化的.概括来说,边缘空间不仅表征着困境,同时还表征着反抗之可能.这一空间说明了她“选择边缘”的立场,即“‘颠覆压迫者的中心地位,主张我们的主体性权利’”⑥,爱德华·索亚将这种态度总结为“边缘拒绝被摆布成‘他者’”⑦.具体到许鞍华作品中,这种反抗之可能就在于其对边缘空间的呈现.前文已经指出,许鞍华作品中的边缘群体总是面对着局限的空间,然而更近一步地分析,这些局限性空间当中又时常内涵着边缘空间.作为分隔功能与联结功能并存的边缘空间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一个能产生更多可能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爱德华·索亚笔下的“第三空间”.“第三空间”是一个地理学和哲学意义上的复合概念.一方面,作为地理学家的爱德华·索亚在其《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一书中详细说明了“第三空间”提供的文化地理学意义上以权力关系介入空间分析的操作方法,而另一方面,他又将这一概念抽象化为一种表征着一切超越于二元对立之外的思维方式.简言之,这是一种基于后现代主义背景的世界观,在这一观念之下,“他者”被“第三化”了,边缘不再祈求于现代主义启蒙式的解放,不再将自己放在受害者立场去追求与“主流”同等的位置,反而转向认同自己的“边缘”身份,在这个身份中寻求认同.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在“第三空间”中,“这个地带虽然充满危机和挑战,但是同时也充满着差异和矛盾……而这种差异、矛盾和含混不清构成的机遇在于,它使得颠覆和抵抗成为可能.”⑧回到许鞍华的电影中,这一立场便催生了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我的路》、《黄金时代》等影片中由边缘空间在具体和抽象的意义上为被困者提供的颠覆境遇的机遇.
事实上,许鞍华导演本人的处境也决定着她在选择边缘立场时近乎必然的态度.在香港成长,在英国受教育的她对自己和所有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认同有着十分自觉的思考,其作品中的“香港性”也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此外,许鞍华本人的原生家庭也影响了她对边缘立场的选择.许鞍华出生于一个跨国家庭,她的母亲是战时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母亲一生漂泊和寻根的心绪始终影响着许鞍华,这种对归宿的追寻和无果最终被集中反映在其作品《客途秋恨》中.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许鞍华的这种成长境遇很像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成长经历.出生于印度的霍米·巴巴是被排除在印度主流社会之外的少数族,而在英国求学的他却又是英国上层社会里的外来者.然而在他的论述中,正是他的这种始终“离家”的状态使得自己处在一种“文化之间”的处境,而这种处境为他提供了在思考后殖民问题时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先天条件,即“正是在‘居间’的现身之处——差异之域的交错与异位——民族性、社群利益或文化价值的主体间性和集体经验才得以被协商”⑨.在许鞍华身上,这就体现为其在边缘叙事中的边缘立场.与霍米·巴巴一样,许鞍华似乎天生就属于边缘中的一员,而这就催生了她在表现边缘人群时选择的近乎天然的复杂化边缘立场.她曾在采访中说,“我自己和家人都是边缘群体,社会的大多数人也都是这个群体的.关注边缘和弱势群体,是我的兴趣,也是天性.”⑩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切身而自然的对边缘的关注,许鞍华对于边缘群体的态度从来不是先入为主地简单同情,而是对之投以更为复杂的人文关照.以其作品中的女性题材为例,许鞍华是一位拍过多部女性题材作品的导演,但同时她又在多个场合声明过自己的非性别化立场,“有时候,我拍一个不幸的女人,或许她的人生是失败的,但决然把失败归给社会或男性,这在我看来也是不全面的……对我而言,女性身份不是什么主义,也许就是一种情怀,一种看待世界的角度,无法回避,但也如此而已.”{11}不同于一些有着鲜明女性主义色彩的女性导演,许鞍华的性别化视角没有那么锋芒毕露,在她的第三空间式思维方式中,一切人都是一样的需要面对命运、需要在社会中寻找安身之所的存在,这种思维方式决定着其影片对女性群体的复杂化表现.因此,不同于有的学者所认定的,对许鞍华在一些影片中表现出来的所谓“父权制视角”的诟病,本文认为恰是这种对性别视角的淡化才使她的作品有独特的动人之处.在这种情况下,许鞍华的电影得以跳脱精英式边缘叙事的悖论,而其作品中的空间也达到了某些研究者所言的底层叙事之空间应该“呈现出某种差异性、否定性、反抗性,不管以激进的方式还是以诗意的方式,提示我们封闭中有希望,含混中有反抗,碎片中有真实”{12}的期望.同时,在效果上,她这种自称“不会把是非黑白分得很清楚”{13}的“第三空间”式态度也造就了她多次提到的对冲淡平实的美学风格的偏爱.
三、空间呈现与美学风格:观照城市的另一种方式
展现底层境遇的电影有很大一部分都侧重利用光线和空间营造混乱、肮脏、促狭的视觉效果,在这部分影片中,边缘人群的境遇被表现为一潭绝望的死水,而其影片的美学风格也呈现出自成一派的阴郁感.然而同样专注于表现边缘人群境遇的许鞍华却追求在影片中营造出平实、冲淡的美学风格,让人们体察到边缘生活里简单朴素的温馨之美.本文认为,这些美学风格的生产与上文所言的“边缘立场”、“第三空间”式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从宏观上来说,这些效果也在为观众提供着观照城市空间的另一种方式.
具体而言,本文认为许鞍华电影中的空间呈现通过3种方式营造了许鞍华式的电影美学风格.首先是利用边缘空间的分隔效果展现温馨的日常生活之诗意.在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中,贵姐与儿子和邻居老人可以说都是社会的边缘者,但整部电影并不着力于强调他们的弱势处境,相反,这部电影的亮点就是由他们3人之间的脉脉温情带动的人文情怀.在影片结尾处,3人一起过中秋节,随着镜头的移动,透过窗户我们看到了天水围的万家灯火.冰冷大厦里的小小窗口闪烁着明的温馨色彩,这种处理方式使得整个故事呈现出一种极富诗意的动人情感,同时,这种室内与室外的衔接在光线和音乐的配合之下也营造出了许鞍华所追求的侯孝贤式的散文化镜头语言.在《明月几时有》中,边缘空间的分隔性则为这个战时故事另辟了更为动人的视觉和情感层次.片中春夏饰演的少女情报人员被捕入狱之后跪在牢房内祈祷,透过分隔着牢房内外的窗户,我们看到她眼中闪烁着悲壮而又热切的泪水,在被窗户隔绝着的牢房内,一个诚恳的心灵正在向上帝诉说着对自由的渴望,这一处理使得这个悲剧角色显得更为复杂.同样的,在这部影片的结尾处,方兰在码头与“黑仔”告别,这一对乱世战友的分离场景并没有被处理得十分悲壮.相反,许鞍华侧重展现的是两个年轻人之间的脉脉温情和对胜利的迫切期望,这一氛围在方姑站立于码头上眺望的镜头里被渲染到了极致.在整部影片中,方兰站立于码头眺望的镜头多次出现,在码头这个边缘空间里凝聚着最极致的战争之痛和期待之切.许鞍华在这部讲述大时代的影片中利用空间传达着每一个小人物坚定的渴望之心,而这种细致入微的情感表达又营造出了如一轮明月一般哀婉动人却也不失光彩的整体风格.在这些案例中,香港不再只是刻板印象中冰冷的钢筋森林,城市中每个个体的喜怒哀乐都为这个空间注入了现代性之隐忧之外的丰富内涵.其次,许鞍华还利用整体空间呈现的变换表现一种怀旧情怀与美感.影片《天水围的日与夜》的开头与结尾都出现了对旧时香港空间的呈现,这种在当下与历史之间的空间转换配合以故事中母子二人与婆婆之间的温馨生活催化着怀旧情趣的产生.对于时常被定义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丧失了地方性的香港城市空间,这一空间变换的方法将观众迅速拉回了“原生”的香港,从而也就使得观者在怀旧中发现了观照香港城市空间的另一种方式.最后,许鞍华还利用空间呈现的超现实色彩营造着影片的超脱感.在《女人四十》中,压力重重的阿娥与公公在回家的途中见到了“夏雪”(影片的英文译名即‘summer snow’),在漫天飞舞的“夏雪”中,公公如孩童般兴奋地嬉戏,疲惫的阿娥也在这出人意外的场景中体会到了久违的轻松愉快.虽然是公公的误会,这场夏天的大雪却在影片中营造出了有着超现实色彩的美感,在这一氛围中,主人公得以暂时摆脱沉重的现实而享受单纯的快乐.此外,《我的路》结尾处主人公走上大街时飞到她身边的白鸽、《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照临姨妈的那轮光彩照人的巨大明月都是导演在空间呈现中为营造出超脱感而加入的超现实元素.这些超现实的元素也像是一个个小小的窗口,为所有边缘叙事中的主人公提供着某种逃离现实的可能.许鞍华曾在回答某位学者对其在香港电影中的定位时坚定地说道,“我一定是不属于先锋派的.我认为我是在主流的边缘工作.”{14}正是这种对边缘位置的选择决定了其影片空间呈现上的独特美学风格,也正是在这种情感基调与美学风格之中,许鞍华才得以不断推陈出新地用作品表达出她对边缘人群处境的个人观照,同时也在更大层面上为观者提供了观照香港城市空间的另一种方式.
空间论文参考资料:
本文汇总,上文是关于经典空间专业范文可作为许鞍华和边缘和许鞍华电影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空间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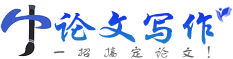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