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儒对中国诗经学的继承性接受》
本文是诗经方面大学毕业论文范文跟诗经和日本汉儒和继承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内容提要】 自公元五世纪《诗经》传入日本,即开始长达千余年的日本《诗经》接受史.日儒对《诗经》的接受大致可分为继承性接受与改造性接受两种方式.而继承性接受的特征更为显著,是日本诗经学的主流接受方式.继承性接受思维主导下的日本《诗》著带有鲜明的注疏表征,与日本自古以来重传统、重家学的传经模式一脉相承,在保存《诗经》古本与承传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 日本 诗经学 继承性接受 海外汉学
【中图分类号】 I207 【 文章编号】 1003-4048(2017)04-0089-94
【文献标识码】 A 【 DOI】 10.16496/j.cnki.rbyj.2017.04.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日本江户《诗经》学与中国影响因素研究”(17CZW037)、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日本江户时代《诗经》著述考(2015-028)”.
【作者简介】 张小敏,山西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太原 030006).
研究海外汉学,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即研究对象国的汉学形态与本国学术究竟有何异同,这是作为旁观者自然而然会联想到的一个问题,也是研究者凸显研究对象价值的症结所在.日本诗经学研究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在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汉文化圈内,两个最主要的辐射国朝鲜和日本当下的诗经学研究,对此问题的回答却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究其原因,一则不能立足经典文本,二则缺乏中外比较的视野.唯有建立在文本精读、辨析的基础上,开展朝、日诗经学与中国诗经学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理清两国诗经学的复杂关系,对《诗经》在域外的流播方式有一个全面、准确的把握.
就日本诗经学而言,江户时代(1603 年-1867年)以前的诗经学,材料过于繁复、零散,不易把握.明治以后的诗经学又受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深刻,也不能准确呈现千余年汉文化主导下的日本诗经学的接受形态.而江户时代作为日本接受中国经学的巅峰时期,产生的数百部《诗经》著述文献,恰好满足了我们研究日本汉儒接受中国诗经学的理路、方法和成果形态的需要.因此,本文以日本江户《诗经》著述为重点考察对象,在与中国诗经学的比较下,去发现日本汉儒学习、继承中国诗经学的具体策略.
据笔者研究,日本汉儒接受中国诗经学的路径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继承性接受,另一种是改造性接受.所谓继承性接受,是指日本汉儒全面接受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对《诗经》经学意义的体认与中国学者一致,他的感受方式和注释体例也完全遵循中国传统注疏,旨在本国全面保留《诗经》的汉学传统.最明显的特征是,如果不看作者,我们仅凭内容很难辨别出作者的国别.而改造性接受则正好相反,充分利用《诗经》在日本的认可度,以此为载体,打着复古的旗帜,在民族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主导下,对《诗经》进行新的阐释,意在回护和建构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其中不乏一些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改造的情况,为便于讨论,根据其总体倾向性,可以将其划分到以上两类.两种接受路径中,继承性接受的特点更为鲜明,是日本接受《诗经》的主流方式,实质上也是日本接受汉学的主流方式.
一、继承性接受的著述表征
日本《诗经》著述的继承性接受有着显著的特征,大致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大量抄写、刊印《诗经》正文、经典注本.注本包括《毛传郑笺》、《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翻阅今本各公私图书馆藏书目录,以上所涉书籍无疑是“诗类”中体量最大,版本最为丰富的图书.今天看来,它们虽为常见书籍,却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一些早期本子,比如唐写本、宋元刊本,其价值不容质疑.即便江户时代的部分本子,因其参校古本、今本而成,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再抄写、刊印这些基本用书,旨在为日本人研学《诗经》提供最好的底本.
二是主要征引中国文献,少见日本人著述.作者有着与中国学者大致相同的,以汉学为基础的知识结构,主要体现在引用文献上,征引文献以中国文献为主,少见日本文献.日本现存最早的用汉文写就的《诗》学专著林恕的《诗经私考》,倾向于首肯明代许天增《诗经讲意》和陈元亮《鉴湖诗说》;中村之钦的《笔记诗集传》,主要赖明代黄文焕《诗经嫏嬛》和黄佐《诗经通解》疏解文意;松永昌易《头注诗经集注》,则将明代王崇庆的《诗经衍义》和徐奋鹏的《诗经删补》作为最主要的文献来源.户崎允明折中《毛传》、《郑笺》、《孔疏》、《朱传》四家,择其善者注释《诗经》,然大意不出《诗序》的旨趣,故名曰《古注诗经考》.随着明清《诗》著的大量传入,之后的著述虽引用范围愈广,但基本不出中国文献的范域,多以一种为主,旁涉数家集注而成,总体而言,引证数量较中国著述有失狭窄.
三是疏不破注,鲜下按语.日本《诗》注的继承性接受或尊序,或尊朱,坚持疏不破注的解《诗》原则,体现出明确的《诗》学旨趣.三宅重固的《诗经笔记》是一部带有明显笔记性质的《诗集传》注本,穿插《朱子语类》、《诗序辨说》、《诗传大全》、《诗经删补》、《诗经衍义》等观点,偶发一两句无关要旨的按语.冈白驹《毛诗补义序》曰:“舍是(《诗序》)伥伥然乎,去圣千五百年之后,妄揣作者之意,就其说虽高乎,竟是郢书燕说已.”[1] 体例先列《诗序》与《毛传》,务在疏解《毛传》,回护《诗序》,依《序》说《诗》.龟井昱《古序翼》视《诗序》为“先哲之遗言”,奉之为“金科玉条”,力驳朱熹《诗序辨说》.并将这种《诗》学观践行于《诗经》的具体注疏中,著《毛诗考》.此作唯《诗序》是从,力倡《诗序》,旨在重建以《诗序》为宗的《诗》学价值体系.诸葛晃《诗序集说》则将《诗序》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广采汉唐宋元明清史上有影响的各家《诗》说集注《诗序》.存在明显地征引有余,辨析不足的弊病.总之,此类著作在疏不破注的注《诗》原则下,主要汇编中国《诗经》文献而成,而又鲜有按语.即便有按语,也大体不出中国已有的《诗》学认知,借此形成了国人对日本《诗》学“借鉴”大于“独创”的整体印象.
四是强烈的宗经意识.继承性接受《诗》著都表现出对《诗经》经学意义的高度认同.在“五经”价值体系中,《诗》因兼具经学与文学的双重特质而显得有些特别.《说文》:“经,织纵丝也.”有恒定不变之意,故刘勰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也.”较之文学解读的多样性,经学阐释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样也就决定了经学传统以继述为主要接受方式的承传模式.日本的思想文化自古受中国影响至深,经学尤为明显.据信史记载,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是最早,也是日本引进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内容构成.直到江户时代达到鼎盛,短短二百年产生数千种研究《十三经》的著作.日本学人对从中国自觉引进的儒家经典文本格外珍视,早在7 世纪即仿效唐制设立太学,以“九经”为课业,将其作为教育上层贵族子弟的重要教材.抱着对中国经学完全尊重、全面接受的态度,重传统,守家学,承传千余年,由此在异域日本诞生并形成了一个类似中国经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在东亚汉文化圈内得到日人广泛、高度的文化认同,成为建构日本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说征引中国文献、述而不作是继承性接受《诗》著的外在表征,那么对《诗经》经学意义的体认则可以看作是它的内在表征.正是基于对《诗经》经学身份的认同,对《诗经》经学传统的尊重,此类《诗》著才表现出以继承为主要目的的接受方式.
二、继承性接受的历史成因
日本《诗》学的继承性接受与其早期儒学接受传统一脉相承.从江户之前的《诗经》相关文献中几乎看不到日本人阐释的文字,其接受主要表现为,《诗经》文字直接引用或间接化用于朝廷外交文书、典章制度、君臣昭表以及上层贵族的汉诗或和歌当中.无须讳言,《诗经》在日本长达一千余年的接受史中,基本处于学习熟练、模仿应用的层面,极难从中发掘出日本人阐释《诗经》的思维逻辑及价值追求.陈景彦等著《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与改造》中也说:“日本在江户时代之前,吸收儒家文化只是表层而已,更深层次的吸收则是江户时代.日本学者安井小太郎也曾说过:‘到江户时代为止的日本学问始终是模仿中国的.’”[2] 因此,就诗经学内部而言,江户之前的诗经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对《诗经》早期文本的保存上,即《诗经》的文献学价值.
导致产生以上情况的原因,与日本自古以来的经典接受群体和接受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和中国有着较大的区别,自平安中期以来形成的较为固定的传经模式,仅限在皇室贵族子弟极其狭窄的范围传衍.另博士职实行世袭制,如明经博士专属清原家、中原家所有.历代世袭的经师和有限的受众,一方面限制了经学普及化及其多样化阐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极易形成重传承、守家学的经学传统,使得自平安时代(794年-1192 年)以来发展起来的汉学传统得以保存下来.由于文献的散逸,已经很难得知早期博士授经的具体内容和方式.现在留存下来的最早、最完整的当属清原宣贤写本《毛诗抄》,清原宣贤(1475-1550)即是清原家世袭的明经博士,《毛诗抄》正是他讲授《毛诗》时学生的听课实录,从中可以了解到早期清原家讲读《诗经》的基本情况.关于此书,王晓平先生对其文献学价值评价甚高,说:“由于平安时代以来,日本经学家皆为清原和大江两家世系相传,而大江家的资料又相对保存甚少,所以谈到日本江户时代以前的诗经学,笼统言之,称为‘清原诗经学’也不为过.”[3] 清原宣贤《毛诗抄》作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由日人完成的《诗》学专著,鉴于日本特有的经学传播方式,王先生的评价不无道理.张宝山先生曾对此书作专门研究,说:“宣贤之《毛诗抄》虽常引述宋元明儒之说,然其主体仍以《传》、《笺》、《正义》之说为据,所引‘近注’乃为对照和补充‘本注’之用,其间有主、从之关系,并非融合汉宋之立场.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中世《诗经》学仍延续中国著述传统,其保守性远高于中国本土.”[4] 张先生所言甚明,当在中国早已完成儒学的转型,朱子学大行其道之时,大量朱子学著作赖中日僧侣流布日本,而清原宣贤仍然遵循着自平安期以来的家学传统——尊崇汉学,仅将朱子学作为“对照和补充”之用,其保守性可想而知.江户学者林信澄《惺窝先生行状》曾言:“本朝儒者博士自古唯读汉唐注疏,点经传,加倭训.”[5] 用“点”和“加”两个动词描述明经博士对文本所作的工作,“点经传”是对文本的句读,“加倭训”是指日本自古学习汉文发明的一种特有的训读方法,即在汉文旁边用本国通行文字标注汉文音读及文意,以便于初学者学习和理解的一种阅读方法.类似于国人今天学英语在英文旁标注的汉文,更多为学习方便为目的,并非一般理解的训释.由此可以看出江户前千余年日本《诗经》学乃至儒学的承传模式及其鲜明的保守性特征.
时至江户时代,这种秉承家学、一支独传的传经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识也由贵族向普通平民下移,但由此形成的尊古、宗经的治经传统却得以延续.市野迷菴《正平本论语札记》曰:“恭维皇国质素成风,古训是由,守而不失,真本永传”.[6] 安井息轩《毛诗集说》曰:“阮(阮元)每有意于抑《考文》(《七经孟子考文》),故动辄古本云采《正义》误删,据《释文》妄增.不知我古博士之法,传授谨严,不敢增损一画,不如汉人恣意窜改也.彼之疑我乃所以自讹也.”[7] 又曰:“不知我古本传自隋初,历世宝守,不敢移易一字,不类朱明以后,任意增损经传,岂能采孔颖达《正义》而补之哉?”[8] 再次披露出自隋唐以来日本明经博士一以贯之地强烈的宗经意识和谨严的治学态度,“古训是由”,“历世宝守”,“不敢增损一画”,表现出对此作法的首肯以及自豪感,并将这种理念与方法践行于自己的注疏实践当中.因此江户时代二百多年中,从初期林恕的《诗经私考》直至末期安井息轩的《毛诗辑疏》,始终保持着继承性接受的鲜明特征,使中国的经学传统得以在异域日本延续.
尽管日本自王朝以来形成的这种世袭为学、封闭授经的学制,对于养成日儒重传承、守师说的继承性接受传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笔者以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学内在的优秀素质,以及在它强大文化辐射力下形成的日本人发自内心深处的价值认同.“五经”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文化最本源的知识和信息,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五经”构成的经典体系,才维系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平稳发展.处于文化发展初期的日本,面对经过历史证明又高度成熟的中国经典文化,继承性接受应该是顺其自然的选择.
三、继承性接受的文化意义
继承性接受因为大量征引中国文献,述而不作,鲜下按语,往往给人留下日本诗经学“借鉴”大于“独创”的印象.连日本学者自己也说,日本儒学史“可以看作是带有相应变形而压缩地重复了”的中国儒学史.[9] 据笔者研究表明,日本诗经学最为繁荣的江户时期,其《诗经》研究与明清诗经学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它们之间自然形成一种此消彼涨的连锁反应模式.江户诗经学甚至可以说就是明清诗经学的浓缩版.[10] 事实上,从《诗经》在日本的继承与改造两种主要接受方式来看,其继承性特点确实要更为明显,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诗》学和文化价值.否定传统,求新求奇,固然能获得众人的关注,但未必有持续的影响力.秉承传统,固本守正,很难获得时人的注意,但未必没有顽强的生命力.日儒对中国诗经学继承性接受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化、模式化进程,体现出的是一种价值观念的普遍性和深刻性,越值得深思和发掘.
就诗经学自身而言,日本汉儒的继承性接受最大的优势,莫过于对《诗经》古本的承传上.自平安期以来,日本明经博士便把承传唐时古本和维护中国正统注释作为家学的历史使命,后世历代奉行不悖,直到江户时代的龟井昭阳、仁井田好古、安井息轩等无不利用世传“唐本”为底本来注解《诗经》.尽管他们只是一个藩国的教习,并不是什么身份显赫的朝廷博士,但已全然接受了这种传统,并自觉践行.奈良平安时期,日本全面向中国学习,向中国派数十次遣隋使、遣唐使,带回包括《毛诗》、《郑笺》在内的大批中国文化典籍.至大化改新,仿唐制设官学、置博士,《毛诗》、《郑笺》等经典注本开始进入官学教材的序列,得以在制度的保障下世代传习.加之日本汉儒谨严的家学传统,以及在家学传统下养成的宗经意识和治经态度,其世代相守的《诗经》注本应该与唐代传入日本的本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诚如岛田翰在《旧抄本考? 小引》中所言:“盖王朝之盛,远通使隋唐,博征遗经,广采普搜,舶载以归,守而不失,真本永传.是以夏殷三代之鼎钟,六朝隋唐之遗卷,往往而有存者.”[11] 关于日藏汉籍的优势,清代学者多有论及,今日学者的搜集、整理、研究更有方兴未艾之势.日本现存《诗》类文献的唐钞本、古写本、古印本、和刻本甚多.天津师范大学王晓平教授积八年之功,收集到大量日本诗经学文献,著有《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一书.该书用近百分之九十的篇幅论述《诗经》日藏古本的文献学价值,对现存状况、版本渊源、文献价值考释详细.总之,日藏《诗经》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将大大丰富《诗经》文献学研究内容,必将成为整个诗经学研究的有益补充.
日本世代汉儒表面上看是对中国正统注释和《诗经》诸类古本的承传,深层次体现出的是对《诗经》所运载的中国主流文化精神的内在接受和高度认可.孔子确立的“五经”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基础和伦理秩序,它们从不同的方面规定着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方向.《易》、《书》、《礼》、《春秋》都具有显著的道德观念和意义指向,或者说它们“经”的本色鲜明,唯独抒发人情的《诗》能进入最早的经典体系多少让人费解.安井息轩曰:“《诗》则多出于田畯红女之口,其辞繁,其事杂,又时有不可为训者.读之若游百货之市,珍怪炫目,而无知所适从也.”[12] 江户大儒伊藤仁斋言:“古之载籍,若《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春秋》以道名分,格局既定,体面各殊.惟《诗》出于古人吟咏情性之言,而无勉强矜持之态,无润饰雕镂之词,是以见者易入,而闻者易感,故圣人取焉.”[13]《诗》因道人情,而具有“易入”、“易感”的优势,故圣人裁定为经.伊藤仁斋的理解带有私意,因此部分地把握住《诗经》的核心价值.刘毓庆先生曾依据《诗序》作出对《诗经》的价值判断,言简义丰,切中要害.他说:“《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正得失’,言其伦理道德功能;‘动天地,感鬼神’指其情感功能.正人之行、动人之心的双重功能,确立了《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14] 一言其正人得失的教化功能,一言其惊天动地的感化功能.日儒正是看到了《诗经》“发乎情止乎礼”的价值功能,通过学《诗》、用《诗》、注《诗》等方式,使这一来自异域的经典持久地发挥作用,以建构本民族的文化精神.
尊崇中国经典,并践行于注疏的实践中,是整个江户时代继承性接受《诗》著的群体特征.中村之钦揭举《朱传》原文,以国字解释,撰《诗经示蒙句解》.序曰:“《诗》者,孔门之所先,而学者之所急也.然去古既远,邦域亦殊,且《诗》之为言,婉微曲折,苟非以国字解释之,则不能使初学喻其意矣,况使彼有得兴、观、群、怨、忠、孝之益乎?”[15] 他著《诗经》蒙学教材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让初学者读懂诗意,更在于获得言外之旨,受到诸如忠孝的人格训化.冈白驹《毛诗补义序》曰:“尽人情世态,又莫详于《诗》焉.君子不达乎人情世态,不能为政.”[16] 序要在阐明《诗经》中的“为政之道”.仁井田好古《毛诗补传序》曰:“盖《诗》也者,道人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道德仁义以耕耨之,而治乱盛衰之所由,千汇万态,不可得而究者,《诗》之所载备矣.”[17] 安井息轩慨叹道:“有志于斯世者,《诗》岂可不学乎哉?”[18] 在其生命风烛残年之时,儒学举步维艰之时,执着于《毛诗辑疏》的著述,用学术回应时代命题,正是建立在对《诗经》经学意义深层体认之上.说:“大史之观风,足以见其国之治乱存亡者,则采之.”[19]“ 圣人编诗之意,岂有他哉?亦唯原治乱所由起,欲使后世人主知所去就耳.”[20]“ 夫《春秋》正名谨礼,苟有紊上下之分者,随而贬之,无所回避,乃圣人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也.《诗》则主于情,情从势而变,就其情,以观势所赴,成败治乱,明若观火,故诵《诗》三百,可以达为政之道矣.”[21] 在安井衡的心目中,《诗》不仅仅是诗歌,而是经圣人裁定的、关乎国之治乱的大经大法.他们以群体的力量使得这种文化精神得以在本国滋长蔓延,持续地为营建本民族文化提供精神滋养,从而形成了日本迥异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思想文化体系.不然,就无法理解《诗经》在日本长达近一千五百年的接受史,也无法解释日儒世代相守的继承性接受的行为方式.
日本对中国诗经学的继承性接受,不仅表现在《诗经》领域,也是整个经学乃至汉学的重要特征.或者说是日本这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国家最主要的文化接受策略.但绝不能因此否定它的文化价值和历史贡献.正是他们的执着与坚守,维系了儒学的纯粹本色,使其在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持续地彰显智慧.此外,文化的发展自有其规律,它必然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熔铸新智而推动前行的.这里有一个主与次、本与末的问题,所谓继承性接受在其中扮演的就是主流或固本的角色.因此,即便是在西方文化主导日本的今天,依然可以看到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中江户汉学学风的遗存.
参考文献:
[1] 冈白驹. 毛诗补义[O].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延享三年(1746)本:3.
[2] 陈景彦、王玉强. 江户时代日本对儒学的吸收与改造[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
[3] 王晓平. 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M]. 北京: 中华书局,2012:352.
[4] 张宝三. 清原宣贤《毛诗抄》研究:以和《毛诗注疏》之关系为中心[A]. 张宝三、杨儒宾. 日本汉学研究续谈:思想文化篇[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3.
[5] 林信澄. 惺窝先生行状,林罗山. 惺窝稿[O]. 宽永四年(1627)刊本:4.
[6] 市野迷菴. 正平本论语札记[A]. 关仪一郎. 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M]. : 凤出版,1973:3.
[7] 安井息轩. 毛诗集说[M].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写本.
[8] 安井衡. 毛诗辑疏[M]. : 崇文院,1932: 卷七25.
[9] 永田广志. 日本哲学思想史[M](中译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61.
[10] 张小敏. 日本江户时代《诗经》学研究[J]. 东北师大学报,2015(4):161-162.
[11] 转引王晓平. 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M]. 北京: 中华书局,2012:2.
[12] 安井息轩. 诗亡然后春秋作说. 安井息轩文集[H],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写本.
[13] 伊藤仁斋. 诗说. 伊藤仁斋. 古学先生文集[O]. 京兆玉树堂,享保丁酉(1717): 卷三16.
[14] 刘毓庆. 怎样读诗经[N]. 中华读书报,2015-5-20.
[15]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汉字国字解全书[M]. :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6:1.
[16] 冈白驹. 毛诗补义[O].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延享三年(1746)本:2.
[17] 仁井田好古. 毛诗补传[M].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文政六年(1823)序刊本: 序.
[18] 安井息轩. 诗亡然后春秋作说. 安井息轩文集[H],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写本.
[19] 安井衡. 毛诗辑疏[M]. : 崇文院,1932: 卷七4.
[20] 安井衡. 毛诗辑疏[M]. : 崇文院,1932: 卷四27.
[21] 安井衡. 毛诗辑疏[M]. : 崇文院,1932: 卷四1.
(责任编辑 张磊)
诗经论文参考资料:
该文点评,此文为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诗经和日本汉儒和继承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诗经本科毕业论文诗经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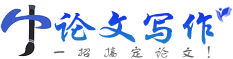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