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冷战批评和中国文学现代性》
本文是关于中国文学方面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与现代性和冷战和中国文学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主持人季进:“后冷战时代”(Post-Cold War era)是学界对于自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两极格局破冰以来新型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权宜表述,然而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历经了“全球化浪潮”、“互联网时代”、“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乃至“后人类”(Posthuman)等种种理论的洗礼之后,却依然没能达成足够的共识与和解,以摆脱仍需借助“冷战”字眼来定义当下的处境.当然,即便是对于“后冷战时代”的表述本身,学者们也是疑虑重重,陈光兴在《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2006)中便直言,“所谓的后冷战时期尚未到来”,因为种种现象表明,“其实我们过去活在半个不完整的世界,冷战结束的宣告,并不能轻易抹去锁在这半个世界中所积累之文化政治效应的历史铭刻”.据陈光兴所言,启发其上述思考的历史时刻,是2000 年朝韩第一次首脑会晤及其促成的南北家属团聚,尽管视觉信息的呈现明显由两韩国家机器主控,但高度的情绪流动,早已甩开国家象征权力的限制,切入了社会集体的情感结构与空间.巧合的是,就在今年(2018)我们又迎来了朝鲜半岛的“历史性时刻”,有关“第一次”首脑会晤,联合声明,家属团聚,南北合作的新闻报道再次纷至沓来,与近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形成饶有意味的对话.不仅如此,我们在这些年的国际政治尤其是大国关系中也明显感受到与日俱增的龃龉和张力,“ 冷战思维”甚至“ 反智传统”(Anti-Intellectuali)等陈旧词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于外交辞令和学术批判之中,这不仅证明了陈光兴所谓冷战“结构性效应”的阴魂不散,也支持了其对于“去冷战”(de-Cold War)的迫切吁求.
如果我们认同上述观察,那是否意味着以“冷战”或“去冷战”为语境来重新检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变得颇有必要?不仅因为这一阶段的文学实践与交流本身备受“冷战”氛围的壁障与阻断,更因为我们在日后的回溯与追问中对于这一氛围的回避,以及对于其中基于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结构的不察.有感于此,本期专栏向大家隆重推荐近年来该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力作,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王晓珏教授的《冷战与中国文学现代性:1949 前后重新想象中国的方法》(Modernity with aCold War Face:Reimagining the Na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across the 1949 Divide,2013).我们有幸邀请到王晓珏教授就此话题展开讨论,同时配发了美国宾州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沈双教授的评论性文章,希望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该书的学术理路,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
《去冷战批评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主要取自原著的结语部分,由王晓珏教授亲自增补审订,可谓最直观的“夫子自道”.论文的前半部分梳理了原书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关怀.“冷战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议题的浮现,首先是起于“9·11”后美国主流媒体报道中二元对立修辞的复苏以及美国学界对于“文化冷战”研究的升温,经由桑德斯《文化冷战:情报局和文艺世界》(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Letters),尼古拉斯·卡尔《冷战与美国新闻署》(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Information Agency)和安德鲁·鲁宾《权威的档案》(Archives of Authority)等著述,“冷战”之于文化建构和知识生产层面的影响得到确认.继而,有感于1949 年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冷战意义上的分裂对峙,不仅启发了“歧义纷呈的民族国家、政治文化想象”,也挑战了“中国文学、新文学、现代文学、国族文学”等传统批评范畴的限度,其“在政治、文化、语言层面上”所生成的诸多“新的边界、中心、路径、网络与交叉点”,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自我定位设置了难题.虽然“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没有哪个时段的现代中国文学比冷战时期承担了更为深重的政治责任”,但如若我们不仅仅在“国族文学”内部讨论这些问题,就会发现“文学,与其说是再现着政治现实或是国族历史,不如说是代表和体现了我们称之为冷战的那些诡谲的经验:个人的、国族的、国际的”,因而“去冷战”的检讨也不能囿于国族的自我中心,而应“跨越文体、性别、学科、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发现多元的“去冷战”策略与实践,将“断裂”化作转机.论文的后半部分探讨了建设“一种有效的去冷战批评的实践话语”的可能,其路径是通过分析冷战末期三次失效的沟通案例.一是1981 年丁玲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Program),其大大出乎西方身份预设的私人反应,显示了其对于“资本主义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等自我标榜的普世理论中二元性的警觉.二是1980 年沈从文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讲座,其历史文物研究的用心所在,类似于奥尔巴赫所谓“人类的自我表达的实现”的“内在历史”,故而其文化实践虽然对政治缄口不言,实际上却是“对中国文明之危机的深切的回应”.三是陈映真1982 年赴爱荷华大学,与几名东欧作家围绕美国电影产生争执,在双方以不同语言共唱《国际歌》取得和解的记忆中,陈看到了新型国际主义形式的可能.显然在这三个案例中,失效并不意味着失败,相反它代表看似铁板一块的二元对立话语中的罅隙,以及与之竞争的努力.沈双教授的评论,原载于著名的学术刊物《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论文从“民族文学史”的角度出发,指出王著针对学界将1949 年作为大写的断代分界时所预设的“冷战的二元对立意识,如共产主义与、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立等等”,提出以现代性和民族主义为考察对象的研究策略.通过对沈从文、丁玲、吴浊流、冯至和张爱玲等五位作家处理冷战时期文化对峙和思想限制的实践,来论证彼时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多元想象,以及中国主体性的复数形式.沈双教授认为,王晓珏通过将五位作家视作具有“离心放射潜力”的分离点,设计出一种“破碎性”的阅读方式,实现其有意识的“去冷战”策略,并对后冷战时代汉语世界的文化政治提供了适时的干预.这样的研究与评论,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学术视域,对于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来说,显然蕴蓄着巨大的刺激性力量,有待我们的回应与对话.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
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在地理上,它带来了冷战式的分裂,导致了多重离散、分隔与动荡.在文化上,它引发了歧义纷呈的民族国家、政治文化想象.1949年的分裂是断裂、延续、转折,它是危机也是契机;流亡和疏离的经验启发了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ed)的自我反思,以及理解历史与文化的新的可能性.1949年之后,中国文学版图呈现出多元的、跨地缘政治疆界的特点.中国文学、新文学、现代文学、国族文学这些范畴是否依然有效?如何在国族文学的传统分野之外,寻求新的研究视角?1949年不仅是一个中国事件,同时也是全球冷战格局形成的一个关键点.冷战开启的地理学,在政治、文化、语言层面上生成了新的边界、中心、路径、网络与交叉点.处于冷战的亚洲与世界的格局之中,如何重新寻求中国文学在兴起的世界文学中的特殊定位?
《冷战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一书动笔于“9·11”恐怖袭击不久之后的纽约.当时,美国主流媒体对恐怖主义的描述,动用了许多冷战时期的二元对立的话语和修辞,并宣告新冷战时代的到来.学界对文化冷战的兴趣逐渐增长,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冷战时期东西方政府如何借助文化的武器,竞争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①.其中翘楚当推桑德斯出版于1999年的专著《文化冷战:情报局和文艺世界》(FrancesStonor Sauders,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仔细钩沉了在美国和欧洲,中情局通过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团体的隐秘资助进行的种种反共文化项目;尼古拉斯·卡尔2008 年的《冷战与美国新闻署1949-89》(Nicolas J. Cull,The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1945-1989)一书,对美国新闻署在冷战期间的公共外交方面的参与与介入进行了完整的描述;以及安德鲁·鲁宾2012年的《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和冷战》(Andrew N. Rubin,Archives of Authority:Empire,Culture,and the Cold War),作者考察了美国中情局的文化自由协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如何以反共为名推崇某些特定作家,以塑造跨国世界文学的新经典.
笔者的《冷战与中国文学现代性》则从20世纪出现的对中国现代性的多重想象出发,在全球文化冷战的语境中来思考中国1949年分裂的意义②.通过对沈从文、丁玲、冯至、吴浊流和张爱玲在1949年前后的文化活动的考察,探讨文学实践中彼此竞争、融合,或冲突的想象现代中国的模式.这些知识分子对艺术与政治、国族与叙述之间的微妙关系的思索,或在大陆,或在台湾、香港,或在海外,跨越地缘政治的隔阂,构成全球文化冷战图景的重要部分.这些未完成的,或是被压抑的理念与想象,在后冷战时代的文学与文化实践中重新浮现出来.
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中,跨越1949年的断裂具有重要的意义.1940年代与1950年代的中国文学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理解美学与政治、国族与叙述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条隐匿的线索.把1949年视为断裂和转机,视为世界冷战格局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内观式的、对民族文学的执着.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对冷战中国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国际政治与外交关系的领域.对1949年的社会文化维度的研究很少.在考察冷战盛期——194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中国大陆、台湾、英属殖民地香港,以及海外华语地区的文学活动时,我认为,相比于历史或政治分析,文学研究更能够把握住冷战变化多端的性质.自从中国文学作为一种现代文化机制出现之后,它就始终深切地与民族、民族主义和国家建设缠绕在一起.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中,没有哪个时段的现代中国文学比冷战时期承担了更为深重的政治责任.隔海对峙的两个政权倾尽全力来掀起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战争.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的是,文学与其说是再现着政治现实或是国族历史,不如说是代表和体现了我们称之为冷战的那些诡谲的经验:个人的、国族的、国际的.
我所选择的五位作家为想象现代中国与文学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视野,希望能够为处在十字路口的现代中国思想绘制地形图.对这五位作家的讨论并无意覆盖现代文学的全貌.还有许多同样重要的作家,他们的文化实践对20世纪的分裂经验也具有症候性的意义.但本书只能稍作提及,甚至遗憾略过:钱锺书(1910—1998)和他的《围城》(1947);路翎(1923—1994)和他的《财主的儿女们》(1945、1948);赵树理(1906—1970)和他的长短篇小说;刘以鬯(1918—2018)和他的《酒徒》(1956),等等.我也无意把这五位作家看作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代表,或者政治牺牲品.在那个转折时代,他们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困惑彷徨.但因为他们的坚持与努力,遭遇了更为深刻的痛苦.本书试图跨越文体、性别、学科、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界限,考察中国冷战文学中互相竞争的多重想象国家、文化与人类生活的方式.在这些中国作家最出色的作品中,他们创造出了各种沟通、连接与阐释的方法,来揭示、对抗那种将东方对立于西方、将共产主义对立于资本主义、将极权主义对立于制的冷战二元论.这些差异与融合、争论与协商的努力,证明了他们的智识能力可以在铁板一块的冷战世界打开缝隙与孔洞.
随着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的溃败,国际冷战对峙告一段落.然而,即便全球化似乎轻而易举地席卷了所有地缘政治疆界,世界的冲突与分隔却并未随冷战而终结.在冷战似乎已成往事之时,冷战思维方式依旧顽固地存在于当下.不论是革命的国家主义话语还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新帝国想象还是反恐主义,冷战思维的幽灵飘荡不散.我们如何去建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有效的去冷战批评的实践话语,来讨论后冷战时代变动的全球现状?如何去寻找新的知识形式,以打破冷战的二元对立,去接触他人的文化与历史,并重构历史与文学的辩证法?作为表达、再现与传播领域的文学与文学批评,又如何继续存在、发挥效用、获取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本文讨论冷战最后几年里的一些特定时刻发生的叙述与交流的失效、暧昧与沉默的时刻.通过考察这些与文学、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等观念相关的实例,我们得以探寻一种去冷战批评的可能性.去冷战批评的目的在于构筑不同人民、文化与思想间新的交流途径,并想象一种新形式的国际主义,或者说是一种新的世界文学的概念,它将更接近于歌德的原初理念——即新的传播、沟通与阐述人类经验的模式.
1981年,在恢复政治名誉后,丁玲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在这次跨过铁幕访问敌国的旅程中,丁玲不断地被问到她在50—70 年代的磨难.对于她的美国观众来说,丁玲下放北大荒养鸡的经历,是极权政治迫害和国家暴力的最好例证.但是丁玲却以一种出人意料的轻快口吻,描述她的农场生活.这不仅使她的观众们感到困惑、失望乃至愤怒,并且经常被引为证据,批评她在80年代的立场.
在一次华府的晚会上,丁玲又一次被中外人士邀请谈谈她的养鸡岁月.丁玲淡淡地说,“养鸡也很有趣味”,震惊全场.这些热心的听众继续追问缘由,并提议丁玲写一部自传,警醒下一代,历史不再重复.面对所有人热切的目光,丁玲冷静地回答,她不在乎记录什么个人历史,“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写头”③.对话在一阵尴尬的沉默中结束了.丁玲后来回忆到,她曾想给这些人上一课,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因此她悄悄地走开了.
这是一次典型的冷战式遭遇,是共产主义的集体观念和式的人道主义观念之间的一次失败的沟通.对丁玲来说,共产主义是所有人类社会的至高理想,尽管它最近在中国走了一段错误的道路.而对她的美国观众来说,将一位作家下放去饲养动物无疑是对基本人性的侵犯,这暴露了共产主义的非人道本质.将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关于人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观念加诸于丁玲的经验的这种冲动,已然将丁玲预先设定为一位共产主义的受害者、目击者以及幸存者,而这样一种身份恰恰是为丁玲所顽强地拒绝的.
丁玲当然不会对人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话语感到陌生,1920年代,她在文坛的亮相之作正是揭露了它们的局限.她的早期作品,包括《莎菲女士的日记》,处理了在半殖民资本主义现代化时期新近获得主体性的中国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这些作品在倡导个人主义理念的同时,也清醒质疑了其所标榜的普世主义:普世的个人主义话语的弊病在于遮掩了历史及语境的特殊性,譬如帝国主义和殖义的侵蚀力量,更不用说种族和性别的差别.冷战意识形态把世界一分为二地分割为共产主义与体制,其话语的核心部分恰恰围绕着人道主义与人性的观念.
在萨伊德写于冷战终结前十年的开创性著作《东方主义》中,他批评了作为一种支配性知识形式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并告诫人们去注意这一貌似普世的概念中的帝国主义残留:“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东方主义在历史上是它的一个部门——延迟了意义的进一步拓展的过程,而正是经由这一过程,才能达到真正的理解.”④
然而,这种冷战式的沟通失败乃至拒绝沟通之所以令丁玲感到不快,其原因不仅在于复杂的国际社会政治秩序问题被以一种可疑的古典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所编码.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她所身处的时刻,即1980年代初,恰有一种不同类型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中国大陆兴起.从王若水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1980)到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1983),从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1979)到伤痕文学,从李泽厚的康德美学到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有关人道主义、人性和人文主义的讨论,在、民间以及批评领域等各个层面方兴未艾⑤.19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论辩和对异化问题的批判试图回应在“”中达到顶峰的社会主义危机.然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以欧洲启蒙价值为其认识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1950年代中期简短的回归欧洲人道主义的思潮在1980年代的延续,而这一思想倾向当时曾遭到冯至这样的学者的严厉谴责,同时,它也是对欧洲启蒙理想的一次迟来的肯定与平反.丁玲后来对伤痕文学及其所彰显的人性理念几近苛责的批评人尽皆知.尽管我与她的文学立场并不相同,但我认为丁玲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品中逐渐消散的革命,而这最终预示了90年代的去政治化与去革命化的思潮⑥.由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之间含而不露的亲缘关系,它亦无法真正地解释晚近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正如汪晖所言,“在这一解释模式中,社会主义从来不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形式;相反,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是对欧洲现代性价值的一次彻底的肯定”⑦.
在冷战日趋缓和之际,丁玲同时遭遇了资本主义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话语的垂询.而对丁玲而言,这两种人道主义都不能提供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的有效方式.由于这两种人道主义都局限于极权对立、压迫对立自由这样的冷战式的二分逻辑,因而在理解人类历史时,它们其实有自己的偏颇,决非如各自所标榜的那样包容与普世.在冷战方兴时,奥尔巴赫(1892—1957)观察指出,冷战的文化危机源于这样一种倾向:“所有的人类活动,要么被塞进欧美模式,要么被塞进苏联布尔什维克模式.”⑧冷战思维的抹平差异、制造分化的力量严重地戕害了人类世界及其文化多元性.如果说冷战是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一种思想的类型,权力借此创造分立、差异、与歧视”⑨,那么它同时也创造了一种破坏知识的方式,并因此限制了知识的生产.
假如关注人的状况与人的历史的人道主义在后冷战时代尚未穷尽其批判潜能,那么,哪一种人道主义仍然保持活力呢?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批评实践,如何积极并有效地介入我们当下的生活?何种“新的”人道主义观念能够帮助我们创造一种去冷战的批评意识,以有效地处理冷战遗产,并消除那种依然活跃在我们这个后冷战时代的冷战话语幽灵?
在《语文学与世界文学》(1952)中,奥尔巴赫扬弃了德国浪漫派语文学传统,提出一种人道主义语文学,以求建立探索历史与文学之关联的文化批评模式,追溯人类“走向对自身的人类状况的自觉,走向对自身天赋潜能的实现”的过程的阐释实践⑩.奥尔巴赫敏锐地意识到冷战文化的危险性,这是一个抹除差异、强化同质性的“猛烈而迅速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同质性强加于丰富多元的人类文化宝库之上.尽管如此,对人道主义实践,他依然抱有希望.奥尔巴赫这种着眼于人文主义的人道主义概念旨在推动不同文化传统间的互相理解与文化交流,同时创造一种知识模式,力求在人性的“多元性中发见统一性”.
在一系列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后在剑桥大学发表的讲座中,爱德华·萨伊德最后一次诉诸人道主义.他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世界性的人道主义概念,它将有助于处理以全球化与恐怖主义为代表的后“9·11”世界的种种危机.在奥尔巴赫的世俗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萨伊德指出,世界性人道主义的任务是将其阐释力量用于抵抗任何支配性的、霸权性的文化.萨伊德主张,一种全球性的、世界性的、移动的人道主义,“必须发掘沉默,发掘记忆与流离失所者的世界,发掘被排斥、隐形之处”.因而,人道主义语文学的批判锋芒在于揭示在语言中被掩盖、隐藏、扭曲之物的阐释能力.萨伊德总结道:
人道主义,我认为,是一种手段,或是一种自觉意识,我们用它来提供一种最终是反律法的、或是对抗性的分析,来处理言辞的空间与它的各种来源及其在物理与社会位置中的部署,从文本到实际中的挪用或抵抗的场所,到传播、阅读与阐释,从私人到公众,从沉默到解释与言说,再重新返回,当我们遭遇自身的沉默与无常——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世界上,有赖于日常生活、历史与希望,对知识与正义,甚或是自由的追寻.
这样一种人道主义实践提供了文本与其所身处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反律法的或对抗性的分析”,因而可以作为一个去冷战批评的起点.在《冷战与中国现代性》一书中,我所致力于揭示的,是知识分子即便在最为深重的冷战局囿之下,仍然努力进行人文主义的实践,探求潜在的能动性,以此来跨越意识形态或其他任何支配性知识形式所施加的限制.去冷战的文化批评质疑冷战话语造成的分裂、隔离与歧视,并抵抗“封闭、化合与固着的意识形态形式”.假如人道主义依旧能为今日的文化批评注入任何生机,一种去冷战的人道主义实践必须反抗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同质化力量,必须挑战隔离与区分的约束,同时要尊重所有人类传统的历史与语境的特殊性.唯其如此,任何文化批判意识才有可能并且有能力在后冷战时代保有政治能量.
这里,让我们重新审视沈从文在1980年代初表达的一种关于文化的深刻观念.在沈从文访美期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一场讲座.在这场演讲中,他重新思考了自己一生不同阶段的工作,并反思了北京何以能够成为中国艺术、文化、人文的博物馆,并且滋养了他的两项彼此相关的热情:写作和历史文物研究.在他对湘西的文学呈现,以及在他的艺术史研究中,沈从文不仅仅是编目、描绘、保存了各种人类活动与文化作品,更重要的是,他将它们当作文本加以处理,厘定它们在人类生活的社会、历史现实中的位置,并因此展现出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正是沈从文的同代人奥尔巴赫所称的“人类的自我表达的实现”的“内在历史”.准此而言,沈从文的文化实践非常接近于一种人文主义的语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文化危机及其不断扩张的意识形态同质化过程中,沈从文在对文物——不论是语言、丝线、数字、铜器或是音符——的这种文本与历史研究中发现了一种保存人性、获得对我们自身的历史产生自觉的方式.人类与人性构成了他一生之工作的根基与信仰,正如他的墓志铭所书:“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尽管他对当代中国具体的政治缄口不言,但他在这一时期的文化实践可以被视为是对中国文明之危机的深切的回应.沈从文的文化反思为后冷战时代的批判性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去冷战批评必须有能力在任何意识形态操控与压迫之外去阅读文本,去捕捉并保存各种文本、文化、历史中的差异与特殊性.
在苏联共产主义溃败之后,当国家社会主义似乎已耗尽了其变革与实验潜力时,一种去冷战批评同时意味着想象替代性道路的勇气——一种替代性的生活方式、自我表达方式和国际文化交流方式,以挑战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开启的又一轮忽视个体文化历史差异的同质化过程.当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将制设定为人类历史的终极形态时,它同时也透露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焦虑,一种“足以与制对抗的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或组织人类集体的方式”的匮乏.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国际主义形式是否依旧可能?这种国际主义如何有助于恢复歌德所预示的文化传统间的丰富联结与交流的世界文学之概念的活力?对这些问题,下面的讨论将为我们提供进一步的反思途径.
2003年,陈映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被授予马来西亚华文最高文学奖项“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在颁奖仪式上,这个奖项的第一届获奖者王安忆谈起了她1982年第一次在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见到陈映真以来,后者给予她的智识上的教益.王安忆感慨道,陈映真是一位孤独的知识分子,“他已经被时代拋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象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对这样一个理想国乌托邦的最好的表达,或许正是王安忆后来发表于《星洲日报》上的那篇文章的标题:“英特纳雄耐尔”,一个国际主义的理想,它尚未实现,便已然被悲剧性地抛弃.
两年后,陈映真也回顾了一次冷战末期发生在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英特纳雄耐尔”时刻,一个语言与思想失效的时刻,一次社会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之间的沟通失败.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是美国冷战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机构,由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与他的太太聂华苓创办于1967年,旨在邀请世界各国的重要作家,提供一个交流、对谈和写作的空间.近些年来,美国文化冷战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并探讨爱荷华大学的文学写作项目与美国冷战机构之间的联系.2014年,艾瑞克·班尼特(Eric Bennett)在《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发表长文《爱荷华如何伤害了文学》,钩沉了1960年代安格尔创建国际写作计划的历史,尤其是其中与美国冷战宣传机构的关系.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成功的基础之上,安格尔设计提出了颇具雄心,面向世界的国际写作计划.针对苏联在莫斯科大学成立的国际学生招募计划,爱荷华的国际写作计划在冷战文化竞赛上更有创意和想象力,企图凭借文学的润物细无声的魅力来征服冷战全球版图.1967年,安格尔成功地获得法菲尔德基金的资助.桑德斯在1999年的力作《文化冷战:情报局和文艺世界》中,已经考证了法菲尔德基金其实是美国中情局秘密设置的文化机构,是文化自由大会的主要资助人.所以,国际写作计划所经营的文学无国界的想象背后与美国冷战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68年,陈映真第一次收到安格尔和太太聂华苓的邀请,参加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坊,然而却没有成行,因为同年他就因其左派立场被国民党当局投入了监狱.直到1982年,也就是丁玲结束在国际写作计划的访问一年之后,陈映真才终于获得准许,前往爱荷华.对聂华苓而言,国际性的作家论坛的念头与她自己在冷战中的离散经验密不可分.聂的文学生涯始于国共内战期间,在台期间为《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1960)的文学副刊担任编辑.《自由中国》在1950年代台湾的反共文学之外占据着一片可观的文学领地.在这份自由派刊物被国民党审查之后,聂华苓离开了白色恐怖下的台湾,在美国继续其文学生命.
一天下午,陈映真和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左翼作家阿奎诺一起去访问他们的东欧同志,共同讨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的理念.然而,这场对话意外地搁浅在一场关于美国电影的激烈争执当中.东欧作家赞赏这些电影对人性细腻入微的刻画,而陈映真和阿奎诺却谴责这些电影的意识形态渗透,借助文化的包装,对美国的冷战保护国的人民宣扬帝国主义.双方操持着带有外国口音的笨拙英语,试图传达对人性与社会主义的不同观点,在这场争论中,无法沟通的是语言还是观念?在僵持中,有人突然开始哼唱一首歌——《国际歌》——于是所有人都用自己的母语,加入了由不同语言演绎的合唱之中.那个下午结束在《国际歌》的旋律里,结束在泪水与彼此的拥抱.
多年以后,在他反思第三世界论和国际主义时,陈映真依旧困惑于那个下午对《国际歌》的召唤:它是“为了一个过去的革命?为了共有过的火热的信仰?为了被唤醒的、对于红旗和国际主义的乡愁”?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成立的宗旨之一是为国际作家提供一个交流的场合,让“中国大陆作家见一见东欧作家,以了解他们的社会主义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不同”,而在这里爆发的这场貌似不可调和的冲突,似乎在一首由各国语言合唱的《国际歌》中被解决,或是取代了.但事实上,这次搁浅的国际主义联盟揭示出了多层面的冲突:不同的社会主义想象之间的冲突;打着冷战反共主义旗帜的美式新帝国主义和新殖义,与亚非拉国家的去殖民独立运动之间的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这两个概念都是交叉的,东方在这里包括亚洲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西方则指欧洲和资本主义阵营,包括了地处亚洲的台湾与菲律宾).更重要的是,这场无法调和的论争揭示了寻求一条替代资本主义的新道路的需求,及其困境乃至急迫性——一种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的“三个世界”图景的第三世界.因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似乎已宣告了历史之终结的二十年以后,陈映真重提当年同唱《国际歌》的时刻,因为在他看来,那个时刻揭示了一种不同的国际主义形式的可能,而非预示了共产主义的安魂曲.
一种去冷战的批评话语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坚韧的信念与承诺之上:它是一种批判意识,抵抗任何忽视和掩盖差异的企图,不论其打着共产主义、普世人道主义、全球化、还是反恐怖主义的旗号;它将文化与传统之间的联结深深地揳入人类状况之中;它在人性的多元性中寻找其共同性.只有这样一种批判立场,才能使我们驱除游荡着的冷战的幽灵,避免滑入一种情绪性的感伤话语和道德立场,这一立场试图以个人英雄对抗国家机器和霸权实体.只有这样一种去冷战批判意识,才能让我们的视界超越冷战二元对立话语的局囿,探索并发现中国现代性中的那些微妙与复杂的地方.■
【注释】
①Frances Stonor Sauders,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New York:New Press,1999;NicolasJ. Cull,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Agency 1945- 198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08;Andrew N. Rubin,Archives of Authority:Empire,Culture,and the Cold War,Princeton,NJ:Prince tonUniversity Press,2012.
②本文是笔者在拙作《冷战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一书的结语的基础上增补修改完成的.Xiaojue Wang,Modernitywith a Cold War Face:Reimagining the Nation in Chinese-Literature across the 1949 Divide. 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3. 原书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于2013年出版.在此特别感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候选人康凌为原书结语提供的初译稿.
③丁玲:《养鸡与养狗》,见《丁玲全集》第6卷,14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Edward Said,Orientali,New York:Vintage,1979,p.254.
⑤周扬报告中的一部分是由文学理论家王元化撰写的.
⑥关于丁玲对伤痕文学的批评,可参其《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丁玲全集》第8卷,441-44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⑦Wang Hui,“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英译稿发表在Social Text 55(Summer 1998),39页,译者为RebeccaE. Karl.
⑧ Erich Auerbach,“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TheCentennial Review XIII(Winter 1969):1-17.
⑨Andrew N. Rubin,Archives of Authority,103页.
⑩Auerbach,“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5、7页.
Said,Humani and Democratic Critici,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81、83页.
Rubin,Archives of Authority,107页.
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见《沈从文全集》第12卷,374-38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Auerbach,“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6页.Jan-Werner Müller,“The Cold War and the IntellectualHistory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冷战与二十世纪晚期的思想史》),见Cambridge Histories of the Cold War(《剑桥冷战史》)2010,21页.
王安忆:《英特纳雄耐尔》,载《上海文学》2004年第1期.
陈映真:《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载《读书》2005年第10期.
Herbert Mitgang,“Publishing:Chinese Weekend in Iowa”(出版:爱荷华的中国周末),New York Times,August17,1979,C24.
(王晓珏,美国罗格斯大学东亚系副教授)
中国文学论文参考资料:
该文点评:这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现代性和冷战和中国文学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中国文学本科毕业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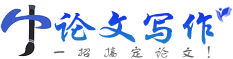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