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目光闪烁,能将黑夜看破谈树才的诗歌》
该文是诗歌相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与树才和诗歌和目光类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星辰如不发光,天空能否宁静?
我只能用悲剧的心情
来祝福天空
——树才《1990年9月15日》
树才的诗歌,就像是暗夜中的星辰,蕴满着冲破黑暗与摆脱困境的冲动,在摒弃了纷繁复杂的遮蔽后,试图抵达的,是生命与心性最本真的澄明.星辰总是在暗夜中,因此灰暗与冰冷是它的底色,而来自灵魂深处的光亮才是它的内核.诗人总是敏感而孤寂的,他们独自冲向这世界的黑暗,然后以词语的触角拷问事物与自身存在的真理.
对于树才来说,无论是结束不了的虚无、生长着疾病的枯瘦肉身,还是无处不在的死亡,灰暗几乎构成了他诗歌的经验世界.面对这“一己”的切身感受以及事物的千般变化与虚无自性,他简单、自由而又极富力度的词语炼金术成为了洞察生命黑洞的武器,在穿透了一切表象的神秘之后,抵达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和智性的超越精神.
一、经验:许多宁静无望的暗夜
树才想抓住“我的骨头错动时发出的声音[1]”,他主张在生活中写诗,写诗的内在点“永远是诗人对自己生存状态及心灵状态的披露[2]”.而在树才的生活和心灵世界中,他感受最多的是许多个宁静而无望的暗夜.缘于对时间的敏感,他意识到“在人类的厨房里,时间的菜刀,需要死亡这块磨刀石[3]”;也正是时间的流逝,使一切都变得空空如也.
树才生于浙江奉化,相对于北方的干燥与粗粝,一个水乡的江南浸润了他生命的前十八年.或许正是江南自然风物的滋养,使他尤为敏感和细致.而从他的人生经历来看,死亡又总是那么切近而逼真地存在着.莫非在《树才小词典》中谈到,“树才四岁丧母,对母亲只有模糊的记忆……自幼养成了对外部世界敏感与超脱的观察.[4]” 1999年,树才的好友苇岸病逝,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以及疾病与死亡的无处不在.2009年,树才的爱女夭折,这更是让他无数次向静夜感慨与自问.
或许正是树才对疾病和死亡痛切与刻骨的经历,他的诗歌才高密度分泌出死亡的气息.可以说,死亡意识、对生与死的思考几乎弥漫了树才诗歌的绝大部分,如《虚脱》、《某个人》、《内外之间》、《慢慢完成》、《同死神开玩笑》、《死亡的献诗》、《窥》、《习静》、《门》、《病这个字》、《竹晶之疼》以及一系列“生日诗”等,不仅直接把生死呈现在了诗歌中,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与死亡的无处不在.“那白天黑夜都敞开的/大门,就是死亡……而死亡是世间运行不息/并把每一个人当做停靠站的[5]”.没有人会怀疑死亡的确定性,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消解了生-死的二元对立,使生成为奔向死的过程,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依然会认为死亡是一件暂时没有被他们碰到的事情.“日常状态就停留在这种两可地承认死亡的‘确知’上——以便继续遮蔽死,削弱死,减轻被抛入死亡的状态.[6]”树才用诗歌提醒人类死亡是一道日夜敞开的门,即使你不愿正视这一道门甚至几乎忘记了这一道门的存在,它也依然无处不在.死亡就像一辆公共汽车,它运行不息,每一个人不过都是它的停靠站.生命的无常让你无从知晓它停靠的时间和方式,纵然你极力躲闪,它依旧会遵循着自己的运行规则.而按照它的规则,就一定能将每一个人找到.在《自己在看》中,我们“每天都躲不过时间的那一声冷”;“什么都在天空里/但人类只顾在大地上忙碌/仿佛只有有才是有的/仿佛失去是最大的悲伤/人类不舍啊!其实/今年的叶子必须抖落,地上的黄叶也必成风景.[7]”树才不断呈现着时间不可逆转所带来的生命存在的悲剧性,既然每一刹那都包含着生与死,那如果我们凡事都要未雨绸缪的话,不如去思考怎样迎接终将到来的死亡.
其实自古以来,“死亡”就是文学表达的永恒主题,死亡从生命的伊始就与其如影随形,忘却死亡的烦恼与实现再生的愿望成为了人类内心深处的心理情结.树才试图用诗化的语言碰触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他所有关于死亡的诗歌就如同是一种对“死亡的修行”, 蒙田曾经说过:“对死亡的修行,就是解脱的修行.学会了怎样死亡的人,就学会了怎样不做奴隶.[8]”他似乎想在一个个日常性的场景中向人们揭开死亡的神秘面纱,让世人接近死亡,熟悉死亡,然后超越死亡.
从对死亡问题的反复思考,以及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引申出的是诗人对世界以及生命虚无本质的认知.在树才诗歌的经验世界中,虚无与无力感作为对时间高度敏感的另一个分泌物也不断流露.1987年,树才大学毕业后来到外经贸部,1989年,和同时代的所有人一样经历了海子之死,海子的死结束了一个蓬勃时代的生命.树才曾说:“就我个人而言,生活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变得陡陗而虚无.[1]” 1990年,他前往非洲塞内加尔开始了外交官生涯.从此,虚无便结束不了了,“虚无是一只壳,更是壳里的空空.[2]”从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到九十年代的转轨,留给一代知识分子的是历史的空场和现实的虚无.当一种最大的“共识”彻底瓦解,意识形态成为枯竭的符号之后,生存的绝对荒芜和空虚便表现了出来.树才在90年代以后的诗歌中也不断传达着一种虚脱感和虚无感.“死亡笼罩了我一下子/阴影还没有消退/第二天,我穿过了一座公园/还没有穿过宽大的恐惧”[3] ;“虚无是因为在生中/一脚踏空.唉多少火焰/我都默默地任其烧成了灰.”[4]纵然和同时代的诗人一样,在他的诗歌中,传达出了一个时代投射给个体的情绪反应,但是他从不试图去把握和记录一个时代.从诗人的独特经历来看,多年来,他似乎一直与政治有着切近的相处.树才曾说:“整个社会生活也是在那一年转向.我对政治始终保持着敏感,而这正是我厌恶它的原因.”[5]也许正因为此,树才在人世间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生命的虚无之后,便开始对这些具有永恒性的命题给予自己的反思与形而上的追问.他似乎认为了解人生的幻灭并寻找超越之路才是能使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的途径.因此他“(我)盘腿打坐度过了/许多宁静无望的暗夜.”[6]几乎被死亡与虚无充溢的经验世界恰如许多宁静而无望的暗夜,但是诗人没有被暗夜所拘,而是似乎一直准备好了刺破黑暗并得到灵魂的飞升,飞升到天上的庭院.在另一个世界诞生,虽然冷,但是很干净.
二、句式:星星的芒刺也是尖的
在夜空中仰望天上的星星,我们能看到像芒刺一样的光,而这些光恰恰可以将黑暗照亮.树才诗歌的句式正像这些星星的芒刺,短小而蕴含着一种诗意的力量.树才的诗歌多用短句,即使使用长句,句法结构也并不繁复,他喜欢将句子切割成一些看似独立却又相互连结的单元,如同星辰散落在漫漫而又无望的黑夜.但是星星的芒刺是尖的,就像坚硬的瘦骨,没有丰腴的包裹,却成为刺破黑暗的武器,读来字字直指人心.如“生命太重要/每时每刻/都必须放弃.灵魂入沧桑/但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无怨.”[7]“扁豆熟了/没有人摘/和风醉了/无人去扶/大自然的一切/来去自如.”[8]“那疼/如今藏在水泥地下/那死/如今存在骨灰盒里.”[9]由于现代汉语的日渐成熟,关系词的引入,句子不断拉长且句法变得复杂,诗歌的散文化也渐渐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而树才诗歌以简单的词语与对应的句式,力求蕴含最饱满的诗意,似乎在对抗着一种散文化的倾向.
树才的诗歌喜欢将句子切割成一些独立的单元,去掉雕饰,让句子以一种简约、本真、最为合心性的形态自然流露出来.在《祝福》中:
初一,或十五
月亮圆满.
我孤单.
因此,我还要伏下身来
祝福无从祝福的土地[10]
这首诗全部使用句法结构简单的短句,不加任何修饰,语言简洁但又充满诗意,每个短句独立成行又虽断实连,“月亮圆满”与“我孤单”分行排列,在满月的映照下更加凸显出我的孤单.似乎初一与十五的月圆都与土地上一个孤单的我无关,因此我要祝福土地. 再如:
生活,在路上.家庭只是
停靠站.轮胎冒烟,出汗,滚烫……[1]
诗人似乎将一个完整的句子刻意以隔断的方式变成几个短句,语言变得短促简洁,但是又把“生活”、“在路上”、“家庭”、“停靠站”几个词强调出来.家庭本来应该是生活的主要场所,但是当下高速运转的忙碌,使生活在路上完成.“轮胎冒烟,出汗,滚烫……”一句,诗人让两个动词和一个形容词在一个句子中排列,暗含着一种生活状态,也似乎内隐了某一个主语.被分割的句子看似与前面两句有些疏离,但实则又藕断丝连.这样一种被异化的、反正常生活的经验以几个简单的词语不加雕饰地直接呈现出来,显得尤为触目惊心.在另一首诗《星星——给明姬》的第4节中,诗人写道:
一念.仿佛
一颗星升起
美,是一念
善,是一念
一颗星熄灭
仿佛.一念[2]
这首诗的句式可谓简约到了极致,但却有一种繁华落尽见真纯的诗意.“一念”与“仿佛”之间以句号隔开,使“一念”和“仿佛”都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单元.句子的语法结构被破坏掉了,而诗歌的语言似乎是在诗人瞬间的意识流动中得以组织起来的.尽管语言朴素微淡,但句子的质地依然是坚硬的,这种坚硬是智慧的锐利,是一种修辞的张力,让看似模糊的诗意逻辑背后透出一种澄澈.
这种短句的运用,弱化了树才诗歌的抒情性,但却使其智性特征凸现出来.这些短句又常常以对应的句式呈现:如“死者已果断地死去/生者犹拘泥地活着”[3] ;“某个人正迎面走来,某个人已擦肩而过.”[4]“曾经,你抱着我.如今,你抱着怨.……怨天怨地,怨割草机……喜鹊欢叫,老树闲坐”[5]这些诗句似乎从古典骈俪中汲取灵感,在一种充满悖论的修辞方式中实现诗人与形而上的问思之间的对话,取得某种文本间性或语言的张力,又构成一种特殊的音乐性.它们有时在诗歌的开篇,暗示着整首诗思考的维度;有时镶嵌在某一个意义的转折处,如同词中的“过片”,调节着诗歌的情感与节奏,这种节奏与思维的节奏同构,与个体生命的节奏同构.虽然没有韵律的调整,但对句式的巧妙运用,使其诗歌无论从内在意蕴还是外在形式上,都具备了很强的音乐性和诗意的逻辑.这些简约而又极富音乐性的诗句恰恰如同深夜中星辰的舞动,它们以智性的光芒试图刺破黑暗的夜空.
三、禅意:佛的好处就是不在我们之外
树才特殊的人生经历或许让他最为真切地感受到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的浊世恶苦,深感尘世间的无量苦恼带来的身心俱瘁.而面对人生的无常与烦恼,禅宗让他开悟.正如树才自己所说:“一个人若无幻灭感,则禅缘不起.幻灭愈深,禅缘愈近.”[6]恰恰是悲苦将他带到了智慧的窄门,从此也成为了真正的单独者.而诗歌则是树才用以表达禅悟的最好方式,也成为了他看破黑暗的无限光明.他在柏林禅寺皈依时曾感悟:“诗即禅,诗道即禅道.但皈依禅,使我识见一己之局囿,之极限.”[7]
佛教与西方基督教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基督教中的神-人处于一种对立的结构中,神是这个世界的主宰,神就是神,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神爱世人,人在神的庇护下生活,人永远不可能变成神;而佛教认为,佛是觉悟了的人,愿度无边悲苦众生.万物众生皆有佛性,皆当成佛.也就是说在佛教的观点中,有情众生,皆可通过毕生的修行,而往生极乐净土.修行最终依靠的是自己,《坛经》上云:“菩提只向心觅,何来向外求玄.”因此树才说:“佛的好处就是不在我们之外 ”[1],由此写诗成为了一种修行,成为了一种修心的见证.
树才最为著名的《单独者》一直被视为诗人的代表作,后来,这个单篇的名字被用于他的诗集.我想一个诗人选择某一个单篇为自己的诗集命名,必有其深刻用意,也足见出这首诗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在我看来,一首《单独者》,正是一个“开悟之境”:
这是正午!心灵确认了.
太阳直射进我的心灵.
没有一棵树投下阴影.
我的体内,冥想的烟散尽,
只剩下蓝,佛教的蓝,统一……
把尘世当作天庭照耀.
我在大地的一隅走着,
但比太阳走得要慢,
我总是遇到风……
我走着,我的心灵就产生风,
我的衣襟就产生飘动.
鸟落进树丛.石头不再拒绝.
因为什么,我成了单独者?
在阳光的温暖中,石头敞亮着,
像暮年的老人在无言中叙说……
倾听者少.听到者更少.
石头毕竟不是鸟.
谁能真正生活得快乐而简单?
不是地上的石头,不是天上的太阳…… [2]
这首诗写于非洲,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正午时分,太阳直射地面,能使一切事物投下的阴影消失殆尽,太阳也同样直射在诗人的心灵之上,将一切冥想与怀疑一扫而空,只剩下佛教的蓝,这尘世就像天庭一样光明而庄严.“我”走在大地的一隅,总是遇到风,似乎成为了走得缓慢的原因.而这在外部世界中遭遇的风恰恰由“我”的心灵产生,一切相皆由心生.这就如六祖慧能大师“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公案一样,诗人思考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意识到内心与外部世界所构成的一个微妙的函数关系,内心的变化导致了外境的变化,我们误以为“我总是遇到风”,却忘记了这些看似动态的图景恰恰是由一个个静止的点构成的.接下来的“鸟落进树丛.石头不再拒绝”两句又选取了两个看似动与看似静的意象“鸟”和“石头”,动静本身不二,“鸟”与“石头”在此达成一种和谐的状态.但也正是因为此,“我成为了单独者”,真理总是在水的另一方,走向真理之人也只有独自彼岸路可行.诉说真理者是如此的寂寞,“倾听者少.听到者更少”,毕竟我们无法通过“诉说”而走向另一个心灵.如何真正生活得快乐而简单?诗人没有停止他的追问,是拥有像鸟一样自由的灵魂和清净的内心.真理本不必诉说,佛说一切法,为除一切心, 既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单独者》似乎可以被看做是诗人在参悟佛禅之后,对世界与自我的一次整体性描述,他用日常生活中简单的意象与朴素的语言试图碰触的是一段深刻、玄妙而神秘的感受与经验.
如果说《单独者》勾勒出的是“开悟之境”,树才的另一首诗作《安宁》则是描绘出了一个“欢喜世界”:
我想写出此刻的安宁
我心中枯草一样驯服的安宁
被风吹送着一直升向天庭的安宁
我想写出这住宅小区的安宁
汽车开走了停车场空荡荡的安宁
儿童们奔跑奶奶们闲聊的安宁
我想写出这风中的清亮的安宁
草茎颤动着咝咝响的安宁
老人裤管里瘦骨的安宁
我想写出这泥地上湿乎乎的安宁
阳光铺出的淡的安宁
断枝裂隙间干巴巴的安宁
我想写出这树影笼罩着的安宁
以及树影之外的安宁
以及天地间青蓝色的安宁
我这么想着没功夫再想别的
我这么想着一路都这么想着
占据我全身心的,就是这
——安宁[1]
这首诗通篇以“我想写出……的安宁”的句式贯穿,全部由对日常生活中细节的发现组成,没有丝毫语言上的雕饰,然而简约质朴的诗句背后却突破了个人世界的局限,呈现出一个庄严的大境界.在这首诗中,诗人从自己内心的安宁写起,延伸到自己生活的外部世界的安宁,最后又回到自己的身心,写出了整个内外环境的清净安宁.诗人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也可谓尽细微之极致,这些细节都为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所见,却往往被我们所忽略.它们入诗人之眼、入诗人之心,变得如此光明、安详和喜悦,因着诗人的一颗欢喜心,此时此刻,占据他全身心的只有安宁.当诗人被安宁所占据全身心时,诗人悟到了禅,而且处处皆是禅,禅并不在我们之外.树才用诗歌复归了一种人的生命中最微妙也最富有启示性的经验,而这些正是现代文明所拒绝探讨的.
另一首诗《去来》,每一句都极其简短,并不刻意写禅意,通篇读来,却禅意尽显:
去哪里过夜?
去大觉寺
来这里干吗?
来大觉寺
大觉寺无门
自然也无进出
大觉寺有门
自然也有石榴
还没有来
怎么就去了?
还没有说
怎么就懂了?
说话说到深处
夜渐渐就去了
问题问个究竟
答案真的来了
去哪里去?
来何处来?
争什么争?
论如何论?
绕舍利塔三匝
去来去来去来
左脚比如去
右脚比如来
任你去又来
大觉寺不觉 [2]
这首诗的题目为“去来”,禅宗本心论中若要达到本心的澄明必须超越“去来”.诗歌的前两段一问一答,正如禅宗公案故事中的对话,去哪里?去大觉寺.来干吗?来大觉寺.诗人并不执着于去来.“大觉寺无门/自然也无进出”,禅宗有言: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如果将大觉寺看做一个觉悟的象征的话,抵达觉悟之境并没有固定的法门,自然也没有进门出门之说.对于真正的修行之人,出定、入定皆是自由.但是现实中的大觉寺恰恰有门,门前也有石榴,对“门”,对“石榴”,关键在“不取”、“不执”.既然是长定不变,又还有什么去与来呢?摆脱了出离与进入,便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一切答案都已澄明,一切问题都已无需争论.“绕舍利塔三匝.去来去来去来”,在去来中参禅悟道.“左脚比如去/右脚比如来”,这两个句子甚至让人不知如何断句.既可以将“比如”作为一个喻词,把左右脚比作“去来”;也可以将“比”作为喻词,将“如去”和“如来”作为喻体.《金刚经》云: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华严经》中也有偈云:十力牟尼亦如是,无所从来无所去,若有净心则现身,量等法界入毛孔.也即是说佛本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自性清净就显现身形,如去如来之中便是禅意.不管你怎样去来,大觉寺都不会执着于此而为之所动.
禅意正是诗人树才一切存在秘密的不二法门,它如一道庄严而澄澈的光芒点亮无明的黑暗世界,它负载在简约而灵动的诗句之上,带着芒刺一般的尖利,刺破了宁静而无望的夜空,一如诗人闪烁的目光,以不在其自身之外的警觉,洞穿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秘密.当现代性的经验无法用一种现代性的方式处理时,我们总是不断向外探求以寻找出路,其实,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并不在人类自身之外.
At elluptate consequam natiatur re sum rerspid ut
诗歌论文参考资料:
归纳上文,本文是大学硕士与诗歌本科诗歌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树才和诗歌和目光方面论文范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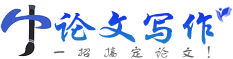

 原创
原创